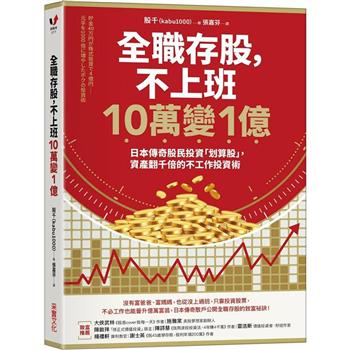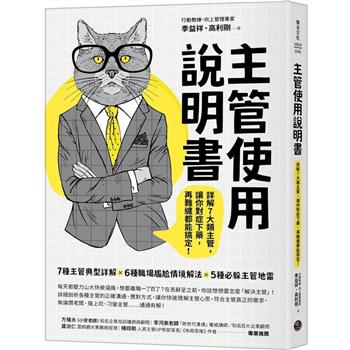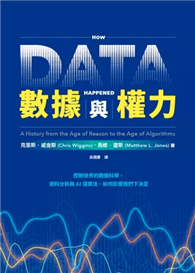多麼希望,人生的盡頭就是青春,璀璨轟烈,沒有遺憾。
★村上春樹之後,唯一征服全球的亞洲作家,《請照顧我媽媽》申京淑最新感人力作!
★申京淑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也是我許多劇本的靈感來源。──金恩淑,《紳士的品格》《巴黎戀人》編劇
★小野 感動推薦
晨間的一通電話,劃破了寧靜的冬日。
八年來,已經遺忘的,無法相見的,在這一刻都被連結了。
那是一段想起來會些微刺痛的青春歲月。
口袋放著媽媽的戒指,卻遲遲不願戴上的潤;
虔誠記錄每一餐,作為生存證明的美縷;
害怕蜘蛛,卻愛上蜘蛛研究的丹;
因為一個背影,而決定守護一輩子的明瑞;
一隻只聽得見雪花飄落的白貓;
還有,消失無蹤卻又如影隨形的「那個人」。
為了尋找「那個人」,四人一貓的生命相互交疊,
但曾經緊緊相繫的四個人,是誰先放手了?
曾經昂首闊步的四個人,是誰先低頭了?
多年前許下的承諾,依舊冰藏在記憶的雪堆之中,等著被實現……
作者簡介:
2011年亞洲文學最高榮譽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得主
申京淑
畢業於韓國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擅長以深刻獨特的視角探索人的內心世界,以象徵和隱喻捕捉事物的細微動態,從人生的試煉與痛苦延伸出精緻且感人的敘事,以擴大她的作品世界,長久以來深受讀者與評論界關注。
《請照顧我媽媽》在台灣出版後,深深打動三萬多名讀者。吳念真導演也感動表示,申京淑特有的細膩,有如一面鏡子,彷彿可以看到自己的故事。
在最新的長篇小說《我們不要忘記今天》,申京淑想對讀者說:「在通過人生的某時期我們會遇到充實感不足感,也會遇到無法安撫的不安與孤獨的許多個時刻,我希望這部小說能成為撫摸這些時刻的手,能成為渴望被抓住的手。」
獲獎紀錄
1985 《冬季寓言》榮獲「文藝中央新人文學獎」
1993 《風琴曾經在那兒》榮獲韓國日報文學獎、文化部當代青年藝術家獎
1995 《深深的憂傷》榮獲現代文學獎
1996 《單人房》榮獲萬海文學獎
1997 榮獲第28屆東仁文學獎
2000 榮獲第5屆二十一世紀文學獎
2001 榮獲第25屆李箱文學獎
2006 榮獲吳永壽文學獎
2007 榮獲美國作家協會翻譯基金會獎金
2009《單人房》於法國翻譯出版,榮獲法國Prix de l’Inaperu
2010《請照顧我媽媽》創下韓國史上兩百萬本空前紀錄
票選為韓國年度代表作家,譽為「韓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墊腳石」
受邀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2011《請照顧我媽媽》於全球34個國家出版
攻占紐約時報、美國亞馬遜書店排行榜
榮獲台灣誠品、博客來、金石堂年度十大小說
2012亞洲文學最高榮譽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公布2011年得主,
申京淑擊敗呼聲頗高的吉本芭娜娜,
成為第一位獲獎的女性作家。
譯者簡介:
政治大學韓文系畢業,韓國漢陽大學教育碩士學位,現任銘傳大學推廣教育與林口社區大學的講師。譯作:《我們的幸福時光》《你看見我愛你嗎》《小豌豆》《愛淘氣-Yiso愛的故事》《原來是美男電視小說》等,超過六十本的譯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 申京淑小說的文句雖然看似輕柔的雪花,但到了小說末尾,卻像能夠吞噬整棟房屋的雪崩般,撼動讀者的心。(黃鍾淵,文學評論家)
* 申京淑的小說讓人感到痛,讓人想到保羅.策蘭的「世界已經走遠,我必須背你前行」。自己的生命、同儕的死亡、甚至共同體的命運,都必須一肩扛起的時代的「克利斯朵夫」原來就在這裡!這裡的四名年輕人的青春裝在玻璃瓶的信,將飄流到今日年輕人的心。要記取痛苦,但不要重返到那些痛苦時光,最終,要邁向沒有痛苦的時光。 (申亨哲,文學評論家)
* 這是一本很快引起我共鳴,一本包含友情、愛情、親情,一本倒影當年韓國民主化運動遊行動盪,一本關乎愛情與友情之間產生的複雜感情。雖然,才看到一半,但她真的吸引了我,彷彿看到自己的青春。獨特的敘述技巧令人讚嘆。(讀者,瑤瑤)
* 申京淑最擅長書寫孤獨的個體,敏感內向的人物吞嚥著小小的細節,試圖從陌生的環境中創造出獨屬自己的世界。這故事寫得最好的就是主角獨自行走的部分,她看到首爾裡的小小溫情,並認為這就是自己存在的證明,雖然故鄉回不去,但總能找到一點支撐。這是她所有作品的共同母題。(讀者,鹿鳴之什)
* 就是好!申京淑是個人特色相當鮮明的作者,的確是水準之作啊!那樣遮遮掩掩的自言自語,你卻輕而易舉就能跟上,或不知不覺沉陷下去。作者的小說總有她的經歷和情感,但透過文字呈現的卻是大大的世界,厲害。讀她的書總心緒滿滿但無處可去。(讀者,Make it right)
名人推薦:【名人推薦】
* 申京淑小說的文句雖然看似輕柔的雪花,但到了小說末尾,卻像能夠吞噬整棟房屋的雪崩般,撼動讀者的心。(黃鍾淵,文學評論家)
* 申京淑的小說讓人感到痛,讓人想到保羅.策蘭的「世界已經走遠,我必須背你前行」。自己的生命、同儕的死亡、甚至共同體的命運,都必須一肩扛起的時代的「克利斯朵夫」原來就在這裡!這裡的四名年輕人的青春裝在玻璃瓶的信,將飄流到今日年輕人的心。要記取痛苦,但不要重返到那些痛苦時光,最終,要邁向沒有痛苦的時光。 (申亨哲,文學評論家)
* 這是一本很快引起我共鳴,...
章節試閱
1. 我.去.找.妳.好.嗎?
八年來第一次接到他打來的電話。
我很快認出是他的聲音。電話那頭,他「喂∼」才剛講完,我立刻問「你在哪裡?」但他沉默不語。八年,並非短暫歲月。若以小時為單位換算,會算出難以想像的數字。雖說是八年來第一次接他電話,但我們的關係早在八年前便淡薄了。那次是為了什麼而和大家聚會的,現在已忘了,但記得當時兩人只望著不同的方向,直到回家道別時才靜靜地牽了手,然後放手。僅止於此。
地點是在哪裡,我已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午夜過後,在這城市靜僻的某個陡峭階梯前方。走向前牽手的人是我。附近似乎有水果店,像李子被咬開時散發的味道瀰漫於悶熱空氣之中。我之所以牽手然後放手,其實是代替道離別。不管他當時有何想法,我想對他說的話,如一顆顆珍珠粒般留在心中,說不出口。我無法開口說「好走」或「再見」。要是開了口,我怕自己會如同串線的珠子,在線斷的瞬間全部咚咚落地。只要說了一句,接著就會一古腦兒地湧出已經失去時效的話語。由於我們當時的感情正在擴張與深化,所以只要引爆開來,怕會變得無法控制。因為這樣的想法,我雖心緒雜亂,卻只在臉上裝出淡淡表情。我不想再多說什麼,不想讓我們曾經互相尋找、彼此依靠的那段日子變得混亂。
八年前或現在都一樣,時間對誰皆公平,不會只有流逝而已。八年來第一次接到他的電話,在問他「你在哪裡」的瞬間,我醒悟到自己內心已無堆積想說卻說不出口的話。所以也無須刻意表現出想隱藏留存的激烈感情而假裝自己過得很好。我發現自己是真的平靜,淡淡地問著「你在哪裡」。過去滿懷的疑問與悲傷,現在都到哪裡了?難過的心情,以及獨處時像獵人用獵槍指著我心的悲痛,竟都悄悄散去了。難道我已經淡忘了嗎?難道這就是人生嗎?當時間一刻不停地流逝時,令人惋惜但也幸運的,難道是因為我們都會淡忘嗎?在我們受困於漩渦之中出不去的時候,如某人所說的「現在過去之後,將又有其他不同的時刻來臨」這句話終將被證明。是的,「度過此時此刻」是對那些身處於最苦難時刻的人,或者身處於最自滿時刻的人,最適合的一句話。對某些人而言,這句話賜予了忍耐的力量;對某些人而言,這句話賜予了謙遜的力量。
隔著電話,我和他之間突如其來的沉默持續加長。後來我才想到順序似乎顛倒了,怎麼連短短一句問候語也沒有?怪了,竟連「好久不見了」「過得好嗎?」的問候也尷尬得難以啟口。省略了問候,對於這八年來第一次聽到的他的聲音,我貿然就問「你在哪裡」,可想而知一定令他很吃驚吧。但我還是連句問候也沒說,一接電話就問「你在哪裡」,像經常在連絡的熟識關係才脫口而出的話。然而,我和他八年不見,他在電話那頭,我在電話這頭。時光不停湧向我們,但如果我在年輕時能體認,同樣的日子不會重現,說不定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那麼,那個人也許就不用告別,那個人可能還活著。如果年輕時能知道「一切結束的那一刻,同時也會有新的開始」,事情就不會演變成那樣了。
我將視線移至窗邊。
在我們持續沉默的這段時間裡,冬天早晨的陽光從窗外透了進來。昨晚天氣預報說今天會下雪,但看樣子不像在下雪。此時猶可見到破曉時的曦光,這麼大清早的,若非家人或熟識的朋友,怎麼會打電話來。這種時候的電話通常是為了急事或告知壞消息。
「尹教授住院了。」
「⋯⋯」
「我想我該告訴妳。」
聽到這,我雙手握住話筒,一時無話可說,只能眨著眼睛,然後轉頭不再看窗外。我想我該告訴妳。這些字彷彿雪花般在我眼前飄下來。我再三細嚼這幾個字音,像要抓住他說的話似地,稍微睜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百葉窗外出現雪的蹤影了。
「好像已經住院三個月。」
「⋯⋯」
「可能該做準備了。」
窗外正飄著片片白雪。
聽到這消息並不意外,因為我一直不安地揣測著有一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就是今天了。一開始,雪花一片兩片,還能數得了,但我站在窗邊之後便開始越下越大。鄰居屋前種的喜馬拉雅雪松,今年入冬以來一直還綠油油,如今枝頭也慢慢積上白雪。外面無人走動,只瞧見我住了四年也不曾搭過的鄰里小型公車,慢慢在雪地滑行,正要轉到巷口外。
最近常常莫名其妙忘東忘西,昨天的事經常感覺像十年前。有時急急忙忙去開冰箱,卻忘記要拿什麼,被裡面冒出的冷空氣迎面吹了一陣後,只能默默關上門。然而,很久以前與尹教授初次見面的情景卻仍歷歷在目。當時我二十歲。想當年,光是一本書的書名,我就能輕易聯想到相關的二十本書書名。還記得,當時是三月,陽光普照的教室,尹教授走了進來。他從我身旁走過時,我正低頭坐在座位上。我的眼睛繼續追著鞋跟一直看。感覺因為皮鞋過大,他穿起來顯得鬆垮垮,簡直不像他自己的鞋。穿著比自己腳更大雙鞋的人是何長相呢?好奇心使我抬頭看,但立刻變得愕然。怎麼會有人瘦成這個樣子?原來不是鞋大的關係,而是因為這世上任何鞋子大概都不適合尹教授穿吧。皮包骨,無疑是給他用的形容詞。
掃過尹教授的削瘦身體,往上找到了他的眼睛,眼鏡底下的眼睛銳利地發光著。那雙眼睛很快移向窗外。學校集會場傳來的示威高喊聲實在大到難以正常上課。集會場的空氣混合催淚瓦斯,乘著三月依然寒冷的風不斷滲入教室,上課前已經有人流著眼淚連忙關上窗戶。尹教授站在窗邊一直注視集會場方向,注視了很久很久。時間一久,我們也紛紛聚到窗邊。可以看到一群學生正被驅趕到某處。風寒三月天的白雲在那群學生頭上緩緩飄盪。那天,尹教授對我們說的話只有一句:「在這個時代,藝術能做什麼?」雖然不知這是對學生們說的,還是在自言自語,但我看到他銳利的眼睛滿是痛苦。盯著他眼睛的瞬間,我的心也突然掠過一絲像被某個尖銳物品刺到的疼痛。當時,怎麼可能料想到我們會面臨像今天這樣的時刻?也沒料想到,那一天被刺到的疼痛即使過了這麼久,仍留在我心裡。即使是與他共同相處的時光褪色變淡,尹教授的眼睛偶爾還是會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每當這樣,與當時一樣的疼痛隨之襲來。那疼痛像切成一模一樣的四角形方塊,無數個坎在我心裡,不時還會蹦跳出來,反覆問我相同的話:
現在,在做什麼?
二十歲時,只要心裡有「現在在做什麼」的疑問,我會走出學校,在這城市不停行走,一邊被空氣中混合的催淚瓦斯嗆得流淚,一邊無止盡地走著。那個時候與現在都一樣,這個世界似乎毫無改變之處。我只要想到那雙眼睛,就會走出家門,隨便走條路,一直走到路的盡頭。不論是我或這個社會,感覺上都沒有變得更好,而是變得不同模樣的不完整。看到新聞報導,橫亙這城市的江河上的一座大橋崩塌,滿載正要上學的女學生的巴士掉落到江河裡,還有某天早晨目睹電視裡飛機直接衝撞華爾街高樓建築物的畫面,以及新年第一天在電視機前緊盯十幾個小時,難以置信地目睹大火吞噬整個崇禮門十幾個小時。看到這些新聞時,和以前同樣的疑問隨之浮現:「現在在做什麼?」某個深夜裡,我拿了汽車鑰匙就出門,一直繞著已經被燒得不留痕跡的崇禮門四周,直到想回家為止。每當想跪下來的時候,不管是以前或現在都一樣,我會在這城市裡不停行走。而憂鬱與孤獨時,都想著同樣的事:多希望他能一直陪著我。
我和他,是誰先放手的?
好像是在某個時間點吧,我已然接受離開他的事實。雖然不安、擔憂,但還是想決心一個人開始過沒有他的日子。可是在那之後很久一段時間,仍然常會想到曾經緊抓住他不放的每個情景。在某個島嶼漁村共度的那個夜晚,我們走了一整夜,偶爾還下起傾盆大雨。我們是從仁川搭船出海的,但那個島嶼漁村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記得我們是臨時起意,也還記得我們在首爾站不知為了什麼事搭了地鐵一號線。雖然提到地鐵一號線,但其實沒特別意義,因為印象曾經過富川站,所以記得那是地鐵一號線。好像是在七月,但說不定是六月吧,或者八月。因為印象中他穿短袖白襯衫,才猜是那個季節。地鐵列車裡擠滿了人,站都快站不穩。那天我為了某事,疲憊得一點兒也不想說話。每當列車停下來,便有許多人帶著汗味湧進列車。我對著一邊皺眉頭一邊站得搖搖晃晃的他,說道:「我們去遠一點的地方走走。」又好像是他提議的?記不太清楚了。我們在仁川站下了地鐵後,搭了開往沿岸碼頭的公車。不管去哪個島都好,反正我們只想去離港口最遠的地方。船隻載著我們航行於海面上。站在船頭迎著海風時,就連原本令我疲憊的某件事,也變得沒什麼了。兩個人一直凝視著大海。我第一次出海到這麼遠的地方,而他則是在海邊城鎮長大的,和我不一樣。那座島嶼並不容易到達,航行兩小時後靠近島嶼時,正值漲潮,無法直接靠岸。島嶼碼頭有人駕著搖槳小船出來接我們,必須靠搖槳小船才能上岸。坐在小船裡望去,岸邊有些孩子泡在深深的海水裡釣魚,彷彿隨時會被海浪捲走。不過,有人看見我的不安表情,便對我說:「孩子們並不是進到海水裡,而是站在堤岸上。」還說:「等潮水退了就知道,孩子們站的位置是堤岸。」搖槳小船讓我們下去的地方也是浸在水中的堤岸。我挽起裙子,他則是把褲管捲到大腿,然後走海水中的堤岸道路,這才上岸。
那天,兩個人沿著海岸線無止盡地走著。可能還是梅雨季的關係吧,坐在海邊不下水的人比下水玩的人更多,而且離碼頭越遠,海邊遊客越少。海風吹來,夾雜著鹽味。海風讓海岸上的樹林偶爾劇烈地搖晃著。我們並肩站在海邊,注視火紅的太陽直落海水的景致,然後相互擁著對方的肩膀。太陽下山只在瞬間,火紅太陽在一眨眼間便已消失在大海。看完日落,不知為何,他一臉憂鬱,原本很想對鬱鬱寡歡的我說什麼話的他變得沉默。我也開始安靜不語。就這樣,我們沿著海邊走了又走,直到發現一隻被海水沖來的死海鷗。
「是鳥!」
看著被潮水擱淺在濕沙子上的海鷗死屍,我喃喃說道。隨即,他挖了一個很深的沙坑,將海鷗就地埋了。
「有什麼用?還是會被海水沖走的。」
「儘管如此,也要埋!」
想到他說的「儘管如此」,我不禁嘴角泛起了微笑。曾有段時間,只要一想到他,就不由得聯想到「儘管如此」這四個字。不管什麼情況下,他總是說:「儘管如此,還是要做!」他從背包裡拿出筆記本,撕了一張,寫上「鳥啊,早日復活吧」,然後綁在木棍上,再將木棍插在這鳥的墳前。那天我們是否吃了晚餐?已不記得了。不記得吃了什麼,也不記得餓過。我們彷彿想知道海的盡頭在何處似地,踩著沙子走了很久很久,直到黑暗湧入島嶼。當時我第一次實際目睹到,島嶼在黑暗之中海水會變黑。黑色的水越過黑色水,又再越過黑色水,浪花撲到我們的腳之後退去,撲來又再退去。
「鄭⋯⋯潤!」
過了一會兒,他呼喚我的名字。通常他連名帶姓叫我,表示他正處於思緒繁亂的時候。
「嗯?」
「我們要永遠記得今天。」
黑色浪花一個個撲打過來,也一個個退下去。
「不要忘記今天。」
叫我不要忘記?我覺得這樣還不夠,於是像自言自語地說:「想不忘記,應該要有定情之物吧。」隨即,黑暗中沙沙作響,他從背包裡掏出了筆記本,放到我手上。
「我將這取名為褐色筆記本,每次想到什麼,就會隨手寫下來。這筆記本給妳。」
他抓住我的手腕,我突然被他一把抱住。他拉著我的手去摸他褲子中間的部位,說道:「這個我也能給。」看他一臉嚴肅,我不禁噗哧笑了出來。就這樣,一手拿著他給的筆記本,另一手放在他褲襠,我心裡盡是莫名的哀愁。接著我在他耳邊細語:「沒有比這裡更遠的地方嗎?」當時我並非不知道那島嶼已是我們能去的最遠地方。
對於未曾經歷的未來,有誰能預測?
未來如潮水般湧來時,我們只能懷抱著記憶繼續往新的時間走去。記憶,它的特性就是只記得自己想記的部分。能喚起記憶的物像混雜在我們生活之中,卻不能拿著自己或某人的記憶強迫別人當成發生的事情去相信。若有人過度強調是他本人親眼見到的,我會認為那人發言時已參雜了自己的希望,已蘊含了希望可以如此的心願。即使記憶並不完美,在面對某些記憶時,還是會掩臉靜靜流淚。特別因為下意識覺得無法適應而徘徊不前,那種記憶更令人難過。為何每天早晨難以睜開眼睛?為何害怕和別人交際?到底該如何穿越這些障礙我們才能相遇呢?
二十歲的我每天早晨都會注視校門,猶豫是否要進學校,然後總是朝著學校的下山路往回走下去。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那時的心情。我十九歲的最後幾個月到二十歲初,都是在剛新婚的表姊家度過的。在她新婚屋裡的角落房間窗戶上,我貼了黑色圖畫紙。雖然只是一張紙,卻讓房裡白天也和夜晚一樣黑漆漆的。在黑暗中開著燈,不管夜晚或白天都以閱讀度日。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除了閱讀,我沒其他能做或想做的事情。一套文學全集,每一本收錄超過二十篇密密麻麻小字的短篇小說,我按照順序讀完六十本的時候,窗外已是三月天。現在想來,也覺得不可思議。新婚屋裡,我竟然把房間弄得像黑夜一樣暗,而我走出那房間,是為了參加大學的新生入學典禮。初到這城市時,就是從那麼自由的空間開始生活的。如今,尹教授人在醫院,過著和我不相干的生活。還有另一個人,永遠無法見到了。如果當初不曾遇見他們,我的日子又會是如何呢?
我望著越來越大的雪花,整理思緒,並且提醒自己,他在八年後第一次打電話來是為了告知尹教授臨終的事情。「別想太多⋯⋯」心裡喃喃告訴自己。然後再次提醒自己:「現在應該先去醫院。」雖然我們不自覺,但總有無數的人在相同的時間裡互相連結與交會。如同下雨過後,將馬鈴薯莖往上一拉,成串的馬鈴薯便會跟著被拉出泥土。被遺忘的事一一從深淵裡湧出,使我無法動彈。這八年來已經遺忘的,以及無法相見的,在這一刻都被連結了,竟讓人悲從中來。
打破沉默的是他。聽完他轉達尹教授的消息,我面對他的聲音實在難以開口,只是手持著電話。他問我:「我去找妳好嗎?」
在這個時間?
原以為和他之間一切結束了,他卻太過自然地問著:「我去找妳好嗎?」已經好久不曾聽到的這句話,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常在電話那頭說的話。「我去找妳好嗎?」還有,他在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我時,也說過這句:「我正要去找妳。」不論是下雨的日子、颳風的日子、陰天、晴天,常在他的話中出現這兩句。那時候的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等著彼此。時間再晚,或比今天更早的時間,他也會來找我,不然我也會立刻去找他。那時候的我們總是向對方說「快點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一無二,而且只有一次。所有人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朝向不同的世界去前進、去愛、去陷入悲傷,以及在死亡面前失去親近的人。我、此刻躺在醫院的尹教授、八年來第一次打電話來的他,以及其他每個人都一樣,無人例外。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是的。如果青春不是只有一次,那麼今天我就不會站在這裡,聽著書桌上的電話響起,然後在八年後又聽到他的聲音。
猶豫片刻後,我拒絕了,對他說:「不了⋯⋯我知道該怎麼做。」
他在電話那頭深深嘆了一口氣,便掛斷電話。
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對他說的話竟讓自己陷入孤獨。這句話雖是我說出口的,對我卻很陌生。其實只要說「在醫院見吧」就好,但我卻說「我知道該怎麼做」,傷了對方的心。這是很久以前他說過的話。那時我們已不再那麼清楚彼此的狀況,為了一件現在早已記不得的事情,我問他該怎麼辦,他卻回答「我知道該怎麼做」。記憶,好像也會讓自己不自覺地捧起匕首。我明明沒有一直牢記他這句話,但就在快要讓人遺忘的長久歲月過後,無意識地瞬間說出來。我其實不是那種會說「我知道該怎麼做」的人。當我覺得跟某人熟識,但那人卻說「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做」,會讓我從此不再靠近此人,我是這樣的個性。經過這麼多年之後,這句話如同遺失的拼圖般,在我心裡徘徊了一陣,剛才透過我的嘴巴傳到了他的耳邊。
「我應該去醫院。」雖然這麼想,卻整個早上沉坐在椅子裡無法起身。儘管坐著,卻像浮在半空中。浮游狀態下,精神恍惚了一陣。直到接近中午,才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望著桌面。沒讀完的詩集書本都亂放著,列印出來之後尚未修改完的一疊紙張,底下壓著隨手記下的一堆便條紙。還有我在巴塞隆納的哥德區畢卡索美術館所買的筆筒裡歪斜插著兩枝鉛筆。我凝視筆筒側面雕刻的鴿子刁著樹葉的嘴喙,過了一會兒,便開始整理我凌亂的桌面。首先,將那些攤開的詩集書本一一闔上,散放的文具也都歸位到筆筒。接著,我將畫有底線的廢紙都揉成團,扔進垃圾桶。然後,壓在讀到一半的厚書上的文鎮被我全部拿了起來,整齊堆放在一起之後,書本則是放回書架原有的位置。把桌面整理好,令我聯想到死亡。曾有一次,我整理好書桌正要出門,打開門,回頭看房間,卻不禁打了個冷顫,於是我又再回到書桌前,把桌面弄亂才出門。生與死的意義,在愛一個人時會特別深刻體會。但這並非與年紀成正比,也不是歲月累積就更能體會的事。
像我,現在反而比年輕時候更不敢為愛而活,要是聽到突如其來的死亡消息,每次都會驚慌失措。如果我死,我希望就在這張書桌前死掉,在某個下雪的早晨,在這裡寫字或讀書到一半時趴在桌上,闔眼辭世。我希望那是我最後的模樣。一邊整理書,一邊盡力驅趕指尖觸碰書本時感受的死亡氣息。好不容易終於將桌面收拾乾淨。去醫院前,我用香皂洗手洗了好幾次,也盥洗了一番,換上乾淨的衣服,照了鏡子。打開房門正要出去的時候,不自覺回頭看書桌。
這時電話鈴聲像在等著我似地,剛好響起了。
1. 我.去.找.妳.好.嗎?
八年來第一次接到他打來的電話。
我很快認出是他的聲音。電話那頭,他「喂∼」才剛講完,我立刻問「你在哪裡?」但他沉默不語。八年,並非短暫歲月。若以小時為單位換算,會算出難以想像的數字。雖說是八年來第一次接他電話,但我們的關係早在八年前便淡薄了。那次是為了什麼而和大家聚會的,現在已忘了,但記得當時兩人只望著不同的方向,直到回家道別時才靜靜地牽了手,然後放手。僅止於此。
地點是在哪裡,我已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午夜過後,在這城市靜僻的某個陡峭階梯前方。走向前牽手的...
作者序
【序】
作者的話
清晨陽光從四方透射進來,好耀眼。
第七本長篇小說交出去了。
這部作品是以六個月連載的原稿為初稿,在上個冬季重新再寫。不僅僅上個冬季,就連上個春季和這個初夏也在寫⋯⋯不,連剛剛也在持續寫著。可能到印刷前一刻也寫,說不定書出版後也寫。我甚至覺得十年後⋯⋯二十年後也會繼續寫這作品。
去年初夏連載,寫第一句之前,我曾做了以下的承諾。
我要清晨三點起床,坐在書桌前寫作,直到早上九點為止。去瑜伽教室回來後,做午餐,和家人吃飯之後,可能稍微睡一會兒,也可能讀點書。偶爾出去和人見見面,可以聊到深夜,還不想道別時,就再聊天或去走走。即使在那種生活之中,也要盡量早一點吃晚飯,早一點睡覺,然後清晨三點起床,過著規律且單純的生活。這段期間,小說應該就會完成了。我要寫一部如同很多時鐘同時發出鳴響的那種愛情故事。如果說青少年期是在安德烈.紀德或赫塞的陪伴下度過的人,九○年代以後大概都是日本作家的小說在代言青少年期的愛情熱病與成長痛。看到這種現象,我感到很遺憾。身為韓語作家,我多麼希望能出現以我們語言寫作出的,美麗且具品格的青春小說。我不知道自己現在想寫的小說是否可以成為那樣的小說,但我已盡最大努力,我試著貼近現在的年輕人,就像窺視他們的筆記本似地貼近他們的心靈。趁現在還來得及,我要趕快寫。不過,也不能只是很青春。在通過人生的某時期,我們會遇到充實感與不足感,也會遇到無法安撫的不安與許多孤獨的時刻,我希望這部小說能成為撫摸這些時刻的手,能成為渴望被抓住的手。我也希望這部小說能在歲月流逝之後,仍被找出來閱讀,而且還能感動人心,就像在某一天某個地方突然響起的電話鈴聲,依然能震動心靈。巴哈說過,親近的人即使遠離彼此也不會惡言相向。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說過,我為陷入悲傷的人們演奏。我內心對這部小說的企盼也是如此。希望能被讀出送親人好友遠離的那種心情,也希望能傳達安慰陷入悲傷者的那種心情。
然後,還有什麼呢?
我認為文學作品是和療癒喪失分不開的。寫這作品的過程之中,有不少時候我都在接受喪失。我希望我的寫作有人閱讀,並因而得到治療與恢復,然而時間一旦過去是不復返的,正如落水的花瓣順著流水飄走,能夠不緊抓住而送走的心,也許才是治癒吧。就好像送走春天迎夏天,在這過程之中,就會有文學上的「什麼」發生。至於是發生了什麼,就連寫這部小說的我在完成時也不知道。不久前的義大利強震,有位老奶奶被埋在廢墟三十小時織毛線等待救援,那位老奶奶的模樣說不定會令人感到有「什麼」。還有,之前新聞報導一對年僅二十出頭的訂婚男女相擁著自殺身亡的事件,說不定會令人感到有「什麼」。不管寫作時歷經何種過程,我希望完成後的作品能給予寫作的我與閱讀的你們帶來小小的治癒與成長的時光。為了這些希望,我承諾要從清晨三點專心寫到早上九點。寫作對我而言是行動與過往時間的證言。想一想,如果哪天你在清晨醒了,說不定在這世界某地寫作的我也醒著,那麼那一瞬間我們就是一起醒著。
遵守承諾了,所以這部小說是我從清晨三點專心寫到早上九點的作品。小說裡的主角們,走在清晨街頭尋找彼此,或者看著清晨的雨,或者聽著清晨的雨聲,在清晨接了某個地方打來的電話,會有這麼多清晨的場景,或許也是受了寫作時間的影響吧。現在我發現,寫這篇作者的話,此時此刻也剛好是清晨。
雖然我已預告這是個如同很多時鐘同時發出鳴響的那種愛情故事。但我覺得有愛情,也會有死亡,所以不斷寫到死亡。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參考了一些應該以震驚與酸楚的心情來哀悼的連續重大死亡事件,死亡慘狀跟著來到了我的書桌前⋯⋯曾經跟我很親近的幾個人,因為無從預料的事突然就永別了,在我內心留下傷痛,可能因為這樣,所以引領我寫作到那個方向。不管是因為什麼,我快結束作品時,有一陣子我的半邊臉與半邊肩膀很痛,好像被什麼擦傷的痛,痛到我暫時遠離這部作品。我無法再看下去。然後過了一段時間,某天清晨⋯⋯我靜靜拉出原稿,放在書桌上,將傾斜一邊的作品開始復原。為了避免讓這部作品成為死亡故事而非愛情故事,我寫進了因為認識某人而喜悅的情節。還有,不想清醒的那些美夢、旅途中擦肩而過的難忘風景、廣場上人們的熱情、孩子們讓你渴望伸手觸摸的漂亮臉頰,當然還有與我同時代的年輕讀者們的呼吸聲與他們繁衍出的美麗。我衷心希望,用如同星星般的我的母語來載裝這些餘韻,將這部作品牽引到愛的方向。
然後,這部小說才終於成就出這個樣子。
對於歷經愛情的喜悅或喪失的痛苦而一步步走向世界的年輕讀者們,我將信號發射向他們,雖然不知道信號最終會到達什麼地方,但是,愛一個人的那顆心會穿越憂鬱的社會風景和時間,讓彼此擁有永不遺忘的情景⋯⋯我在詩人崔勝子的《不停地找我的電話鈴聲響起》之中找到了這部作品的書名(編註:原書名為《哪裡傳來找我的電話鈴聲》)。我盡可能不讓現代電子產品登上這部作品,排除非心靈的溝通工具,讓潤、丹、美縷和明瑞四人的青春用走的,用寫的,用讀的方式呈現。即使風俗改變,時間流逝,我認為行走、寫作和閱讀仍是身為人的條件根源。主角在書裡,我在書外,我們都在寫作。寫著未來的故事,寫到手臂顫抖,有好幾次突然振奮起身。寫丹的故事時寫到青年的憂愁,我難過地突然遊走街頭。沒有寫作的早晨,餐桌上擺滿那些失蹤者和不明死亡者的紀錄,讀到一半我突然用手摀住臉龐,暗暗哀悼。⋯⋯還有,書裡的主角們以及寫作的我,有時會突然激動而振奮起身,這些突然來臨的每個時刻,我都要放在這裡,從現在起,我將邁向其他的時光之中。
希望在這部小說你能體會到,踩著悲傷去接近愛的人的那顆心。希望你能走向樂觀而非悲觀的方向。這部小說之中經常出現的「以後有一天」,是載著許多未來夢想的,我希望閱讀到這些夢想的你,心中有清晨陽光,耀眼閃爍⋯⋯
二○一○年五月
申京淑
【序】
作者的話
清晨陽光從四方透射進來,好耀眼。
第七本長篇小說交出去了。
這部作品是以六個月連載的原稿為初稿,在上個冬季重新再寫。不僅僅上個冬季,就連上個春季和這個初夏也在寫⋯⋯不,連剛剛也在持續寫著。可能到印刷前一刻也寫,說不定書出版後也寫。我甚至覺得十年後⋯⋯二十年後也會繼續寫這作品。
去年初夏連載,寫第一句之前,我曾做了以下的承諾。
我要清晨三點起床,坐在書桌前寫作,直到早上九點為止。去瑜伽教室回來後,做午餐,和家人吃飯之後,可能稍微睡一會兒,也可能讀點書。偶爾出去和人見見面,可以聊到深夜...
目錄
序曲 我.去.找.妳.好.嗎?
1• 離別
2• 渡河人
3• 我.們.呼.•吸
4• 前往鹽湖的路
5• 一起同行
6• 空房子
7• 樓梯底下的房間
8• 一艘小船
9• 擁抱一百個陌生人
10• 我們在火中
尾聲 我.去.找.你
作者的話
序曲 我.去.找.妳.好.嗎?
1• 離別
2• 渡河人
3• 我.們.呼.•吸
4• 前往鹽湖的路
5• 一起同行
6• 空房子
7• 樓梯底下的房間
8• 一艘小船
9• 擁抱一百個陌生人
10• 我們在火中
尾聲 我.去.找.你
作者的話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