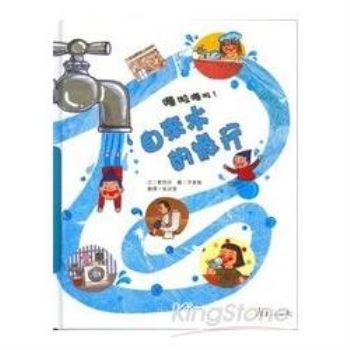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3 項符合
Lidia Yuknavitch的圖書 |
 |
$ 363 電子書 | The Book of Joan
作者:Lidia Yuknavitch 出版社:HarperCollins 出版日期:2017-04-18 語言:英文 |
 |
$ 363 電子書 | The Small Backs of Children
作者:Lidia Yuknavitch 出版社:HarperCollins 出版日期:2015-07-07 語言:英文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124 ~ 380 | 流年似水:一部關於愛、性與傷痕的回憶錄【外版書】
作者:莉狄亞‧約克納維契(Lidia Yuknavitch) 出版社:時報文化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