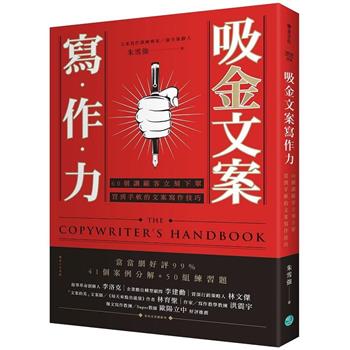從歷史的角度來說
脫離了對形上學的敵視狀態
從內容上來說
深度探討了我們看待這個世界時所持有的思想結構
《個體論》一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何以「物體」與「個人」的概念是我們思想結構中極為核心的概念。第二部分則說明這樣的思想結構如何反映在我們談論這個世界的語言中。作者彼得‧弗列得瑞克‧史陶生從常識出發,但卻對常識看法所涉及的各種複雜面向作出極為深刻的省思,這樣的深刻省思無疑是分析哲學的極佳範例。
第一部分「殊相」(particulars)旨在建立起物質性物體和個人在一般殊相中所占據的中心地位。共分成四章。第一章從殊相的識別(identification)和再識別(reidentification)說起,並藉此給出一些概括性的論證,以論證具有空間與時間性的物質性物體是基本的殊相。第二章藉著探索一個純粹聽覺世界的可能性,而企圖去回答下面這一個問題:是否任何一個包含了客觀殊相在其中的概念架構,都必須以物質性的物體作為基本的殊相呢?該章的結論雖然是相當不確定的,但它卻引導到了下一章中的主題。第三章論證說,在我們實際的概念架構中,個人的概念是一個初基性的概念;而將意識狀態歸給自己的一個必要條件則是:我們必須同時也預備將它們歸屬給其他的人。這一個看法的一個結果是:有關於其他心靈的懷疑論根本無由產生。至此,史陶生建立起了他在第一部分中想要建立的主要主張。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則旨在對照史陶生自己的理論與萊布尼茲(G. Leibniz)的學說,並藉著探索這個對照而對後者作出進一步的闡釋與批評。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旨在於建立、並解釋一般性的殊相的觀念與指稱對象或邏輯主詞的觀念之間的關聯。傳統上,殊相與非殊相之間的區分被認為是以下述不對稱的方式關聯於主詞(subject)與述詞(predicate)之間的區分:殊相只能作為命題的主詞,而不能作為命題的述詞;而非殊相則既能作為命題的主詞,也能作為命題的述詞。史陶生在這一部分想要建立起來的看法主要有二。首先是有關於於主詞與述詞之間實際區分的理據,而這個理據要能夠說明上述這個傳統的看法:「殊相只能作為命題的主詞,而不能作為命題的述詞;而非殊相則既能作為命題的主詞,也能作為命題的述詞。」史陶生認為,該區分可以在某種「完整性」與不完整性觀念的對照裡找到。其次,根據這個被提議的主述區分,殊相是邏輯主詞的典範,但根據類比而來的、對此區分的延伸,殊相和非殊相都同樣可以被說成是一個命題的主詞,因而都是個體。這一部分同樣分成四章。第五章說明了兩種主述詞區分的標準,以及這兩種標準之間的關聯。在第六章中,史陶生提出了他認為是這兩種主述區分標準背後的根本理由,而這一章可以說是本書第二部分中最重要的一章。第七章檢視了一個沒有殊相的語言的可能性,以及這種語言所涉及的問題。在最後一章中,史陶生探討了邏輯主詞與存在概念之間的關係,反對對非殊相的化約式企圖,並倡議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類比的延伸下被當作是邏輯主詞,或個體。
延伸閱讀:
中國文學理論
道德底形上學
歌德詩歌:德語抒情詩及藝術歌曲譯注
共善:引導經濟走向社群、環境、永續發展的未來
論語與孔子思想
作者簡介:
彼得‧弗列得瑞克‧史陶生(Sir Peter Fredrick Strawson)
1919-2006,英國當代著名哲學家。1948至1987年任教於牛津大學哲學系,1968年起獲牛津大學韋恩福里特教授(Waynflete Professor)殊榮。1960年獲選英國皇家學院院士,1971年獲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院士,英國王室於1977年封他為爵士。
譯者簡介:
王文方
1961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哲學博士,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長邏輯哲學、數理邏輯、形上學、語言哲學。著有《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2005)、《形上學》(2008)、《語言哲學》(2011)等書以及四十餘篇學術論文。
章節試閱
第一部分 殊相
一、物體
1. 殊相之識別
我們認為這一個世界容納了一些特殊的事物,其中的一部分獨立於我們之外而存在;我們認為這一個世界的歷史是由特殊的事件所構成,而我們或許是、或許不是這些事件當中的一部分;我們認為這些特殊的事物和事件是被囊括在我們日常交談的話題中,認為它們是我們在交談時可以談及的事物。上述這些說法,乃是一些有關於我們思考這一個世界的方式,以及有關於我們概念架構的說法。換一種顯然是較為哲學性的表達方式──雖然不會因而更清楚些──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本體論裡包含了客觀的殊相。但除了殊相以外,我們的本體論裡還可能包含其他事物。
我的部分目標在於:展示我們用以思考特殊事物的概念架構之一般性和結構性的特色。我將從殊相的識別(identification of particulars)開始說起。但目前,我還不急著去概括性地說明我將如何使用「辨識」(identify)這一個詞和它的相關字詞,也不急著去說明我將如何使用「殊相」這一個詞。「殊相」這一個詞,儘管在應用的邊陲上模糊不清,但在哲學的用法裡無疑已經有了一種大家都已經熟悉的核心用法。所以,我目前只需要說:我對該詞的用法並沒有什麼稀奇古怪之處就可以了。比方來說,在我的用法中,歷史的事件、物質性的物體、人們和他們的影子都是殊相,但特質(qualities)、性質(properties)、數目(numbers)和物種(species)則不是;我的這一個用法和大家熟悉的大部分哲學用法並無不同。至於「辨識」、「識別」等這幾個詞,我則有幾個不同但密切相關的用法;我將在介紹它們的時候一併解釋這些用法。
我首先關切的是「殊相的識別」;這一個詞的用法如下。通常,當兩個人在交談的時候,他們當中的一個,也就是說話者,會指稱(refers)或提到某個殊相或其他殊相。而通常,他們當中的另一個,也就是聽話者,知道說話者所談論的事物是哪一個;但有的時候他並不知道。我將如此表達聽話者的這兩種可能:聽話者或許能、或許不能辨識出說話者所指稱的那一個殊相。作為說話者,我們用來指稱殊相的語言表達式包括這樣的詞:它們的標準功能在於能夠讓聽話者在它們被使用的場合中辨識出被指稱的那一個殊相來。這一類的表達式包括了一些專有名稱(proper names)、一些代名詞、一些以定冠詞開始的描述片語,以及上述這些詞的複合詞。當一個說話者使用這樣的一個表達式去指稱一個殊相時,我將說他對某殊相作了一個辨識性的指稱(identifying reference)。當然,當說話者在某一場合對某殊相作了一個辨識性的指稱時,我們並不能因此就推論說:他的聽話者便實際上辨識出了那個殊相。我可能藉著某個名字向你提到某個人,但你卻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不過,當說話者對某殊相作了一個辨識性的指稱,而聽話者因著這個辨識性指稱的力量而辨識出那一個被指稱的殊相時,那麼我將說:說話者不只對那個殊相作了一個辨識性的指稱,他還辨識了那個殊相。所以,我們有聽話者意義下的「辨識」,也有說話者意義下的「辨識」。
作為說話者和聽話者,我們經常能夠辨識出我們言談所涉及的殊相,這件事並不僅僅是一個值得慶幸的巧合而已。某類型的殊相應該可以被我們辨識出,這一點似乎是該類型殊相被包含在我們本體論裡的一個必要條件。畢竟,如果我們宣稱說,我們承認某一特殊事物類型的存在,並且彼此談論這一類型中的成員,但卻限定我們的宣稱說,原則上我們當中沒有人可以讓其他人懂得他在任何時刻所談的到底是這一類中的哪個或哪些成員,那麼,我們這樣的宣稱究竟能有什麼樣的意義呢?這樣的限定似乎會使得該宣稱變得一點用都沒有。這個省思也許會將我們帶到另一個省思。經常,我們對某類型事物中某個殊相的識別,得依賴於我們對於另一類型事物中另一個殊相的識別。因而說話者在指稱某一特定的殊相時,也許得說它是在某類型事物當中唯一的那一個(the)與另一殊相有特定關係的事物。比方來說,他可能指稱某棟房子為「傑克所蓋的那一棟房子」,或指稱某個人為「刺殺亞伯拉罕.林肯的那一個刺客」。在這些情形下,聽話者對第二個殊相的識別依賴於他對第一個殊相的識別。他知道整個的辨識性片語所指稱的殊相為何,因為他知道該片語的部分所指稱的殊相是什麼。對一個殊相的識別經常依賴於對另一個殊相的識別,這個事實本身並沒什麼格外重要的地方,但它暗示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對某類型殊相的識別也許是以一種一般性的方式依賴於對其他類型殊相的識別之上。如果事實的確是如此,那麼,該事實對於探索用來思考殊相的概念架構之一般性結構的學問來說,將有著一定的重要性。比方來說,假設我們研究的結果是:有一殊相之類型β,其中的殊相不可能不藉著另一類型a中之殊相而被辨識出,但a類型中的殊相卻可以不藉著β類型中的殊相而予以辨識出。那麼,我們的概念架構就會有這樣的一個一般性特徵:談論β類型殊相的能力是依賴於談論a類型殊相的能力,但反之則不然。這個事實也可以這樣合理地加以表達:在我們的概念架構中,a類型的殊相比β類型的殊相在本體論上更優先(ontologically prior to),或更根本、或更基本。也許某類型的殊相在其成員的可識別性上依賴於另一類型的殊相這件事,並不太可能像是我們在這裡所暗示的那麼直接和簡單,而這也就是說,一般說來,為了要對某個相對依賴類型的殊相作出辨識性的指稱,我們不可能不提到另一個相對獨立類型的殊相這件事,是不太可能為真的。但我們對於某類型的殊相的識別,仍然有可能是以其他較為間接的方式依賴於對另一類型的殊相的識別之上。
[2] 對聽話者意義下的識別來說,我們有什麼測試的方法呢?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說:聽話者知道了說話者所指稱的殊相呢?首先考慮下面的情形。說話者說了一個他宣稱是事實的故事。該故事這樣開始:「一個男人和一個男孩站在飲水器旁」,接著:「那一個男人(The man)喝了些水」。我們是否可以說:聽話者知道第二句話中的主詞片語所指稱的殊相是哪一個或什麼事物呢?我們或許會說:「是」。因為,對某一特定範圍(range)內的兩個殊相來說,由於「那一個男人」一詞中的描述僅僅適用於其一的緣故,因而該主詞起了區別出被指稱對象的作用。這雖然是一種識別的情形,但只是較弱意義下的識別,我將稱之為是僅僅相對於故事(story-relative)的識別,或更簡單一點,相對性(relative)的識別。因為,它只是相對於某一殊相範圍(包含兩個成員的範圍)所作出來的識別,而該範圍本身則只是被辨識為說話者所談論的殊相的範圍。這也就是說,當聽話者聽到了第二個句子時,他知道說話者所談論的那兩個特殊生物中的哪一個是被指稱的殊相;但缺少了粗體中所說的限定,他就不知道被指稱的特殊生物是什麼了。這裡的識別是在某個說話者所說的特定故事中的識別。它是在他的故事中的識別,而不是在歷史中的識別。
我們需要一個夠嚴格的條件來排除相對性的識別。在上述的例子中,聽話者能夠在說話者所描繪的圖像裡定位出(place)那一個被指稱的殊相來。這意味著:就某一意義來說,他也能夠在他自己對這一個世界的一般性圖像裡定位出該殊相來。因為,他能夠在他自己對這一個世界的一般性圖像中定位出說話者,並因而定位出說話者的圖像。但缺少了哪一個架構,聽話者並不能夠將說話者圖像中的人物在自己對這一個世界的一般性圖像裡定位出來。由於這個緣故,聽話者識別的完整要求條件並沒有被滿足。
第一部分 殊相
一、物體
1. 殊相之識別
我們認為這一個世界容納了一些特殊的事物,其中的一部分獨立於我們之外而存在;我們認為這一個世界的歷史是由特殊的事件所構成,而我們或許是、或許不是這些事件當中的一部分;我們認為這些特殊的事物和事件是被囊括在我們日常交談的話題中,認為它們是我們在交談時可以談及的事物。上述這些說法,乃是一些有關於我們思考這一個世界的方式,以及有關於我們概念架構的說法。換一種顯然是較為哲學性的表達方式──雖然不會因而更清楚些──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本體論裡包含了客觀的殊相。但除了殊...
作者序
歷來的形上學往往是修正性的(revisionary),較少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描述性的形上學以描述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思想的實際結構為滿足,修正性的形上學則關心於製造出更好的結構來。修正性形上學的作品一直是長期令人關注的,而非只是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的插曲而已。由於它們的內容清晰、而其部分洞見又具有強度,這使得它們當中最好的作品在本質上就值得欽羨,並且具有持久的哲學用處。但最後這個好處之所以能夠歸屬給它們,乃是因為有另外一種的形上學,其本身的證成(justification)並不需要概括性研究的證成之外的東西。修正性形上學是為描述性形上學來服務的。無論從其意圖或效果上來說,也許沒有任何現實中的形上學家一直是全然修正性的,或全然描述性的。但我們可以大致這樣區分:笛卡兒(Descartes)、萊布尼茲(Leibniz)和柏克萊(Berkeley)是修正性的形上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和康德(Kant)則是描述性的形上學家。哲學的諷刺者休姆(Hume)比較難以加以定位。他時而在某一方面是修正性的,時而在另一方面是描述性的。
描述性形上學的想法容易遭遇到懷疑的態度。這種形上學與所謂哲學的、邏輯的,或概念上的分析有何不同?它與這些分析在意圖上並無不同,只有在範圍及概括性上有別。由於其目標是在赤裸裸地呈現我們概念結構裡最一般性的特色,因而,描述性形上學比較不能夠像一些在研究範圍上較為局限的、部分概念性的研究一樣將太多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它們在方法上也有別。在一定的程度上,依靠對實際使用字詞作出細密的檢視,這是哲學中最好、也是唯一可靠的方法。但以這種方法所能作出的區分,以及所能建立起來的關聯都不夠概括性,其成果也不足以達到形上學對理解所作出的完整要求。因為,當我們問說,我們是如何使用這個或那個表達式的時候,不管我們的回答在某個層次上多有啟發性,它還是會很容易就假定形上學家想要揭露的結構的一般性成分,而非去揭露它們。形上學家所要追尋的結構並不輕易地展現在語言的表層,它潛藏在這些表層之下。當語言的引導並不能帶領描述性形上學家走到他所想要到達的地方時,他必須放棄他唯一可靠的嚮導。
描述性形上學的想法,可能還會受到另一方向上的攻擊。因為,可能會有人主張說,形上學在本質上乃是概念變遷的工具,是一個用來推動或標示新思想方向或新思想風格的手段。我們的概念當然會改變,這樣的改變雖然主要發生在專業領域,但卻不限於此;而即使是專業領域上的改變,也會影響到日常的思維。當然,形上學一直主要關切的,的確是這裡所暗示的這兩種改變。不過,以這種歷史的風格去思考形上學會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在人類的思想中,有一大塊的核心部分是沒有歷史的──或者說,是沒有記錄在思想史上的;有一些範疇和概念,它們最基本的特性是一點都不改變的。顯然,這些不是最精緻思維裡的專業概念。這些是最不精緻思維中隨處可見的概念,但也是思維最複雜的人類之概念配備中不可避免的核心部分。一個描述性形上學所主要關切的,也就是這些概念、它們之間的關聯,以及它們所共同形成的結構。
形上學有其悠遠卓越的歷史,而其結果是:在描述性形上學中,我們不太可能發現任何新的真理。但這並不是說,描述性形上學的任務曾經,或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在過往,該任務一直被重新執行著。如果沒有任何新的真理可以被發掘,至少我們可以重新發掘舊的真理。因為,雖然描述性形上學的中心主題並不改變,但哲學中用以批判和分析的用語卻經常改變。恆常的關係乃係以不恆常的用語來加以描述,而後者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氣氛,也反映了個別哲學家的思想風格。在他使用他那個年代的語詞去重新思考過其前輩的思想之前,沒有一個哲學家會理解它的前輩的想法;而這也正是諸如康德和亞理斯多德這些大哲學家們的共同特性:他們比其他任何的哲學家都花了更多的功夫來重新思考。
本書只能說部分是、而且適度地是一本描述性形上學的論文。之所以說它僅僅適度地是描述性的,那是因為,雖然書中有些討論的主題是充分概括性的,但我們的討論卻只從一些局限性的、而非全面涵蓋性的觀點來進行;之所以說它僅僅部分是描述性的,那是因為,在第二部分裡所討論的某些邏輯和語言的分類,在相對性上來說也許只有局部的和暫時性的重要性。對於我處理這些分類的方法,我現在可以作出一點概括性的評論。通常大家承認,在分析地去處理某個頗為特定的概念、希望去理解該概念時,尋找一個單一的、嚴格的陳述,以說明該概念在應用上的充分與必要條件的作法,可能不如將它的應用看作是──用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比喻來說──形成一個家族,其成員也許是因為圍繞著某個典範的緣故而被組合起來,而這些成員與典範之間的連結,則是各種直接或間接的邏輯與類比關係。我認為,不論是在企圖去理解普遍性的邏輯與文法結構時,或者是在像知覺哲學或心靈哲學裡處理特定概念分析的時候,這個在理解上的寬容原則都同樣可以被有用地加以引用。
對我而言,將這本書分成兩個部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第一部分旨在建立起物質性物體(material bodies)和個人(persons)在所有殊相中所占據的中心地位。該部分顯示說,在我們實際的概念架構裡,這兩種範疇的殊相是最基本的,或最根本的殊相,而相對於這些概念來說,其他類型的殊相概念,則一定得被看成是次要於這些概念。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旨在建立並解釋一般性的殊相觀念與指稱(reference)對象或邏輯主詞(logical subject)的觀念之間的關聯。這兩種觀念間的連結,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殊相作為典範的邏輯主詞的地位之解釋,可以在某種「完整性」(completeness)的觀念裡找到,而該觀念則在該部分第二章的前半部分中加以闡釋。這個段落是本書第二部分裡的重要段落。然而,這本書的這兩個部分並非彼此獨立的。第一部分中的主張,在第二部分的許多地方被其中的論證所預設,而且在有些地方被其中的論證所延伸,並進一步加以解釋。我懷疑我們是否可能完全理解任何一部分的主要論題,而無需考慮另一部分的主要論題。
歷來的形上學往往是修正性的(revisionary),較少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描述性的形上學以描述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思想的實際結構為滿足,修正性的形上學則關心於製造出更好的結構來。修正性形上學的作品一直是長期令人關注的,而非只是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的插曲而已。由於它們的內容清晰、而其部分洞見又具有強度,這使得它們當中最好的作品在本質上就值得欽羨,並且具有持久的哲學用處。但最後這個好處之所以能夠歸屬給它們,乃是因為有另外一種的形上學,其本身的證成(justification)並不需要概括性研究的證成之外的東西。修正性形...
目錄
導論
第一部分:殊相
一、物體
1. 殊相的識別
2. 再識別
3. 基本殊相
二、聲音
三、個人
四、單子
第二部分:邏輯主詞
五、主詞與述詞(1)——兩個標準
1. 「文法的」標準
2. 範疇的標準
3. 這些標準之間的緊張和密切關係
六、主詞與述詞(2)——邏輯主詞與特殊事物
1. 殊相之被引介到命題中
2. 殊相之被引介到言談中
七、沒有殊相的語言
八、邏輯主詞與存在
結論
附錄A:史陶生爵士生平簡介及著作目錄
附錄B:與《個體論》有關之重要研究文獻提要
索引
導論
第一部分:殊相
一、物體
1. 殊相的識別
2. 再識別
3. 基本殊相
二、聲音
三、個人
四、單子
第二部分:邏輯主詞
五、主詞與述詞(1)——兩個標準
1. 「文法的」標準
2. 範疇的標準
3. 這些標準之間的緊張和密切關係
六、主詞與述詞(2)——邏輯主詞與特殊事物
1. 殊相之被引介到命題中
2. 殊相之被引介到言談中
七、沒有殊相的語言
八、邏輯主詞與存在
結論
附錄A:史陶生爵士生平簡介及著作目錄
附錄B:與《個體論》有關之重要研究文獻提要
索引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