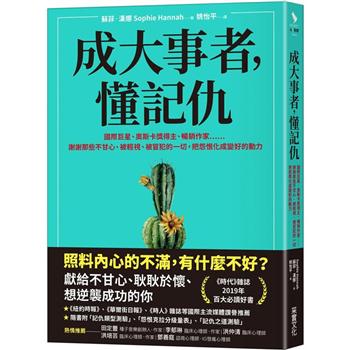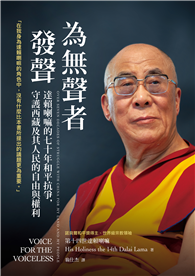本書收錄了三十三首詩作,詩人許萍芬透過這些作品記錄了她對國際局勢、各大事件及社會百態的觀察。新冠疫情結束前後,世界各地頻仍發生的天災人禍,從俄烏戰爭、以巴衝突到摩洛哥地震等事件,都在不同的國家真實上演。詩人長年旅居德國柏林,目睹著許多烏克蘭人在此流亡、工作或學習的種種境況,這些經歷讓她充滿了對世事的思考與感悟。
本詩集由她的母語中文,以及她熟悉已久、充滿藝術氣息的德文與國際共通語言的英文三語共譜,更附上節錄數首詩篇的朗讀QR code,供讀者一同聆聽、欣賞。詩文中多處提及對戰爭和衝突的反思,期待為讀者帶來一場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精神之旅。
本書特色
★本詩集由中、英、德三語共譜,書中更是附上部分詩篇的三語朗讀QR code,供讀者一同聆聽、欣賞。
★詩中多為詩人對國際局勢、各大事件及社會百態的闡發與描繪。多處提及對戰爭和衝突的反思,期待為讀者帶來一場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精神之旅。
各界推薦
廖亦武(2012年德國書商和平獎得主)
「因為只有『失眠的鯊魚』才將暫時迷失嗜血的攻擊本能,這剛巧道出了叢林世界弱肉強食的冷酷本質。」——廖亦武 德國書商和平獎得主(2012)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Ping-Fen HSU的圖書 |
 |
$ 210 ~ 270 | 失眠的鯊魚 Insomniac Shark.Der schlaflose Hai ——許萍芬漢英德三語詩集
作者:許萍芬(Angela,Ping-Fen HSU)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7-08 語言:繁體/中文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失眠的鯊魚 Insomniac Shark.Der schlaflose Hai:許萍芬漢英德三語詩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許萍芬
廣告人,策展人。
1969年出生於台灣,英國薩里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居住於德國柏林。
認為詩是所有藝術形式的原型。《失眠的鯊魚》收錄她於2022-2024年後疫情期間,所創作之發表與未發表共33首詩。大部分的作品在柏林所寫。包含她對戰爭與生命的理解,以及她對第一故鄉台灣的童年記憶。
許萍芬
廣告人,策展人。
1969年出生於台灣,英國薩里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居住於德國柏林。
認為詩是所有藝術形式的原型。《失眠的鯊魚》收錄她於2022-2024年後疫情期間,所創作之發表與未發表共33首詩。大部分的作品在柏林所寫。包含她對戰爭與生命的理解,以及她對第一故鄉台灣的童年記憶。
目錄
【總序】詩推台灣印象/李魁賢
【推薦序】柏林詩人.Berlin Poet/廖亦武
【自序】失眠的鯊魚.Insomniac Shark
▲第一輯
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to You
時間的流.Flow of Time
我到麥比拉來看你.I Came to Maibila to See You
再見.Farewell
地鐵正義.Subway Justice
帕岸島的早上─驚醒.Morning in Ko Pha Ngan - Awakened
帕岸島的早上─發呆.Morning in Ko Pha Ngan - Daydreaming
芭蕾舞者.Ballet Dancer
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攪動著.The First Morning Coffee – Mixed
早晨的第一杯咖啡─喝完了.The First Morning Coffee – Gone
噪音.Noise
▲第二輯
陽光拜訪法蘭克福大街.Sunlight Visits Frankfurter Allee
巴赫姆特的《月光奏鳴曲》.Moonlight Sonata in Bachmut
陽台上最後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n the Balcony
御風玫瑰.The Rose Braving the Wind
彈著鋼琴的流浪漢.The Piano-Playing Vagabond
仲夏夜奏鳴曲.Midsummer Night Sonata
冬雪輕爵士.Smooth Jazz in Snowy Winter
烏魚米粉.Blackmullet Vermicelli
摩洛哥悲歌.Morocco Lament
那個英國人和他的夫人.The Englishman and his Wife
霧.The Fog
▲第三輯
黑夜裡的噩夢.In the Nightmare of the Night
被退回的明信片.The Returned Postcards
秋天的華爾滋.Autumn Waltz
深夜食堂.Late Night Diner
聖誕不快樂.Unhappy Christmas
幽靈與種子.Spectre and Seed
回家.Return Home
月亮依然升起.Moon also Rises
雙黃蓮蓉.Double Yolk Mooncake
十月菱角.October’s Water Chestnuts
我的魔法.My Magic
朗讀——線上音檔.Reading - Audio Data
感謝.Acknowledgements
作者簡介.About the Author
【推薦序】柏林詩人.Berlin Poet/廖亦武
【自序】失眠的鯊魚.Insomniac Shark
▲第一輯
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to You
時間的流.Flow of Time
我到麥比拉來看你.I Came to Maibila to See You
再見.Farewell
地鐵正義.Subway Justice
帕岸島的早上─驚醒.Morning in Ko Pha Ngan - Awakened
帕岸島的早上─發呆.Morning in Ko Pha Ngan - Daydreaming
芭蕾舞者.Ballet Dancer
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攪動著.The First Morning Coffee – Mixed
早晨的第一杯咖啡─喝完了.The First Morning Coffee – Gone
噪音.Noise
▲第二輯
陽光拜訪法蘭克福大街.Sunlight Visits Frankfurter Allee
巴赫姆特的《月光奏鳴曲》.Moonlight Sonata in Bachmut
陽台上最後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n the Balcony
御風玫瑰.The Rose Braving the Wind
彈著鋼琴的流浪漢.The Piano-Playing Vagabond
仲夏夜奏鳴曲.Midsummer Night Sonata
冬雪輕爵士.Smooth Jazz in Snowy Winter
烏魚米粉.Blackmullet Vermicelli
摩洛哥悲歌.Morocco Lament
那個英國人和他的夫人.The Englishman and his Wife
霧.The Fog
▲第三輯
黑夜裡的噩夢.In the Nightmare of the Night
被退回的明信片.The Returned Postcards
秋天的華爾滋.Autumn Waltz
深夜食堂.Late Night Diner
聖誕不快樂.Unhappy Christmas
幽靈與種子.Spectre and Seed
回家.Return Home
月亮依然升起.Moon also Rises
雙黃蓮蓉.Double Yolk Mooncake
十月菱角.October’s Water Chestnuts
我的魔法.My Magic
朗讀——線上音檔.Reading - Audio Data
感謝.Acknowledgements
作者簡介.About the Author
序
總序
詩推台灣印象
李魁賢(叢書策畫)
進入21世紀,台灣詩人更積極走向國際,個人竭盡所能,在詩人朋友熱烈參與支持下,策畫出席過印度、蒙古、古巴、智利、緬甸、孟加拉、尼加拉瓜、馬其頓、秘魯、突尼西亞、越南、希臘、羅馬尼亞、墨西哥等國舉辦的國際詩歌節,並編輯《台灣心聲》等多種詩選在各國發行,使台灣詩人心聲透過作品傳佈國際間。
多年來進行國際詩交流活動最困擾的問題,莫如臨時編輯帶往國外交流的選集,大都應急處理,不但時間緊迫,且選用作品難免會有不周。因此,興起策畫【台灣詩叢】雙語詩系的念頭。若台灣詩人平常就有雙語詩集出版,隨時可以應用,詩作交流與詩人交誼雙管齊下,更具實際成效,對台灣詩的國際交流活動,當更加順利。
以【台灣】為名,著眼點當然有鑑於台灣文學在國際間名目不彰,台灣詩人能夠有機會在國際努力開拓空間,非為個人建立知名度,而是為推展台灣意象的整體事功,期待開創台灣文學的長久景象,才能奠定寶貴的歷史意義,台灣文學終必在世界文壇上佔有地位。
實際經驗也明顯印證,台灣詩人參與國際詩交流活動,很受重視,帶出去的詩選集也深受歡迎,從近年外國詩人和出版社與本人合作編譯台灣詩選,甚至主動翻譯本人詩集在各國文學雜誌或詩刊發表,進而出版外譯詩集的情況,大為增多,即可充分證明。
承蒙秀威資訊科技公司一本支援詩集出版初衷,慨然接受【台灣詩叢】列入編輯計畫,對台灣詩的國際交流,提供推進力量,希望能有更多各種不同外語的雙語詩集出版,形成進軍國際的集結基地。
推薦序
柏林詩人
廖亦武(2012年德國書商和平獎得主)
許萍芬是詩人,這是我以前沒想到的——以前我只知道她是文化方面的策展人。她曾受臺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的委託,組織團隊幫我拍攝過描述香港淪陷的詩歌朗誦影片《二次屠殺》,也曾主持過臺灣駐柏林使館歡迎美麗島抗議事件的英雄之一陳菊訪歐。我們有過相當多的交往——萍芬有無數的可能性變換無數的稱謂,可我唯一沒想到她是一個詩人,竟然用詩行來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靈氣十足,天分足夠,比如「失眠的鯊魚」這個題目,就讓我很意外。因為只有「失眠的鯊魚」才將暫時迷失嗜血的攻擊本能,這剛巧道出了叢林世界弱肉強食的冷酷本質。
萍芬的德國丈夫,中文名叫「孔茂」,是個小說家。這也是我以前沒想到的——以前我只知道孔茂是一個高明的醫生,對病人和朋友都極有耐心。直到有一天,他拿出一疊翻成中文的小說稿,就像這次,萍芬寄來一本詩集,冷不防嚇人一跳。並且,孔茂的小說是寫他在上海行醫之際,如何千難萬險上湖北武當山,尋找道家的修煉方式,以求得心靈的解脫或開悟——讀完萍芬的詩集,我的眼前不再是臺灣策展人和德國醫生的組合,而是詩人和小說家的神交。萍芬的日記式詩歌,恰恰是孔茂當年追尋的答案。比如在自序中,萍芬提到弘一法師臨終那世人皆知的「悲欣交集」,我的理解是,對於活著的人們未知的死亡,或未知的疆域,即將跨入死亡的弘一法師,不知道是「悲」還是「欣」,所以,萬般「交集」——孔茂也一定讀懂了以下詩句:
「大滴大滴的眼淚
迅速跳出我的眼睛
掉落到桌面上
第一次聽到眼淚的聲音」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柏林人。雖然,據說,這句話,兩個美國總統(甘迺迪和雷根)都說過。可我沒有模仿他們的意思。柏林這地界,街上走著的每個普通人,表面的身份也許和萍芬和孔茂一樣,是策展人、廣告人、工人、醫生、市民、修理工、清潔工、公務員、郵遞員、藝術家,甚至流浪漢,可被掩蔽的心靈的身份或職業,卻是自我高度期許並認可的某某人、某某家。比如我是流亡的、用中文寫作的職業作家,可誰也不知道我喜歡去墓地,因為在墓地我可以高聲用母語講故事,而沒有任何德國人從地下冒出來反對;再比如某個冬日,我從二戰中被美國飛機削去腦袋的威廉二世教堂(又叫破教堂)附近的鐵路橋下路過,猛然瞅見一個流浪漢從睡袋中掏出一本厚厚的書,我忍不住好奇,就湊了過去——封面的德文我不認識,但湯瑪斯.曼那張胖臉我還能分辨出來——這個流浪漢竟然在閱讀《魔山》——火車從頭頂轟隆隆地碾過。這就是我現在的故鄉柏林,離我的原鄉成都,相差十萬八千里。
我今生只為劉曉波和劉霞的詩集寫過序言,因為他們的情況相當特別。而今天破例為萍芬寫這篇不合格的「序言」,是因為她和我是一樣的柏林人,真摯,隨意,不那麼在乎,特別包容,也特別嫉惡如仇。還有就是這兒的氛圍,也適合寫這樣一篇序言——地盤沒紐約大,閱讀人數卻比紐約多,上街抗議或歡慶的人數也多,做夢或夜遊的人也多。不務正業的醉漢就更多了。你、我、他,真是超級幸運啊。感謝上帝。
2024年1月17日,夏洛特城堡
自序
失眠的鯊魚
今年一月,我在京都的東本願寺門口看到了一個立牌寫著「悲しみ、苦しみ、惱み、痛みは,人生の味」(意思是:悲傷,心酸,煩惱,痛苦,是人生的滋味)。我想:這是寫給來拜訪寺廟的人看的吧?
我心裡有個疑問:也許吧?但為什麼不至少加一個「樂」混合一下?恰巧,我決定把我為笠詩社60週年紀念寫的一首詩〈深夜食堂〉放進這本詩集─我在那首詩裡借用了弘一法師臨終前寫的「悲欣交集」四個字。在我的理解裡,悲傷與喜悅像兩股繫得緊緊交纏的繩子,形成一股生命的軸。
2022年到2024年,在新冠疫情結束前,世界上發生了許多人禍天災,俄烏戰爭,以巴衝突,還有摩洛哥地震等。我住在柏林,看到不少烏克蘭人在此流亡,學習,或是工作,有時候跟他們對話時,會想這個世界怎麼了。我為此寫下幾首詩:〈巴赫姆特的《月光奏鳴曲》〉,〈陽台上的最後一朵玫瑰〉,〈地鐵正義〉,〈被退回的明信片〉,〈黑夜裡的噩夢〉。
這一本詩集是我2022年8月到2024年1月之間寫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德國柏林完成的。我在2022年八月寫的〈時間的流〉是我此刻對人生的感受:
「……
像河流裡一個小小的鵝卵石
快快的
慢慢的
駐留與離開
滾動與滑行
而最終消失
不擔心我是否被記住
因為我記得
這個痛苦的滾動
以及暢快的游著」
最近在柏林讀到民主鬥士施明德過世的消息,想把這首詩獻給他。
萍芬
2024年1月29日 柏林
詩推台灣印象
李魁賢(叢書策畫)
進入21世紀,台灣詩人更積極走向國際,個人竭盡所能,在詩人朋友熱烈參與支持下,策畫出席過印度、蒙古、古巴、智利、緬甸、孟加拉、尼加拉瓜、馬其頓、秘魯、突尼西亞、越南、希臘、羅馬尼亞、墨西哥等國舉辦的國際詩歌節,並編輯《台灣心聲》等多種詩選在各國發行,使台灣詩人心聲透過作品傳佈國際間。
多年來進行國際詩交流活動最困擾的問題,莫如臨時編輯帶往國外交流的選集,大都應急處理,不但時間緊迫,且選用作品難免會有不周。因此,興起策畫【台灣詩叢】雙語詩系的念頭。若台灣詩人平常就有雙語詩集出版,隨時可以應用,詩作交流與詩人交誼雙管齊下,更具實際成效,對台灣詩的國際交流活動,當更加順利。
以【台灣】為名,著眼點當然有鑑於台灣文學在國際間名目不彰,台灣詩人能夠有機會在國際努力開拓空間,非為個人建立知名度,而是為推展台灣意象的整體事功,期待開創台灣文學的長久景象,才能奠定寶貴的歷史意義,台灣文學終必在世界文壇上佔有地位。
實際經驗也明顯印證,台灣詩人參與國際詩交流活動,很受重視,帶出去的詩選集也深受歡迎,從近年外國詩人和出版社與本人合作編譯台灣詩選,甚至主動翻譯本人詩集在各國文學雜誌或詩刊發表,進而出版外譯詩集的情況,大為增多,即可充分證明。
承蒙秀威資訊科技公司一本支援詩集出版初衷,慨然接受【台灣詩叢】列入編輯計畫,對台灣詩的國際交流,提供推進力量,希望能有更多各種不同外語的雙語詩集出版,形成進軍國際的集結基地。
推薦序
柏林詩人
廖亦武(2012年德國書商和平獎得主)
許萍芬是詩人,這是我以前沒想到的——以前我只知道她是文化方面的策展人。她曾受臺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的委託,組織團隊幫我拍攝過描述香港淪陷的詩歌朗誦影片《二次屠殺》,也曾主持過臺灣駐柏林使館歡迎美麗島抗議事件的英雄之一陳菊訪歐。我們有過相當多的交往——萍芬有無數的可能性變換無數的稱謂,可我唯一沒想到她是一個詩人,竟然用詩行來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靈氣十足,天分足夠,比如「失眠的鯊魚」這個題目,就讓我很意外。因為只有「失眠的鯊魚」才將暫時迷失嗜血的攻擊本能,這剛巧道出了叢林世界弱肉強食的冷酷本質。
萍芬的德國丈夫,中文名叫「孔茂」,是個小說家。這也是我以前沒想到的——以前我只知道孔茂是一個高明的醫生,對病人和朋友都極有耐心。直到有一天,他拿出一疊翻成中文的小說稿,就像這次,萍芬寄來一本詩集,冷不防嚇人一跳。並且,孔茂的小說是寫他在上海行醫之際,如何千難萬險上湖北武當山,尋找道家的修煉方式,以求得心靈的解脫或開悟——讀完萍芬的詩集,我的眼前不再是臺灣策展人和德國醫生的組合,而是詩人和小說家的神交。萍芬的日記式詩歌,恰恰是孔茂當年追尋的答案。比如在自序中,萍芬提到弘一法師臨終那世人皆知的「悲欣交集」,我的理解是,對於活著的人們未知的死亡,或未知的疆域,即將跨入死亡的弘一法師,不知道是「悲」還是「欣」,所以,萬般「交集」——孔茂也一定讀懂了以下詩句:
「大滴大滴的眼淚
迅速跳出我的眼睛
掉落到桌面上
第一次聽到眼淚的聲音」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柏林人。雖然,據說,這句話,兩個美國總統(甘迺迪和雷根)都說過。可我沒有模仿他們的意思。柏林這地界,街上走著的每個普通人,表面的身份也許和萍芬和孔茂一樣,是策展人、廣告人、工人、醫生、市民、修理工、清潔工、公務員、郵遞員、藝術家,甚至流浪漢,可被掩蔽的心靈的身份或職業,卻是自我高度期許並認可的某某人、某某家。比如我是流亡的、用中文寫作的職業作家,可誰也不知道我喜歡去墓地,因為在墓地我可以高聲用母語講故事,而沒有任何德國人從地下冒出來反對;再比如某個冬日,我從二戰中被美國飛機削去腦袋的威廉二世教堂(又叫破教堂)附近的鐵路橋下路過,猛然瞅見一個流浪漢從睡袋中掏出一本厚厚的書,我忍不住好奇,就湊了過去——封面的德文我不認識,但湯瑪斯.曼那張胖臉我還能分辨出來——這個流浪漢竟然在閱讀《魔山》——火車從頭頂轟隆隆地碾過。這就是我現在的故鄉柏林,離我的原鄉成都,相差十萬八千里。
我今生只為劉曉波和劉霞的詩集寫過序言,因為他們的情況相當特別。而今天破例為萍芬寫這篇不合格的「序言」,是因為她和我是一樣的柏林人,真摯,隨意,不那麼在乎,特別包容,也特別嫉惡如仇。還有就是這兒的氛圍,也適合寫這樣一篇序言——地盤沒紐約大,閱讀人數卻比紐約多,上街抗議或歡慶的人數也多,做夢或夜遊的人也多。不務正業的醉漢就更多了。你、我、他,真是超級幸運啊。感謝上帝。
2024年1月17日,夏洛特城堡
自序
失眠的鯊魚
今年一月,我在京都的東本願寺門口看到了一個立牌寫著「悲しみ、苦しみ、惱み、痛みは,人生の味」(意思是:悲傷,心酸,煩惱,痛苦,是人生的滋味)。我想:這是寫給來拜訪寺廟的人看的吧?
我心裡有個疑問:也許吧?但為什麼不至少加一個「樂」混合一下?恰巧,我決定把我為笠詩社60週年紀念寫的一首詩〈深夜食堂〉放進這本詩集─我在那首詩裡借用了弘一法師臨終前寫的「悲欣交集」四個字。在我的理解裡,悲傷與喜悅像兩股繫得緊緊交纏的繩子,形成一股生命的軸。
2022年到2024年,在新冠疫情結束前,世界上發生了許多人禍天災,俄烏戰爭,以巴衝突,還有摩洛哥地震等。我住在柏林,看到不少烏克蘭人在此流亡,學習,或是工作,有時候跟他們對話時,會想這個世界怎麼了。我為此寫下幾首詩:〈巴赫姆特的《月光奏鳴曲》〉,〈陽台上的最後一朵玫瑰〉,〈地鐵正義〉,〈被退回的明信片〉,〈黑夜裡的噩夢〉。
這一本詩集是我2022年8月到2024年1月之間寫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德國柏林完成的。我在2022年八月寫的〈時間的流〉是我此刻對人生的感受:
「……
像河流裡一個小小的鵝卵石
快快的
慢慢的
駐留與離開
滾動與滑行
而最終消失
不擔心我是否被記住
因為我記得
這個痛苦的滾動
以及暢快的游著」
最近在柏林讀到民主鬥士施明德過世的消息,想把這首詩獻給他。
萍芬
2024年1月29日 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