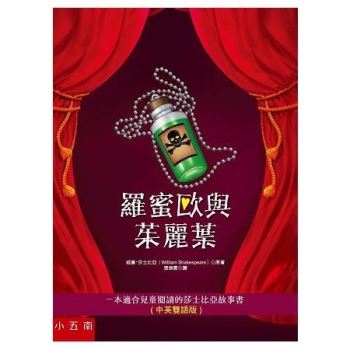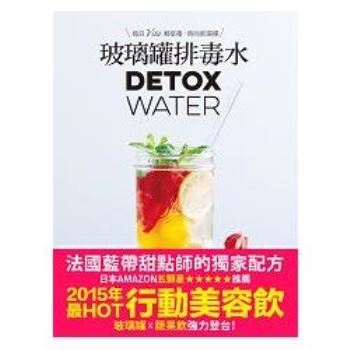無論在任何時代,閱讀中的女性都是令藝術家著迷的創作主題。但是女性要等待好幾百年以後,才獲准隨心所欲讀書。不過一旦她們發現閱讀能夠提供機會,用思想、想像力和知識的無限天地來取代家中的狹隘空間,她們從此就變成了一種威脅。
以閱讀中的婦女為主題之圖畫具有獨特的美感、優雅及表現力。本書以簡潔的文字說明了她們為何閱讀,以及沉浸於何種讀物之中。我們彷彿於漫遊之際同時獲得了有關藝術家、畫中天地和整個時代的資訊。
斯提凡.博爾曼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對緊張刺激的婦女閱讀史進行探討。所涵蓋的時間從中世紀一直延伸到現代,並以十九和二十世紀做為重點。全書精選的繪畫、插圖和照片均附有說明短文。
作者簡介
斯提凡.博爾曼(Stefan Bollman)
出生於一九五八年,曾在大學研習德國文學、戲劇、歷史及哲學,以湯瑪斯.曼為論文主題獲得博士學位。博爾曼現在定居慕尼黑,擔任教師和作家,並為許多叢書的編撰者。
譯者簡介
周全
民國四十四年出生於台北市,台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o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譯者旅居歐美二十年,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羅斯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美國及巴哈馬高科技公司行銷總經理,現為自由業者,從事撰著及歷史書籍翻譯。譯作有《白玫瑰 一九四三》、《德藝百年特展》(故宮博物院)、《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破解希特勒》。譯者在俄羅斯的工作成果,曾於西元二000年起由Discovery頻道「科學新疆界──俄國裡海水怪」節目,在全球重複播出。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