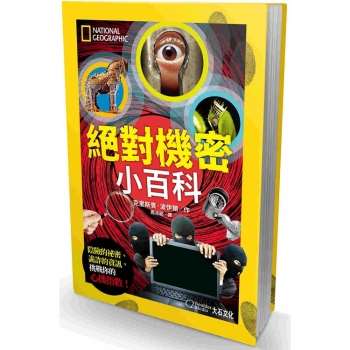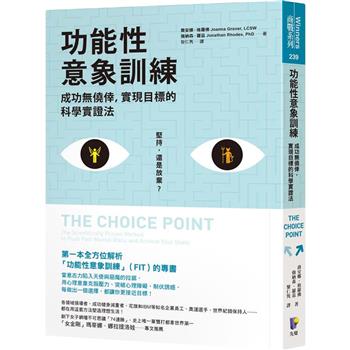五四一百週年,回顧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
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
「五四」一百週年,從各種角度來解析「五四」及其影響,以小觀大,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思想有所回顧和反省。
重新回到「五四」的現場,從容觀賞「五四」傳奇。「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爲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
「五四」發生一百年後,除了學術界的思考之外,一般社會中的「五四」記憶已湮沒於時間之河中。與此同時,權力當局的刻意介入或刻意忽視,恰恰顯示「五四」的被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痕跡──「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潛能反而被埋沒了。
「五四」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此。「五四」不遠,卻已有考掘的必要。《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邀請51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於不同面相揭開「五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本書旨在回顧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這三者息息相關,構成「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以此觸動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
《五四@100》以眾聲喧嘩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回顧「五四」,我們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未必不同於「五四」:呐喊與徬徨,激情與幻滅,神話「五四」與否想「五四」,相互糾纏,導入下一輪的思考與行動。
延伸閱讀
《思想史6:五四新文化運動》,潘光哲、瞿駿、王銳、Sebastian Veg、Shakhar Rahav、王汎森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王德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論、比較文學等。主要著作包括《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等。
宋明煒
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科幻小說。著有《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少年中國:青春文化與成長小說》等。
本書作者
陳思和(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平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陳建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致遠講席教授)
王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現代文學教研室副教授、研究員)
戴燕(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楊貞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彭小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應磊(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石井剛(ISHII Tsuyoshi)(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季進(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揚(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楊聯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濱田麻矢(HAMADA Maya)(神戸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歷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季劍青(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
鄭毓瑜(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邱怡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夏小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吳盛青(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王璞(布蘭戴斯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
葛兆光(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婧裬(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助理教授)
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馬筱璐(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晨(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陳國球(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潘光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彭春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涂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候選人)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兼職教授)
郜元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張麗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現代文學教研室教授)
李浴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肖鐵(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
張新穎(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袁一丹(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蔣漢陽(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戲劇與影視系博士候選人)
黃英哲(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暨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宋明煒(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
(姓名排列按目次次序)
章節試閱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王汎森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接觸一九三○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分,而且兩種成分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從一九一七年左右開始,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白話新文學等為主軸。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左右兩翼時濃時淡,像調色盤中的色彩到處竄動、交融(譬如傅斯年也寫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其成色與分量之增減,與北伐、清黨等政治局勢的變化也有非常複雜的關聯。但是愈到後來,則儼然有左右兩個「五四」運動。
我認為,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因而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當時青年常將「新學理」掛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也在「新學理」的大傘下被並置。從《「五四」時期的社團》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等書,可以看出同一個社團或同一個期刊,往往同時擁有在當時不覺得互相排斥、而在左右兩翼分裂之後覺得不共戴天的思想成分。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有許多材料顯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管是閱讀的書刊,或是信從的觀點,都是左右雜存的(「問題與主義論戰」期間,毛澤東一度還是胡適「問題」派的信徒)。蔣介石早期的日記與年譜,亦復顯現他在「五四」時期一方面服膺「輸入新學理」的主張,積極學英文、想遊學歐美三年,同時也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愛好者。
以傅斯年、羅家倫兩位「五四」運動的主將為例,他們後來皆成為胡適陣營的人物,而且都堅決反共。可是如果以後來的發展,倒著回去看他們在「五四」時期的思想面貌,就會發現後來發展出的單一面相與「五四」時期有明顯的差距。傅斯年在《新潮》中發表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在傅斯年過世之後台灣大學所編的集子以及一九八○年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傅斯年全集》,這篇文章都未被收入,因此遮蓋了他在「五四」時期思想的複雜性。至於羅家倫,他在念北京大學時原與李大釗過從甚密,曾積極撰文回應李大釗,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全世界之主流。
我們暫時不管這些全國知名的風頭人物,改看當時在地方上尚不知名的小讀者,也常見左右兩翼成分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情形。最近我有機會讀到《王獻唐日記》的列印本,在王獻唐一九一七年所讀的書中,既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及《杜威五大講演》,也有《馬克思經濟學說》、《革命哲學》。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的意義與價值》(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雜在《老子》、《莊子》、《東塾讀書記》、《求闕齋日記》之類古籍中。這一位不知名的山東青年的私人紀錄告訴我們,在當時青年心中,我們後來以為天經地義的分別是不存在的,所以應當合「左」、「右」兩端看那個時代,才能比較清楚地把握當時的實況,也比較能有意識地觀察它們後來為何分道揚鑣。
「五四」是一個改變近代中國各種氣候的關鍵事件,所以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時,我們往往因過度注意平滑上升的軌跡而忽略了事件發展、積累到一個程度,會因各種因素的彙集而有一個「量子跳躍」(quantum leap)的時刻。「量子跳躍」造成一種大震動、一種重擊,它對日常之流造成「中斷」、「回頭」、「向前」,形成了一種新意識,在認識原有的情境與材料時,形成了新的線索。
探究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用蒙文通的意思來說,必須要能「前後左右」。一方面是,在了解這個運動的形成時,不能只注意與運動內容直接相關的部分,必須從「前後左右」去尋找;另一方面是,描述這個運動的影響時,不能只局限在思想領導者所意圖要傳達的訊息,因為它的影響無微不至,常常在意想不到之處也發生了影響,故必須從「前後左右」去求索。
「五四」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眼光」,老舍即回憶經過「五四」,有一雙「新眼睛」在影響著他的創作:
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
我的觀察是,「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有「德先生」、「賽先生」這兩隻大瓜,不經意的幾篇短文或幾句話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響,形成一種新的氣氛或態度:包括新的學術態度(譬如有「新」意識的人,對古代經書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不會再把先秦禮經當作周代生活的實際紀錄。)、文化氛圍、人生態度、善惡美醜好壞的感覺與評價、情感的特質(譬如強大的「道德激情」)等。
「五四」也帶來一種新的政治視野,對於什麼是新的、好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標準。用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的話說:「(民國)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變化,使得國民黨得著革命的生力軍。」
「五四」運動造成一波新的政治運動與政治菁英。真誠的信從者(true believer)與現實的利益往往套疊在一起,不再能分彼此,「新青年」及後來的「進步青年」成為一種既帶理想又時髦的追求後,帶出了一種新的現實,成為出風頭、趕時髦的資本。同時,連出風頭、趕時髦、吸引異性、戀愛的方式都有一種微妙的變化。
「五四」運動激起了一種關心國事、關心「新思潮」的風氣,造成了一種閱讀革命,書報閱讀者激增,能讀新書報即代表一種新的意向;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青年的生命及行為的形式,人們常常從新文學中引出新的人生態度及行為的方式。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閱讀史時,有學者從一宗訂閱盧梭著作的通信中發現,有的讀者因為太深入盧梭的思想世界,竟模仿起盧梭的生命歷程及行為方式來。這類例子當然是常見的,晚清以來有許多人讀曾國藩的日記或家書,而在生命的安排及行為方式方面深受其影響。
像「五四」這種改變歷史的重大運動,它搖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塊石頭都翻動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來的地方,往往也是經過一番思考後再放回去。而且從此之後,古今乃至未來事件的評價、建構方式,每每都要跟著改變。譬如以「五四」作為新的座標點,古往今來的文學、藝術、政治、歷史等,都要因它們與「五四」的新關係而經過一些微妙的變化。即使連反對派也不能完全豁免。許多反對派隱隱然接受某些新文化運動的前提,或是為了與它對抗而調動思想資源,形成某些如非經過這一對陣,是不可能以這個方式形成或如此展現的討論形式,或是根本在新文化運動論述的籠罩之下而不自知。
這不是一種單純的「影響」,應該說是新文化運動當空「掠過」而使得一切分子的組成方式發生變化。此處可舉達爾文進化論與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例子。這一學說影響許許多多人,可是起而與之對抗的學說(譬如宋恕等人的以弱者為主體的「扶弱哲學」),顯然是針對「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強權公理」的一種反擊;但反擊在另一種方面說是潛在的「反模仿」,如果不是因為有「天演論」,則不至於有像宋恕那樣動員各種思想資源來構作以歷史上的弱者為中心的哲學。至於章太炎提出「俱分進化論」,主張「善進惡亦進」,太虛大師用佛經來評天演論等等,也都不是「天演論」之前會出現的表述。
沒有五四,何來晚清?/王德威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是我論晚清小說專書《被壓抑的現代性》(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997)中文版導論的標題。長久以來,文學和政治文化史上的晚清一直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集頹廢、封建於一身。相對於此,五四則代表現代性的開端;啟蒙與革命,民主與科學的號召至今不絕。
這樣的二元史觀其實早已問題重重,但因學科建制和政治論述使然,學界始終不能攖其鋒。在《被壓抑的現代性》裡,我重讀太平天國以來的小說,企圖藉此重理晚清文學文化的脈絡,並挖掘「被壓抑的」現代性線索。我處理了狹邪、公案、譴責、科幻四種文類,視之為現代情感、正義、價值、知識論述的先聲。我認為在西學湧進的前夕,晚清作家想像、思辨「現代」的努力不容抹煞。
始料未及的是,因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一命題,《被壓抑的現代性》中譯本在大陸出版後(二○○五)引起許多討論,至今不息。爭議最大的焦點在於,五四所代表的中國「現代」意義空前絕後,豈容與帝國末世的晚清相提並論?更何況「沒有」、「何來」這樣的修辭所隱含的邏輯先後與高下之別。批評者或謂此書譁眾取寵,解構正統典範,或謂之矯枉過正,扭曲五四豐富意涵;等而下之者則刻意羅織線索,謂其反毛反黨反馬列。論晚清而反黨反毛,如此學術文章果然證明「厲害了,我的國!」
晚清文學一向被視為現代邊緣產物,如能因為一己並不算成熟的研究引起矚目,未嘗不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部分論者所顯現的焦慮和敵意暴露「文學」在當代中國作為政治符碼,畢竟不能等閒視之。無可諱言的,直至今日中國官方歷史仍然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下展開,因此近代、現代、當代的劃分有其意識形態基礎,不容逾越。在這樣的論述下,五四具有圖騰意義,它必須是「新的」文學和歷史的起源,是啟蒙和革命的基礎。
我在書中強調,「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與其說是一錘定音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引發批評對話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現代中發現後現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衛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學史單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五四和晚清「當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從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範式都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這不必意謂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更不意味歷史進展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回顧每一個歷史節點,我們理解其中的千頭萬緒;必然與偶然,聯關與突變都有待後之來者的不斷思考定位。
對《被壓抑的現代性》的爭論多半集中在史料史實的辯駁,而忽略更深層次的批評動機。論者往往強調晚清的「發現」是由五四首開其端。但以此類推,五四的「發現」豈不也總已是後見之明?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斷折衝,正是歷史化「歷史」的重要步驟。我使用「時代錯置」(anachrony)、「擬想假設」(presumptive mood)方法看待晚清與五四的公案,目的不在解構傳統而已──那未免太過輕率虛無。恰恰相反,我希望以此呈現現代與傳統異同的糾纏面相,以及「俱分進化」的動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言,革命歷史的神祕力量恰恰在於召喚過去,以古搏今,爆發成為「現在」(jetztzeit)的關鍵時刻:「呈現過去並不是將過去追本還原,而是執著於記憶某一危險時刻的爆發點。歷史唯物論所呈現的過去,即過去在歷史一個危險時間點的意外呈現。」
這帶向第二類批判:晚清是否果然具有現代性,或如何被壓抑和解放,也成為討論熱點。事實上一九三○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別自左右不同立場,將中國現代性上溯到晚明;日本京都學派更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的起點。這類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無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被視為現代的開端。倡導托古改制、微言大義的「公羊派」經學曾經沉寂千年,何以在晚清異軍突起,成為維新者的托詞;百年之後,「公羊派」又何以成為後社會主義論述支柱之一?換句話說,我們的問題不再是發生學的,而是考掘學的。
除此,識者亦有批評:小說作為一種文類,是否能承載被壓抑的現代性?我認為梁啟超一九○二年提倡小說革命,不僅是文學場域的突變,也是一場政治事件,一次敘述作為歷史載體的重新洗牌。梁啟超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改變人心。如果穿越時空,他或許可以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產生共鳴。鄂蘭強調敘述──說故事──是構成社會群體意義的根本動力。她更認為革命的精神無他,就是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新奇力量(pathos of novelty)。馮夢龍《古今小說》序曾有言,「史統散而小說興」。斷章取義,我要說相對於大言夸夸的大說,是小說才承載了生命的眾聲喧譁。晚清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被壓抑的現代性》出版已逾二十年。許多未必完備的論點已有後之來者的補強,而曾經被視為末流的晚清現象,居然引領當代風潮。二十一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勃興,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顧晚清最後十年的科幻熱,彷彿歷史重演。而歷史當然是不重演的。將過去與現在或任何時間點做出連接比較,劃定意義,本身就是創造歷史的行動。
延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命題,我們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層辯證:「沒有五四,何來晚清?」五四的意義坐標如此多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新舊知識分子的掙扎問難,從而理解他們來時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為五四所帶來的啟蒙思想,我們才得以發揮主體「先入為主」的立場,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國論述下無數的維新契機,被壓抑而復返的衝動。五四可以作為一個除魅的時代,五四也同時是一個招魂的時代。
梁啟超在五四前後歐遊,之後轉向情感教育與倫理美學,比起當年倡導小說革命的豪情壯志,他的思想是退步了,還是以退為進?魯迅的變與不變一樣耐人尋味。曾經號召以文學「攖人心」的摩羅詩人歷經五四,轉而成為死去活來、「自抉其心」的屍人。這是徬徨頹廢,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召喚?歷經哲學美學轉向的王國維此時傾心考古和文字學,最終自沉而亡;眼前無路,他以此調動了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而晚清的章太炎在革命與保守之間劇烈擺盪,並以唯識佛學作為超越起點。五四之後章成為風雲時代的落伍者;五四百年之後章證明他才是「鼎革以文」的先行者。同樣的,沒有對五四的期望或失望,我們何來對晚清或任何其他時空坐標的投射?
當代學者與其糾結於「沒有/何來?」的修辭辯論,不如對「文學」,或「人文學」的前世與今生做出更警醒的觀察。在五四百年以後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然希望發揮五四啟蒙、革命的批判精神,豈不應擱置天天向上的樂觀主義,見證啟蒙所滋生的洞見與不見,革命所帶來的創造與創傷?這是和諧歲月,也是維穩時代。我們奉五四之名所嚮往的眾聲喧譁是否實現?抑或我們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像魯迅所召喚的「真的惡聲」?
在眾多質疑「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述裡,似乎未見對問號這樣句式的討論。事實上新式標點符號就是五四的發明。一九一九年秋,馬裕藻、周作人、胡適、錢玄同等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次年教育部頒行採用。在眾多標點符號中,問號的語義學其實複雜多端,可以是詮釋學式的求證、哲學式的探索、解構式的自嘲、政治式的先發制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時期裡,問號指向疑問、詢問、質問,甚至天問。面向過去與未來,五四是一個提出問號的時代。一百年以後紀念五四,我們仍然有前人的勇氣和餘裕,對新時代提出百無禁忌的問號麼?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王汎森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接觸一九三○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分,而且兩種成分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
作者序
編者序言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五四」的意義堪稱空前絕後。這不僅因為「五四」所引爆的政治、外交角力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也因為「五四」觸發了範圍廣泛的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啟蒙與革命,人權與國權,語言與文學……,種種話題充滿問題性與爭議性,至今仍是思想文化界論證的焦點。更重要的,「五四」所召喚的「情感結構」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成為我們想像或辯證中國現代性的標竿。
「五四」背後,思想革命、文化嬗變、政治行動接踵而來,其間湧現出改變中國人書寫、言說、經驗與理想的種種企劃:啟蒙和反啟蒙、問題與主義、政治與文學、國故與新潮……論爭不絕。如何定義現代、怎樣對待傳統,諸種言說、衝突此起彼落,難有定論,繼起的對話或辯難則籠罩了整個二十世紀,以迄至今。
「五四」的輝煌又伴隨著失落──幾乎少有「五四」知識分子,以為「五四」是一場勝利。恰恰相反,「五四」的任務,無論基於哪一個出發點,都仍需要不斷地被後來者接力,每一次回到「五四」的努力,卻似乎最終總是帶來更悲涼的落寞。「五四的憂鬱」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的課題。
「五四」發生一百年後,除了學術界的思考之外,一般社會中的「五四」記憶已經隨時間而湮沒。與此同時,權力當局的刻意介入或刻意忽視,恰恰顯示「五四」的被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痕跡──「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潛能反而被埋沒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第一次學生運動在海峽對岸已經被物化為愛國樣板,在海峽此岸則被異化為域外故事。又或者,規範的歷史敘事面對這一場歧異重重的事件,只能給出一個最簡單的意義歸納,如官樣文章那樣,在敘事上不需爭論,在思想上也「著無庸議」。
但我們認為「五四」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此。「五四」離開我們不遠,卻已有考掘學的必要。我們編輯這一本小書,無意給予「五四」全景的描述、抑或整體的重構。我們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各抒己見,毋寧說是重新打開「五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我們認為,發生在百年前的運動和我們的時代仍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希望通過具體的形象、同情的理解重新讓這段歷史活過來。
本書旨在回顧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這三者息息相關,構成「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以此觸動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在「五四」一百週年之際,本書邀請五十一位學者,從各種角度來回顧「五四」及其影響,包括「五四」時期提出的問題、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文體、「五四」時期具有影響的人物等。每一位撰稿人都根據一個話題撰寫兩千至三千字短文,風格不拘,旨在以小觀大,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思想有所回顧和反省。
本書所呈現眾聲喧嘩的形式其實有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編輯體例雖不能夠無所不包,但盡量保持寬容的態度。對讀者而言,我們期待的是,假如這些文章能夠引起一些思考,觸類旁通,並進一步理解「五四」在今天的意義,或許我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五四」已經一百年了。回顧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蕩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回顧「五四」,我們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未必不同於「五四」:吶喊與徬徨,激情與幻滅,神話「五四」與否想「五四」,相互糾纏,導入下一輪的思考與行動。而這種辯證過程直指「歷史的不安」,也正是一百年前激發一個世代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的動能。
當我們重新回到「五四」的現場,我們或許發現,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事不關己的位置,讓我們能夠從容觀賞「五四」傳奇。「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在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為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
編者序言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五四」的意義堪稱空前絕後。這不僅因為「五四」所引爆的政治、外交角力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也因為「五四」觸發了範圍廣泛的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啟蒙與革命,人權與國權,語言與文學……,種種話題充滿問題性與爭議性,至今仍是思想文化界論證的焦點。更重要的,「五四」所召喚的「情感結構」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成為我們想像或辯證中國現代性的標竿。
「五四」背後,思想革命、文化嬗變、政治行動接踵而來,其間湧現出改變中國人書寫、言說、經驗與理想的種種企劃:啟蒙和反啟蒙、問題...
目錄
王德威、宋明煒 編者序言
陳思和 士的精神‧先鋒文化‧百年「五四」
王汎森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
陳平原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王德威 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陳建華 「共和」話語
王風 思想革命
戴燕 新文學與舊傳統
楊貞德 學理、主義和現實社會──再探「問題與主義」論辯
彭小妍 五四的反啟蒙:人生哲學與唯情
應磊 現代覺音
石井剛 《國故》月刊──夭折的「古學復興」
季進 重估《學衡》
楊揚 南北五四不同論──對上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價值建構的一個思考
胡曉真 發現文字,想像歌聲:五四學人對非漢族民歌及其歷史傳述之研究的當代意涵
楊聯芬 「新女性」的誕生
濱田麻矢 五四與女學生
梅家玲 發現青少年,想像新國家
張歷君 五四青年的「自殺之道」
雷祥麟 隱形的賽先生──以「性事實」的歷史為例
李奭學 白話文
季劍青 文學
鄭毓瑜 詩國革命
邱怡瑄 執抝的低音──舊詩文中的五四運動
夏小雨 新生的老鴉
吳盛青 「我願把我的靈魂浸入在你的靈魂裡」:五四情書
李孝悌 粉墨登場的五四新文化
王璞 靈感(煙士披里純)
葛兆光 愛恨糾纏的那個日本──對「五四」之前的一個觀察
陳婧裬 希臘的陽光
傅光明 兩個「狂飆」中的莎士比亞
馬筱璐 被轉述的俄羅斯文學
陳相因 不瘋魔,不成活:「以俄為師」──被錨定的現代性
林晨 歐戰
高嘉謙 刀刻與戰士:魯迅在南洋的木刻與雜文遺產
陳國球 香港的「五四」與「新、舊文化」
潘光哲 「五四」與台灣
黃克武 嚴復與五四:中國現代性的內在張力
彭春凌 康有為:聖人的隱退
夏曉虹 五四期間的梁啟超
涂航 美育代宗教:蔡元培與中國現代美學的起源
錢理群 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郜元寶 一份剪報,兩個時代
張麗華 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陳寅恪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對話
李浴洋 另一種「新青年」:「五四」前後的馮友蘭
肖鐵 「我就是群眾;群眾就是我」:五四時期朱謙之的自我書寫和革命想像
張新穎 沈從文與五四
袁一丹 五四:「文化」還是「武化」?
蔣漢陽 五四遺事‧《戲劇春秋》
黃英哲 「五四」在台灣的實踐──魏建功與光復後台灣的國語運動
陳曉明 鄉土農民的「麻木」與「醒覺」──從魯迅到賈平凹的難題
宋明煒 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
王德威、宋明煒 編者序言
陳思和 士的精神‧先鋒文化‧百年「五四」
王汎森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
陳平原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王德威 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陳建華 「共和」話語
王風 思想革命
戴燕 新文學與舊傳統
楊貞德 學理、主義和現實社會──再探「問題與主義」論辯
彭小妍 五四的反啟蒙:人生哲學與唯情
應磊 現代覺音
石井剛 《國故》月刊──夭折的「古學復興」
季進 重估《學衡》
楊揚 南北五四不同論──對上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價值建構的一個思考
胡曉真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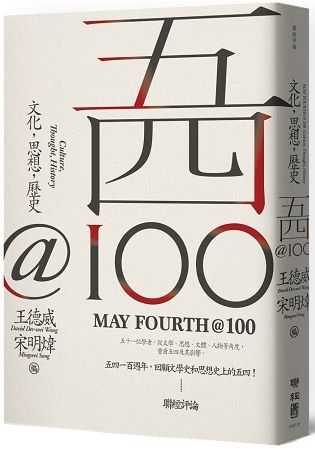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