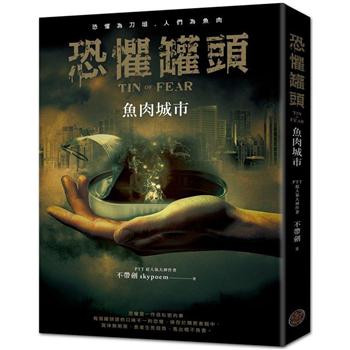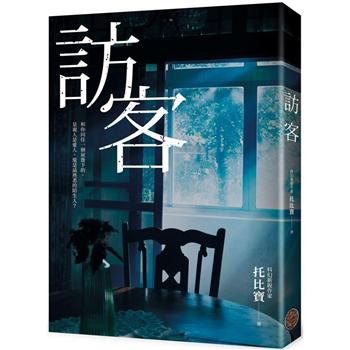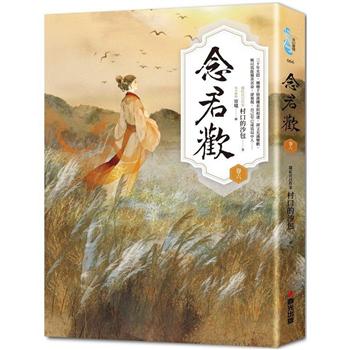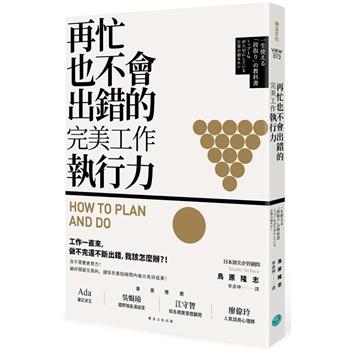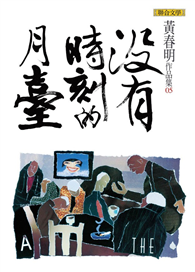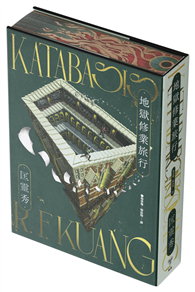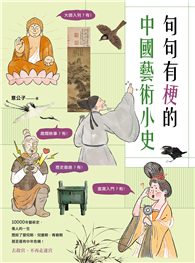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德一人的圖書 |
 |
$ 284 ~ 324 | 論語時用點心:新時代的君子智慧(夏)
作者:德一人 出版社:愛德法國際培訓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6-01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252 ~ 288 | 論語時用點心:新時代的君子智慧(春)
作者:德一人 出版社:愛德法國際培訓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4-01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