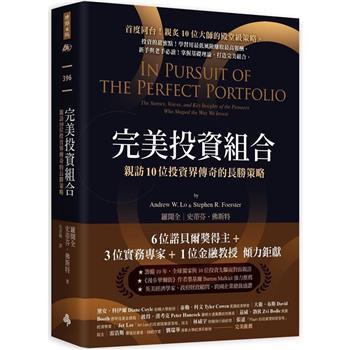第一章 紐約,再見
在這個城市裡,你不會凝視星辰,作白日夢。你不會在早晨出外散步後,埋頭翻閱平原野花手冊,尋找一種途中看到的、綻放璀燦藍色花瓣的喇叭花花名。你不會在雪地上搜尋動物的足跡,或是在這片冰封的森林裡停下腳步,閉上眼,聆聽五子雀覓食的啁啾。在這種時刻,你可能會忘記有蛇這種生物的存在。這種感覺就像紐約被包在一個巨大的塑膠泡泡裡,人類身上帶著信用卡和《查氏餐館指南》,端坐在食物鏈的頂端。本地的野生動物?不過是蟑螂、鴿子、老鼠而已,都是傳染疾病的媒介,都是應該被撲殺的。我們的故事就是從這個泡泡裡展開的。
當時是二○○○年,一個新的千禧年露出曙光。社會各界幾乎已將人們對Y2K的恐懼拋在腦後。經濟前景看好,失業率降到歷來最低點,美國政府對破紀錄的會計盈餘多所誇耀,那斯達克指數超過五千點,使得社會發出一陣振奮活潑的歡呼。股市讓每個人都變得富有──至少在帳面上是如此。在歷史上最富裕的時刻,生活在這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當中的最富裕的城市裡,希瑟和我應該覺得很快樂。
其實不然。
我們花了太多錢在房子上,到戶外走動的時間太少。我們從抽屜裡拿出外國菜餐廳的菜單,週而復始地打電話叫外送餐點來吃。我們在轉角的一家錄影帶店,跟隔在防彈玻璃後面的老闆租來一些令人失望的電影。我們的生活裡失落了某種東西──我們的感情也一樣。然而我們太忙了,沒法面對這個問題。至少我們是用它來當作藉口。於是我們整日辛勤工作,很少談話。到了晚上,我們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樓上公寓裡兩情繾綣、彈簧床嘎吱作響,讓我們無法入眠。然而我們累極了,實在沒力氣讓自己的床鋪也這麼響一下。
這不是身體的疲憊。許多世代的先人努力追求美國夢,令今日的我們受益匪淺。我們放棄了南方小鎮家鄉的農場和工廠的活計,用來換取接受教育和都市生活。讓我們受苦的不再是開耕耘機的時候出了意外,或是被生產線上不停轉動的殘酷機器輾斷了一隻臂膀或一條腿,在我們這個世代,折磨人們的是跟壓力有關的疾病:焦慮症、憂鬱症、電子郵件上癮症、有所虧欠的罪惡感。
我的焦慮感在電腦掛掉的那一天達到高峰。我的米色塑膠殼的戴爾桌上型電腦──我謀生的工具──嗡嗡地停止運轉,螢幕一片漆黑。我內心的慌亂越來越強烈,我用力敲打鍵盤,把開關鍵按了又按,完全沒有反應。我的手指沿著插座上的電線,摸索到電腦的主機上。插頭沒有鬆脫。想到這部我不甚了解的機器,它那滿是金屬線的肚子裡裝了我所需要的大量資料,不禁感到一陣暈眩:一頁頁的調查研究,訪談手稿,一篇三天前就該交稿、馬上就可以完成的文章,寫書的構想,許多認識的人的地址,朋友和編輯們的電子郵件地址,家人的合照,工作相關的資料,稅務的資料。對我來說,這部電腦就是一切。我真是笨蛋,竟然沒有作備份。
剛知道電腦掛了以後,心裡冒出一陣驚慌的情緒,等這陣情緒平息後,我馬上想到我爺爺。他是一位鄉村醫生,也是個養牛的農夫。他生於一八八六年。今日所謂節省時間的科技當時尚未出現,包括讓人們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個星期七天,完全無法離開工作的手機,以及讓人們半夜還在回覆電子郵件的電腦。當人們手上使用的是以鐵、鋼和木材用手工製造而成的器具,他們怎能掌握現代使用鋰離子電池的數位設施虛無飄渺的本質呢?這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在我們中間,有著這一整個世代的人──成長過程中的那個世界,跟我所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樣。
我領悟到,沒有人知道現代化生活長期的後遺症是什麼?我們是否真的可以適應這一切耗盡腦汁的變遷?科技的種種進展、大量湧現的城市、日常生活飛快的步調,還有我們購買的東西和吃下的食物--這些東西的製造過程逐漸由手工全面轉為機器製造。也許我不應該為了內心對科技的矛盾情感(還有電腦當機時,我所感受到的強烈恐懼)而覺得羞愧。我心中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嘶喊:停下來一分鐘!你瞪著電腦螢幕太久啦。你前一次挖掘泥土,或是走過田野,是什麼時候的事了?更不要提你是否種過東西給自己吃了。也許我們跟自然界失去了聯繫,使得我們心中混亂,迷失了方向。如果是這樣,也許這件事就能說明,近來我為什麼如此的不快樂。也許我只是不高興事情沒有按照我的方式順利進行。無論是什麼原因,那一天我就是想要逃離這裡。
然而,我很本分地打電話給戴爾電腦的一位技師。我有妻小,有事業要追求,我能做什麼樣的選擇呢?
幾星期後,在某一個時刻,我突然在一瞬間清醒了,這個時刻改變了一切。當時我正在閱讀報紙上的一篇文章,主題是公視(PBS)的一個節目。這個節目報導英國有一家人正過著十九世紀倫敦居民的生活,並描述他們如何努力對抗這種生活的種種嚴酷考驗。我想到我的電腦危機,這個問題依舊在腦中縈迴不去--我究竟能作什麼樣的選擇?我領悟到,原來我答案就在這裡!答案不是這個真實故事的本身,而是它的核心觀念──採用過往的生活技能。如果我是這麼渴望有所改變,何不回到過去,用這種方式作為重新開始的起點?
我覺得,一九○○年是個合適的年份。我想擺脫某些科技,但我不想當拓荒者,不想徒手建造一棟小木屋,或是自己挖一口井。一九○○年──算是還可以回想到的時期──非常合適。我作了一點調查研究,證明我的直覺是對的。在一九○○年,農村的人口數仍然超過都市人口。在一九○○年,務農仍然是最主要的職業,當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小農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種植、蓄養他們三餐所需的食物。在一九○○年,汽車──也叫作「路程計」(viamote)──仍然是件新奇的玩意兒。在美國農村地區,當時還沒有電視、電話,當然也沒有個人電腦。人們還是用手寫信。還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一九○○年,你能買到衛生紙。
一個星期六,在布魯克林的一家窄小的酒館裡,我們輪流抱著煩躁吵鬧的兒子。我很緊張地把這個構想說給希瑟聽。她聽後微微一笑,這讓我記起了,我是為什麼愛上她的。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羅根.沃德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90 ~ 323 | 我們沒瘋,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
作者:羅根.沃德(Logan Ward) / 譯者:汪芸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9-05-2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00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我們沒瘋,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
一對紐約的文人夫妻,決定移民到沒有3C的1900年,過著返璞歸真的日子。這決定,為他們帶來了危機四伏,卻也充滿歡樂與溫馨回憶的一年……走遍全世界的旅遊作家羅根.沃德,厭倦了半夜還要接手機、回email、通msn,也害怕兒子在城市長大,只認得漢堡不認得牛。於是他和妻子希瑟決定「回到過去」,搬家到維吉尼亞州鄉間去過1900年的農村生活。沒有電視電話、沒有電腦,也沒有汽車,他們得自己種田養牲口,而且只能用一百年前的工具。在這個錯逆的時空之中,沃德夫婦找回了生命中恆常不變的價值,並在親友們的懷疑轉變為支持後,建立起一個超越科技與時空的美好社群。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紐約,再見在這個城市裡,你不會凝視星辰,作白日夢。你不會在早晨出外散步後,埋頭翻閱平原野花手冊,尋找一種途中看到的、綻放璀燦藍色花瓣的喇叭花花名。你不會在雪地上搜尋動物的足跡,或是在這片冰封的森林裡停下腳步,閉上眼,聆聽五子雀覓食的啁啾。在這種時刻,你可能會忘記有蛇這種生物的存在。這種感覺就像紐約被包在一個巨大的塑膠泡泡裡,人類身上帶著信用卡和《查氏餐館指南》,端坐在食物鏈的頂端。本地的野生動物?不過是蟑螂、鴿子、老鼠而已,都是傳染疾病的媒介,都是應該被撲殺的。我們的故事就是從這個泡泡裡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羅根.沃德 譯者: 汪芸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6-01 ISBN/ISSN:9789573264811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11/02/11
201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