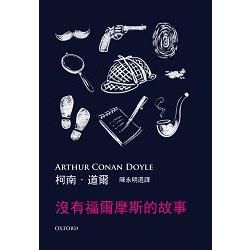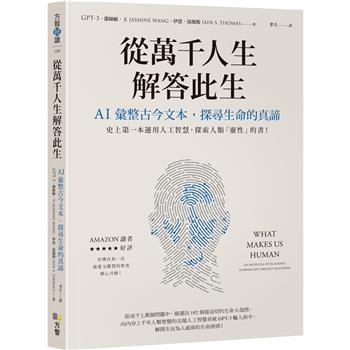偵探小說除了福爾摩斯外,不作他人想;但沒有了福爾摩斯,罪案也就沒有人能夠偵破了嗎?
柯南.道爾曾經擺脫了福爾摩斯十年,擺脫掉福爾摩斯期間寫了不少其他優秀的作品,包括和偵探小說同類的作品,柯南.道爾在文學上,始終得不到他希望得到的尊重。其他沒有福爾摩斯的懸疑小說也遠不及福爾摩斯探案的受讀者歡迎。
本書譯者陳永明教授覺得,柯南.道爾輸了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心中始終是有點不忿的。這本《沒有福爾摩斯的故事》今時今日讀過的人不多,中國讀者就更少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沒有福爾摩斯的故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8 |
小說/文學 |
$ 356 |
文學作品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沒有福爾摩斯的故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英國小說家,因塑造歇洛克.福爾摩斯而成為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作家。《福爾摩斯全集》被譽為偵探小說中的聖經,除此之外他還寫過多部其他類型的作品,如科幻、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戲劇、詩歌等。柯南.道爾1930年7月7日去世,其墓誌銘為「真實如鋼,耿直如劍」(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
柯南.道爾一共寫了60個關於福爾摩斯的故事,56個短篇和四個中篇小說。在40年間陸續發表的這些故事,主要發生在1878到1907年間,最後的一個故事是以1914年為背景。這些故事中,有兩個是以福爾摩斯第一人稱口吻寫成,還有兩個以第三人稱寫成,其餘都是華生(John H. Watson MD)的敍述。
譯者簡介
陳永明
退休教授,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等。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英國小說家,因塑造歇洛克.福爾摩斯而成為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作家。《福爾摩斯全集》被譽為偵探小說中的聖經,除此之外他還寫過多部其他類型的作品,如科幻、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戲劇、詩歌等。柯南.道爾1930年7月7日去世,其墓誌銘為「真實如鋼,耿直如劍」(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
柯南.道爾一共寫了60個關於福爾摩斯的故事,56個短篇和四個中篇小說。在40年間陸續發表的這些故事,主要發生在1878到1907年間,最後的一個故事是以1914年為背景。這些故事中,有兩個是以福爾摩斯第一人稱口吻寫成,還有兩個以第三人稱寫成,其餘都是華生(John H. Watson MD)的敍述。
譯者簡介
陳永明
退休教授,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等。
序
前言
歇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虛構人物了。他的名字——“Sherlock”,在英文裏面,已經成為「偵探」的同義詞;最近,更有人把它作動詞「偵查」用。他的深入人心,備受尊重,於茲可見。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應該大大以他為榮、為傲了。然而,柯南.道爾和福爾摩斯的關係卻不是這樣簡單。
柯南.道爾本來的職業是醫生,1881年從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取得內外科學位。他本來應該早一年便畢業的,但1880年,他到了一艘捕鯨船上充當醫生(雖然,他那時尚未正式畢業,是不夠資格的。不過充當船上,尤其不是客船的醫生,在當時的要求和監管都不十分嚴格),在近北極的海域生活了七個月。畢業後,他在一艘名叫〈美蔭巴〉(Mayumba)的輪船到西非海岸的行程中當醫生。回來後,1882年六月,他選擇在英國,漢普郡,樸茨茅斯濱海一個度假城——南海鎮開業(Southsea, Portsmouth in the county of Hampshire),直到1890年為止。
很多人以為柯南.道爾的寫作是因為他的醫生業務不順暢,不得不靠寫小說,賺點外快為生。其實不然。沒錯,他剛出道的時候生活有點拮据,不過,沒有靠出的新醫生哪一個沒有經過像他這樣的經濟艱難?他在南海鎮開業只三年,每年便已經有三百多鎊(合今天三萬鎊)的收入了,雖然不算富有,但已是當時職業人士的一般收入。而且,他病人越多,寫作越勤。如果只是為了幫補收入,大概不會是這樣的。
還在大學的時候,柯南.道爾已經開始寫作。不過作品沒有出版商接受發表。但他沒有氣餒,屢敗屢戰,終於在1879年發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後數年間,他再發表了兩三篇短篇故事,直到1887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故事《猩紅的習作》*面世,才開始有點文名。1890年,柯南.道爾決定結束在南海鎮的業務,移到倫敦,以眼科醫生的身份開業。作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對眼科是沒有任何特別研究過的,所以遷往倫敦之前,準備先到當時以眼科著名的維也納進修六個月。可是他的德文水平,應付日常生活還勉強可以,學習眼科專業,卻是遠遠不足。在維也納只留了三個月,他便買棹回國去了。這個看來似乎鹵莽的決定,卻增加了我們對他的了解。
讓我們來看看他要搬到倫敦去的真正原因。1889年,他被邀請到倫敦,和一些出版商,包括美國的代表會面,在那次會面中,他被邀約寫第二本福爾摩斯長篇《四簽名》,還認識了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一些國會議員。不到一年,柯南.道爾便決定遷居倫敦了。我看,他所以搬到倫敦並不是要進一步發展他的醫務,而是希望他的寫作生涯,在這個國際文化大都會,可以開出一個新局面。其實,他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靠寫作來多賺一點錢,幫補他醫務收入的不足,恰恰反過來,他是靠醫務的收入來支持他醉心的寫作。從開始,寫作便是他的志趣,當醫生只是在寫作還未能支持生活的時候,賴以維持生活的手段。
1891年,從維也納回來,雖然眼科專業未能學成,他仍然依原定的計劃,四月在倫敦開業。開業的第一個月,半個求診的病人都沒有。五月,他患上了嚴重的感冒,幾乎性命不保,病愈後,他便下了決心,退出醫務,專心寫作。第一個月業務的失敗固然是他不再當醫生的原因之一,但醫生轉到一個新城鎮,開始的時候沒有病人應是意料中事。我看,他的大病幾死,令他感到生命的無常,還是趁有生之年做自己歡喜的事,像陶淵明的「因事順心」,才更是他棄醫從文的主要原因。再加上,1890年出版,第二本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書:《四簽名》,一紙風行。減少了他經濟上的顧慮。
《猩紅的習作》是他初露頭角的一本書,但在經濟上並未有給他帶來甚麼好處。柯南道爾首先把書稿送到《粟崗》雜誌(Cornhill magazine),但編輯覺得故事的篇幅有點兒尷尬,一次刊出太長,分期連載又嫌太短,把稿退了回去。他再送到其他刊物,都沒被接受,有些甚至連看也沒有看,原封不動,便退了回來。後來,終於被一所出版公司:瓦德.洛克(Ward-Lock)接受了,連版權,稿酬二十五英鎊。最後,還被擱置了一年,到1887年,十一月,才在《畢頓聖誕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和其他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混在一起出版,故事雖然獲得一兩篇好的書評,卻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翌年,七月瓦德.洛克把故事獨立印發,1889年又再版,以後,柯南.道爾聲名大噪,更是再版又再版了。可是,他二十五英鎊已經把版權賣斷,所以一點經濟的利益都沒有拿到。《四簽名》才是柯南.道爾第一部以福爾摩斯為主角,名成利就的作品。
可是《猩紅的習作》還是和柯南.道爾的成功有關係的。出版《猩紅的習作》的瓦德.洛克公司編輯白坦尼(G.T.Bettany)後來當了美國《立平可得》雜誌(Lippincott’s Magazine)駐英國的編輯。《四簽名》就是他委約柯南.道爾寫,在該雜誌連載的。獨立成書的出版權也是經他洽商,付予倫敦的史賓沙.柏立葛(Spencer Blackett),後來再轉由喬治.紐尼士(George Newnes)接手,紐尼士就是《斯德蘭特》月刊(Strand Magazine)的創辦人,福爾摩斯的短篇故事開始便是在該刊物發表的,每月一篇,持續了兩年。一時洛陽紙貴,奠定了柯南.道爾在偵探小說上不朽的地位。
因為福爾摩斯得享盛名,柯南.道爾應該對他所創出來的人物寵愛至加,可是事情卻不是這樣,1893年,離《猩紅的習作》出版僅僅七年,柯南.道爾便要把福爾摩斯置諸死地了。雖然,福爾摩斯迷不斷的抗議,出版商重價的利誘,*還是等了足足十年他才勉強地把福爾摩斯復活過來**。留心的讀者,很容易看出,復活後的福爾摩斯大不如前,作者再沒有在他身上放上從前一樣的心力和愛顧了。
「對我來說,他好像鵝肝醬一樣,有點過量了。一次,我吃得太多鵝肝醬,現在一提到這個名字我便覺得作悶。」這是1896年柯南.道爾對人說他對福爾摩斯的感受。這也難怪,自從《四簽名》面世。福爾摩斯的名不脛而走,不到一年,讀者要求他轉達給福爾摩斯的信無日無之,有美國費城的某菸草商,要求福爾摩斯提供怎樣分辨不同菸草氣味的報告;有希望充當福爾摩斯的管家(可能覺得赫臣太太〔Mrs. Hudson〕需要退休了)的;有想聘請福爾摩斯代為查案的;到訪倫敦的旅客,不少以貝克街221B為必須一到的景點;有些還送上禮物:盛菸草的袋子、清潔菸斗的器具、小提琴的絃線⋯⋯等等,只差沒有給他送上毒品海洛英。這都是很煩擾的事,但總不至因此便要把福爾摩斯殺死。
柯南.道爾也曾向友人投訴,每月一篇福爾摩斯令他透不過氣。他說,寫的雖然只是短篇,但佈局,組織所花的時間,心力並不亞於長篇。這些縱使是事實,他大可以少寫幾篇,從每月一篇,減至兩月,三月一篇,固然,為了利益,出版商定必反對,可是總比把福爾摩斯置諸死地更容易接受,反對得更少吧。為甚麼一定要殺死福爾摩斯呢?
文學創作,在文壇取得一席位,是柯南.道爾一生的願望。他自知他的長處是說故事,敍事條理分明、描寫細緻逼真、文字生動活潑、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故事性很強的。他最希望是寫一本成功的歷史小說。福爾摩斯的故事,都是主角從案件發生後,以推理方法,一步一步,抽絲剝繭,至終尋得水落石出,這樣的程式,固然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卻沒有提供很多機會給作者發展故事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刻劃角色之間的關係,描述複雜刺激的行動。福爾摩斯探案意外的成功,便把作者困在這一類的偵探小說的創作程式裏面。更有甚者,這些作品雖然成功,讀者記得的只是那位虛構的主角,卻把作者完全忘掉了。眾多讀者來信求取福爾摩斯,而不是柯南.道爾的簽名,便是明證。所以他覺得福爾摩斯,不錯,為他帶來很大金錢的利益,但也給他帶來巨大,難以承擔的壓力,並且局限了他其他文學方面的發展,又沒有增加他的知名度,幫助他的寫作事業。有點像電影明星辛.康納利(Sean Connery),飾演007占士邦(James Bond),紅透了半邊天。然而,拍了四,五部007電影後,他便毅然拒絕再扮演占士邦,因為他不想給定了型,把他的演藝困死在占士邦這一個,或一類的角色裏面。柯南.道爾也是因為同樣的顧慮,恐怕富福爾摩斯會窒息了他的文學前途,所以對妹夫*說,必須在福爾摩斯未殺死他之先,把福爾摩斯幹掉,雖然,他明白很可能同時也「幹掉」了他的銀行存款。
從1893年到1903年福爾摩斯「死去」那十年當中,柯南.道爾的創作從未中斷,其中不乏包括罪案的懸疑小說,但除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當作是福爾摩斯死前舊案發表外,沒有一篇是和福爾摩斯有關的。在這些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中,他是力圖創出新風格,發揮在寫福爾摩斯探案中用不上的技巧。從本書選譯的故事,讀者便可略見一斑了。然而,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窺到他和福爾摩斯間另一種微妙的關係。
柯南.道爾和福爾摩斯死前的關係似乎是要拼個你死我活。然而在後者「死去」那十年間,前者所寫的懸疑小說裏面的罪案,不是沒有被偵破,犯案者逍遙法外,便是犯案人自己道破做案的始末詳情。有些故事裏面提到某偵探提出這個建議,另一個提出那樣可能,都是幼稚可笑的;很多案件其實是有線索的,但沒有跟進。熟悉福爾摩斯探案的讀者都會覺得要是他沒有「死」,一定不會錯過,案情便會得到水落石出了。柯南.道爾也沒有,像不少其他偵探小說的作者一樣,創造另一個偵探*。在他筆下,只有一個偵探,就是福爾摩斯。這是他對福爾摩斯的尊重,潛意識裏面覺得,偵探除了福爾摩斯外,不作他人想;沒有了福爾摩斯,很多案件也就沒有人能夠偵破。
儘管擺脫了福爾摩斯十年,其間寫了不少其他優秀的作品,包括和偵探小說同類的作品,柯南道爾在文學上,始終得不到他希望得到的尊重。其他沒有福爾摩斯的懸疑小說作品,也遠不及福爾摩斯探案的受讀者歡迎。1903年,他不得已,只好讓福爾摩斯復活,以後,再多寫了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三十二篇短篇,一篇長篇,最後一篇發表於1926年,他逝世前四年。不過,我覺得他輸了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心中始終是有點不忿的。
柯南.道爾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今日讀過的人不多,中國的讀者就更少了。在這裏,我選譯了八篇他寫的,不是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懸疑小說。三篇是寫於《猩紅的習作》——第一部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小說之前。
第一篇,〈那個小四方箱〉(That Little Square Box),1881年發表於《倫敦社會》雜誌(London Society),是柯南道爾最早的作品之一。比它更早的作品有三篇,兩篇帶有神怪的情節,在此不選。另一篇〈與無政府主義者同過的一夜〉(A Night With the Nihilists)也是1881年在《倫敦社會》發表,較〈那個小四方箱〉早幾個月。雜誌的編輯很欣賞這兩篇作品,還去信鼓勵柯南.道爾棄醫從文,不要埋沒了他寫作的天份。這裏選譯〈那個小四方箱〉,因為故事的幽默風趣,在他其他的作品裏面很少見得到。敍事的活潑傳神,情節的引人入勝,與他後來成熟的作品不遑多讓,這篇作品,雖然並沒有惹起太多人的注意,卻是我在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歡的三四篇之一。
第二、第三篇:〈出租馬車車夫的故事〉(The Cabman’s Story)發表於1884年,〈偉奇大叔的回憶〉(The Recollections of Captain Wilkie)發表於1895年(雖然出版日期很晚,但一般人認為寫成的日期,大概不會早於1885年)。兩篇文筆都很生動,但沒有甚麼情節。選在這裏,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故事,讓我們看到柯南道爾作品是怎樣取材的——他把道聽途說得來的故事,增刪潤色,寫成小說,所以他的作品,雖然離奇曲折,真實感還是很強。今日,很多人喜歡克里斯蒂的作品,但和柯南道爾的比較,她的作品未免叫人感到只是故弄玄虛,閉門造車的猜謎遊戲。
不少讀者知道,柯南.道爾在愛丁堡醫學院的老師,約瑟.貝爾教授(Professor Joseph Bell1837–1911)是福爾摩斯的原型。〈偉奇大叔的回憶〉,除了故事生動有趣外,開始一段應該是貝爾教授的寫真,而故事裏面的我,也應該是柯南.道爾的夫子自道。在這裏選譯給讀者參考。
接下來的五篇寫在1898–1899年,福爾摩斯死了,但還未復活的年間,選在這裏是讓讀者評斷,一般人忽略了柯南.道爾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是否合理,是不是他們的損失。除了〈新地下墓穴〉(The New Catacomb)1898年發表於《陽光年刊》(Sunlight Year Book)外,其餘四篇都是發表於《斯德蘭特》月刊,〈營火周圍〉系列(Round the Fire)。
〈新地下墓穴〉,〈巴西貓〉(The Brazilian Cat)和〈失踪的特別專車〉(The Lost special),尤其是前兩篇,我認為在柯南.道爾所有作品中堪稱上上之選,情節的譎詭、曲折,文筆的生動,描寫的細緻,氣氛的緊張,叫人不一口氣看完難以釋卷。在福爾摩斯的探案裏面,找不到幾篇可以及得上。上面提到過,從案件發生後,破案人的角度去寫,是很難給作者提供這種敍事,描寫的機會的。
〈古猶太的胸牌〉(The Jew’s Breastplate),〈黑人醫生〉(The Black Doctor),故事和福爾摩斯的探案最近似,裏面提到一些線索,令人覺得,如果福爾摩斯是故事主角,定可循此而破案。故事由當事人說出來,當事人的感情,心理變化的描寫,福爾摩斯探案裏面,曾不多見。
希望選譯的這八個短篇,能帶給讀者欣悅。
歇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虛構人物了。他的名字——“Sherlock”,在英文裏面,已經成為「偵探」的同義詞;最近,更有人把它作動詞「偵查」用。他的深入人心,備受尊重,於茲可見。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應該大大以他為榮、為傲了。然而,柯南.道爾和福爾摩斯的關係卻不是這樣簡單。
柯南.道爾本來的職業是醫生,1881年從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取得內外科學位。他本來應該早一年便畢業的,但1880年,他到了一艘捕鯨船上充當醫生(雖然,他那時尚未正式畢業,是不夠資格的。不過充當船上,尤其不是客船的醫生,在當時的要求和監管都不十分嚴格),在近北極的海域生活了七個月。畢業後,他在一艘名叫〈美蔭巴〉(Mayumba)的輪船到西非海岸的行程中當醫生。回來後,1882年六月,他選擇在英國,漢普郡,樸茨茅斯濱海一個度假城——南海鎮開業(Southsea, Portsmouth in the county of Hampshire),直到1890年為止。
很多人以為柯南.道爾的寫作是因為他的醫生業務不順暢,不得不靠寫小說,賺點外快為生。其實不然。沒錯,他剛出道的時候生活有點拮据,不過,沒有靠出的新醫生哪一個沒有經過像他這樣的經濟艱難?他在南海鎮開業只三年,每年便已經有三百多鎊(合今天三萬鎊)的收入了,雖然不算富有,但已是當時職業人士的一般收入。而且,他病人越多,寫作越勤。如果只是為了幫補收入,大概不會是這樣的。
還在大學的時候,柯南.道爾已經開始寫作。不過作品沒有出版商接受發表。但他沒有氣餒,屢敗屢戰,終於在1879年發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後數年間,他再發表了兩三篇短篇故事,直到1887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故事《猩紅的習作》*面世,才開始有點文名。1890年,柯南.道爾決定結束在南海鎮的業務,移到倫敦,以眼科醫生的身份開業。作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對眼科是沒有任何特別研究過的,所以遷往倫敦之前,準備先到當時以眼科著名的維也納進修六個月。可是他的德文水平,應付日常生活還勉強可以,學習眼科專業,卻是遠遠不足。在維也納只留了三個月,他便買棹回國去了。這個看來似乎鹵莽的決定,卻增加了我們對他的了解。
讓我們來看看他要搬到倫敦去的真正原因。1889年,他被邀請到倫敦,和一些出版商,包括美國的代表會面,在那次會面中,他被邀約寫第二本福爾摩斯長篇《四簽名》,還認識了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一些國會議員。不到一年,柯南.道爾便決定遷居倫敦了。我看,他所以搬到倫敦並不是要進一步發展他的醫務,而是希望他的寫作生涯,在這個國際文化大都會,可以開出一個新局面。其實,他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靠寫作來多賺一點錢,幫補他醫務收入的不足,恰恰反過來,他是靠醫務的收入來支持他醉心的寫作。從開始,寫作便是他的志趣,當醫生只是在寫作還未能支持生活的時候,賴以維持生活的手段。
1891年,從維也納回來,雖然眼科專業未能學成,他仍然依原定的計劃,四月在倫敦開業。開業的第一個月,半個求診的病人都沒有。五月,他患上了嚴重的感冒,幾乎性命不保,病愈後,他便下了決心,退出醫務,專心寫作。第一個月業務的失敗固然是他不再當醫生的原因之一,但醫生轉到一個新城鎮,開始的時候沒有病人應是意料中事。我看,他的大病幾死,令他感到生命的無常,還是趁有生之年做自己歡喜的事,像陶淵明的「因事順心」,才更是他棄醫從文的主要原因。再加上,1890年出版,第二本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書:《四簽名》,一紙風行。減少了他經濟上的顧慮。
《猩紅的習作》是他初露頭角的一本書,但在經濟上並未有給他帶來甚麼好處。柯南道爾首先把書稿送到《粟崗》雜誌(Cornhill magazine),但編輯覺得故事的篇幅有點兒尷尬,一次刊出太長,分期連載又嫌太短,把稿退了回去。他再送到其他刊物,都沒被接受,有些甚至連看也沒有看,原封不動,便退了回來。後來,終於被一所出版公司:瓦德.洛克(Ward-Lock)接受了,連版權,稿酬二十五英鎊。最後,還被擱置了一年,到1887年,十一月,才在《畢頓聖誕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和其他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混在一起出版,故事雖然獲得一兩篇好的書評,卻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翌年,七月瓦德.洛克把故事獨立印發,1889年又再版,以後,柯南.道爾聲名大噪,更是再版又再版了。可是,他二十五英鎊已經把版權賣斷,所以一點經濟的利益都沒有拿到。《四簽名》才是柯南.道爾第一部以福爾摩斯為主角,名成利就的作品。
可是《猩紅的習作》還是和柯南.道爾的成功有關係的。出版《猩紅的習作》的瓦德.洛克公司編輯白坦尼(G.T.Bettany)後來當了美國《立平可得》雜誌(Lippincott’s Magazine)駐英國的編輯。《四簽名》就是他委約柯南.道爾寫,在該雜誌連載的。獨立成書的出版權也是經他洽商,付予倫敦的史賓沙.柏立葛(Spencer Blackett),後來再轉由喬治.紐尼士(George Newnes)接手,紐尼士就是《斯德蘭特》月刊(Strand Magazine)的創辦人,福爾摩斯的短篇故事開始便是在該刊物發表的,每月一篇,持續了兩年。一時洛陽紙貴,奠定了柯南.道爾在偵探小說上不朽的地位。
因為福爾摩斯得享盛名,柯南.道爾應該對他所創出來的人物寵愛至加,可是事情卻不是這樣,1893年,離《猩紅的習作》出版僅僅七年,柯南.道爾便要把福爾摩斯置諸死地了。雖然,福爾摩斯迷不斷的抗議,出版商重價的利誘,*還是等了足足十年他才勉強地把福爾摩斯復活過來**。留心的讀者,很容易看出,復活後的福爾摩斯大不如前,作者再沒有在他身上放上從前一樣的心力和愛顧了。
「對我來說,他好像鵝肝醬一樣,有點過量了。一次,我吃得太多鵝肝醬,現在一提到這個名字我便覺得作悶。」這是1896年柯南.道爾對人說他對福爾摩斯的感受。這也難怪,自從《四簽名》面世。福爾摩斯的名不脛而走,不到一年,讀者要求他轉達給福爾摩斯的信無日無之,有美國費城的某菸草商,要求福爾摩斯提供怎樣分辨不同菸草氣味的報告;有希望充當福爾摩斯的管家(可能覺得赫臣太太〔Mrs. Hudson〕需要退休了)的;有想聘請福爾摩斯代為查案的;到訪倫敦的旅客,不少以貝克街221B為必須一到的景點;有些還送上禮物:盛菸草的袋子、清潔菸斗的器具、小提琴的絃線⋯⋯等等,只差沒有給他送上毒品海洛英。這都是很煩擾的事,但總不至因此便要把福爾摩斯殺死。
柯南.道爾也曾向友人投訴,每月一篇福爾摩斯令他透不過氣。他說,寫的雖然只是短篇,但佈局,組織所花的時間,心力並不亞於長篇。這些縱使是事實,他大可以少寫幾篇,從每月一篇,減至兩月,三月一篇,固然,為了利益,出版商定必反對,可是總比把福爾摩斯置諸死地更容易接受,反對得更少吧。為甚麼一定要殺死福爾摩斯呢?
文學創作,在文壇取得一席位,是柯南.道爾一生的願望。他自知他的長處是說故事,敍事條理分明、描寫細緻逼真、文字生動活潑、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故事性很強的。他最希望是寫一本成功的歷史小說。福爾摩斯的故事,都是主角從案件發生後,以推理方法,一步一步,抽絲剝繭,至終尋得水落石出,這樣的程式,固然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卻沒有提供很多機會給作者發展故事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刻劃角色之間的關係,描述複雜刺激的行動。福爾摩斯探案意外的成功,便把作者困在這一類的偵探小說的創作程式裏面。更有甚者,這些作品雖然成功,讀者記得的只是那位虛構的主角,卻把作者完全忘掉了。眾多讀者來信求取福爾摩斯,而不是柯南.道爾的簽名,便是明證。所以他覺得福爾摩斯,不錯,為他帶來很大金錢的利益,但也給他帶來巨大,難以承擔的壓力,並且局限了他其他文學方面的發展,又沒有增加他的知名度,幫助他的寫作事業。有點像電影明星辛.康納利(Sean Connery),飾演007占士邦(James Bond),紅透了半邊天。然而,拍了四,五部007電影後,他便毅然拒絕再扮演占士邦,因為他不想給定了型,把他的演藝困死在占士邦這一個,或一類的角色裏面。柯南.道爾也是因為同樣的顧慮,恐怕富福爾摩斯會窒息了他的文學前途,所以對妹夫*說,必須在福爾摩斯未殺死他之先,把福爾摩斯幹掉,雖然,他明白很可能同時也「幹掉」了他的銀行存款。
從1893年到1903年福爾摩斯「死去」那十年當中,柯南.道爾的創作從未中斷,其中不乏包括罪案的懸疑小說,但除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當作是福爾摩斯死前舊案發表外,沒有一篇是和福爾摩斯有關的。在這些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中,他是力圖創出新風格,發揮在寫福爾摩斯探案中用不上的技巧。從本書選譯的故事,讀者便可略見一斑了。然而,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窺到他和福爾摩斯間另一種微妙的關係。
柯南.道爾和福爾摩斯死前的關係似乎是要拼個你死我活。然而在後者「死去」那十年間,前者所寫的懸疑小說裏面的罪案,不是沒有被偵破,犯案者逍遙法外,便是犯案人自己道破做案的始末詳情。有些故事裏面提到某偵探提出這個建議,另一個提出那樣可能,都是幼稚可笑的;很多案件其實是有線索的,但沒有跟進。熟悉福爾摩斯探案的讀者都會覺得要是他沒有「死」,一定不會錯過,案情便會得到水落石出了。柯南.道爾也沒有,像不少其他偵探小說的作者一樣,創造另一個偵探*。在他筆下,只有一個偵探,就是福爾摩斯。這是他對福爾摩斯的尊重,潛意識裏面覺得,偵探除了福爾摩斯外,不作他人想;沒有了福爾摩斯,很多案件也就沒有人能夠偵破。
儘管擺脫了福爾摩斯十年,其間寫了不少其他優秀的作品,包括和偵探小說同類的作品,柯南道爾在文學上,始終得不到他希望得到的尊重。其他沒有福爾摩斯的懸疑小說作品,也遠不及福爾摩斯探案的受讀者歡迎。1903年,他不得已,只好讓福爾摩斯復活,以後,再多寫了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三十二篇短篇,一篇長篇,最後一篇發表於1926年,他逝世前四年。不過,我覺得他輸了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心中始終是有點不忿的。
柯南.道爾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今日讀過的人不多,中國的讀者就更少了。在這裏,我選譯了八篇他寫的,不是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懸疑小說。三篇是寫於《猩紅的習作》——第一部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小說之前。
第一篇,〈那個小四方箱〉(That Little Square Box),1881年發表於《倫敦社會》雜誌(London Society),是柯南道爾最早的作品之一。比它更早的作品有三篇,兩篇帶有神怪的情節,在此不選。另一篇〈與無政府主義者同過的一夜〉(A Night With the Nihilists)也是1881年在《倫敦社會》發表,較〈那個小四方箱〉早幾個月。雜誌的編輯很欣賞這兩篇作品,還去信鼓勵柯南.道爾棄醫從文,不要埋沒了他寫作的天份。這裏選譯〈那個小四方箱〉,因為故事的幽默風趣,在他其他的作品裏面很少見得到。敍事的活潑傳神,情節的引人入勝,與他後來成熟的作品不遑多讓,這篇作品,雖然並沒有惹起太多人的注意,卻是我在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歡的三四篇之一。
第二、第三篇:〈出租馬車車夫的故事〉(The Cabman’s Story)發表於1884年,〈偉奇大叔的回憶〉(The Recollections of Captain Wilkie)發表於1895年(雖然出版日期很晚,但一般人認為寫成的日期,大概不會早於1885年)。兩篇文筆都很生動,但沒有甚麼情節。選在這裏,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故事,讓我們看到柯南道爾作品是怎樣取材的——他把道聽途說得來的故事,增刪潤色,寫成小說,所以他的作品,雖然離奇曲折,真實感還是很強。今日,很多人喜歡克里斯蒂的作品,但和柯南道爾的比較,她的作品未免叫人感到只是故弄玄虛,閉門造車的猜謎遊戲。
不少讀者知道,柯南.道爾在愛丁堡醫學院的老師,約瑟.貝爾教授(Professor Joseph Bell1837–1911)是福爾摩斯的原型。〈偉奇大叔的回憶〉,除了故事生動有趣外,開始一段應該是貝爾教授的寫真,而故事裏面的我,也應該是柯南.道爾的夫子自道。在這裏選譯給讀者參考。
接下來的五篇寫在1898–1899年,福爾摩斯死了,但還未復活的年間,選在這裏是讓讀者評斷,一般人忽略了柯南.道爾沒有福爾摩斯的作品是否合理,是不是他們的損失。除了〈新地下墓穴〉(The New Catacomb)1898年發表於《陽光年刊》(Sunlight Year Book)外,其餘四篇都是發表於《斯德蘭特》月刊,〈營火周圍〉系列(Round the Fire)。
〈新地下墓穴〉,〈巴西貓〉(The Brazilian Cat)和〈失踪的特別專車〉(The Lost special),尤其是前兩篇,我認為在柯南.道爾所有作品中堪稱上上之選,情節的譎詭、曲折,文筆的生動,描寫的細緻,氣氛的緊張,叫人不一口氣看完難以釋卷。在福爾摩斯的探案裏面,找不到幾篇可以及得上。上面提到過,從案件發生後,破案人的角度去寫,是很難給作者提供這種敍事,描寫的機會的。
〈古猶太的胸牌〉(The Jew’s Breastplate),〈黑人醫生〉(The Black Doctor),故事和福爾摩斯的探案最近似,裏面提到一些線索,令人覺得,如果福爾摩斯是故事主角,定可循此而破案。故事由當事人說出來,當事人的感情,心理變化的描寫,福爾摩斯探案裏面,曾不多見。
希望選譯的這八個短篇,能帶給讀者欣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