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縣
我六歲時,連狗都嫌,黃皮寡臉,頭髮稀得打不起一個辮子。頭腦遲頓,連過路收破爛的老頭都驚奇,最後,母親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餘。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鬥鬧騰無人管,從三峽巫山農村回家,住了一陣子。不知為什麼事與母親大吵一頓,發狠說是要回鄉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說是行李,也不過是將家裏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個星期天,母親在堂屋裏悶坐了好久,突然對大姐說,你要走,那就順路把六六帶回我的老家忠縣吧。
後來我才明白母親心裏想的是什麼,她一直嘗試著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讓我試試能否討鄉下哪個親戚喜歡,算是對我降格以求。母親沒有告訴我她的陰謀,但是我感覺到她不要我,因此對離開這家好不好,也全然不當一回事。
那個春末,天氣已經暖和了,我跟著大姐坐輪船。那是第一次出遠門,母親一直把我們送到江邊輪渡口。她的樣子很漠然,我不理母親,大姐也沒好臉色給母親看。母親掉頭走得很快,大姐拉著我的手走得更快,上渡船過江,然後再去轉大輪船。
記得坐的是底艙,鐵板地面,機器隆隆,與許多擔扁擔背東西的人擠一塊。到忠縣縣城,已是深夜。大姐說已經晚了,最便宜的旅館我們倆人付一個統鋪位,花那錢也不值。結果她費了好多口舌,被允許在碼頭躉船上的凳子上過一夜。我們兩人擠在一起,搭了件衣服湊合著到天亮,然後我們坐第一班長途汽車,再趕山路,看著長江在眼前不斷地消失,又不斷地出現,一直到我膩透了任何風景,才聽到村子裏的狗吠亂叫,大姐說到了。
大姐把我送到忠縣鄉下,住了兩夜自己就回巫山去了。那時我以為這兩個地方都在長江邊,離得近,大姐會來看我,後來會查地圖了才知道遠著,她就是把我一個人撂下來狠心走了。大姐當知青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巫縣小三峽。她落戶的地方就是後來作為文化保護的大昌古鎮。
母親的家鄉關口有個石寨,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石頭砌的,沒人說得清是什麼時候的建築。老人說起碼明清時就有了,說是張獻忠打到過這兒,蠻族女將秦良玉把關,殺得個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守和攻相持不下。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崗亭,全由整塊大青石而築,但年久風化,石頂全坍了,前院的石縫裏生滿野草。村子裏用來開露天群眾大會或曬糧食什麼的,牆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草人手裏還塞了一把芭蕉扇,風一吹,扇子就動,嚇唬來偷吃糧食的麻雀。這古老的石寨,在村口池塘邊,透過樹枝就望得見,算是這個「關口」村的歷史見證。後來我恨這地方的一些人,就認為他們都是反動分子秦良玉的後人,再後來我恨這地方的那些人,就覺得搭們應當是張獻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種。
我先在大舅家落腳,大姐嫁給了大舅的大兒子,大舅同時也是大姐的公公,大舅媽在大饑荒餓死,一直未娶,他們生有三兒一女。二舅與大舅家的兩間平瓦房連在一起,各有草屋和搭的豬圈,豬圈邊就是茅房,幾根樹樁釘在一起,四周是麥折芭。
我的到來,讓這個一向平靜的寨子掀起波瀾,整個村子的人都來到大舅前看城裏的「小姐」是什麼樣?這裏幾沒有從大城市來的親戚,倒是有人出去過,比如我母親當年逃婚,一出去就難回來。這兒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時,那也是天垮下來的絕境,如果數一下村裏去過大城市的人,那就是我這兩個舅舅。他們在我未出生前,抬著重病快死的母親,也就是我外婆,去重慶交給我母親,送到了就趕快回轉。
那些看稀奇的村裏人失望極了:屋子裏站著一個瘦瘦小小的女孩,滿頭黃毛,眼睛充滿恐懼,而且半天都不說一句話,也沒有笑臉,穿得幾乎和他們一樣破舊。也拿不出任何禮包,這裏連農村人走親戚,都要帶自做的麻花或紅糖。可我什麼也沒有帶,母親只想把我從她身邊趕走,完全沒有想到這些細節。那些人很快就散了。當晚我和小姐姐一起睡。
有一天么姨來關口接我,她離得比較近,翻了兩匹山過了三條溪溝就到了。么姨長得不像母親,五官較小,瞇瞇眼,個子也小。她沒有兒女,丈夫在煤礦挖煤,經濟情況比舅舅門好一些,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膽,害怕丈夫被炸死,因為這小煤礦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坍方、瓦斯爆炸,死人是經營小煤礦預算的一部分。
么姨坐下沒一會兒,拉著我的手就落淚,我沒有辦法讓她停,就跟著她哭,我哭的是自己被重慶城裏的母親拋棄,一輩子就留在這偏遠的農村。我一哭,么姨就停住哭,帶我到小河溝去搬螃蟹。
那天遇見一條大花蛇,我嚇壞了,么姨竟和那蛇對視,而且拾了一石子,拋上半空,嘴裏念念有詞。那蛇身子伸得很高,但費勁地彎過腦袋去看那石子,最後整個身體垮倒在地上,一溜煙不見了。我從驚嚇中緩過勁來,問么姨怎麼一回事?她說,遇見那種蛇,就要比高矮,若拋出的石子高到連蛇抬起頭都看不見,蛇就會饒了我們。
我在么姨那兒住了很久,有天表姨來么姨家,說是有事耽擱,不然早就來接我了。她生得白淨,不像風吹日曬的農婦,頭髮在腦後綰得整整齊齊,穿得也乾淨。總之,我當時一下子就被她的端正模樣吸引住了。么姨捨不得我走,但表姨態度很堅決,說以前我母親在鄉下時與她最要好,現在母親把她的麼姑娘送到鄉下來,能不管嗎?不過她們在屋裏商量了一天,最後達成協議,我先去她那裏,然後再回來。
表姨那兒很遠,就在長江邊的豐都鬼城附近。我們走了一天山路,她走路不快,因為她說小時家裏對她期望太高,要嫁個好人家,被纏了腳。她實在受不了,就悄悄放腳,被家裏發現,狠狠打了一頓,重新纏腳,但又被她放了。這麼折騰過幾次,那雙腳就不成樣子了。我們一路說著話,等到她家天就黑盡了。表姨是第一個打開我話匣子的人,她喜歡問我,我也喜歡問她,關於重慶城裏的事,她最感興趣。
她說很後悔,當初應該跟你媽一起跑到重慶,哪怕做紗妹,也比在農村強。
我問她為什麼不走呢?
她說有些東西丟不下。
問她什麼東西,她笑笑,說你小娃兒,你不懂,有一天你懂了,表姨再講給你聽。
表姨爹已經做好玉米稀飯等我們。比起其他親戚,表姨家的房子最像模像樣:石頭房子,屋頂很高,其實就是一個舊時雕堡。解放那陣分田分地時,那個石房子裏炸死的國民黨士兵太多,邪氣太沖,沒人敢要,就分給了她家。此後,她遇到來村裏做石匠的表姨爹,她被招做上門女婿。
表姨告訴我這個故事,說她自己八字大,壓得住邪。她的話我相信。在重慶南岸家裏的閣樓上,我總看見一個白衣女鬼,家裏三個姐姐也都看見過,只是我見到次數最多,所以最有理由怕鬼。可是在這小石屋裏,一次也沒有看見什麼可怕的東西,也沒有聽到什麼怪聲音,看來只要陽氣足,鬼屋不是個壞地方。
表姨門前有一棵李子樹,我來沒幾天,這棵李子樹就開滿花朵。記得天天爬到李樹上,遠遠看表姨爹從村口那個山道回家來,肩上扛著一個布袋,裏面是錘頭、鑽子、剁斧之類的工具,他們抱養了一個孤兒,比我大五歲。十一歲就跟村裏全勞力一樣下田。
生產隊隊部的院子在一個窪地。我們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見。有一天生產隊長來動員表姨去鬥地主。表姨說,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時已經被槍斃了嗎?我不跟魂鬥。
生產隊長說,不是老地主,是少爺,附近的知青說是國家要搞的。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樣,是在文革前就到農村去的,這麼些年生活寡淡無味,終於輪到「革命」的機會了。
少爺?解放那陣子他才四歲,鬥他?表姨說。
生產隊長說,你以前在他家當過丫嬛,你最知道他家怎麼欺壓我們窮人。所以,你一定要鬥。
隊長走後,表姨很難過。她說,她在地主家時,一家子對她不錯。再說那少爺就是小時看見父親被敲了沙罐斃掉,嚇得半死,變成精神病的。
表姨在家裝病,被隊長狠狠罵了一頓,不過也拿她沒辦法,她是地地道道的貧農出身。
我那天跑下山坡去,隊部的院子熱熱鬧鬧,天井和堂屋裏站著人,坡上也坐了不少人,拖兒帶女的。那個地主的少爺被押上來,一個瘦高個兒青年,衣服又破又髒,頭髮長得不男不女,但一臉漠然,別人罵他,他笑;別人數他罪狀,他笑;有知青上台階去搧他耳光,他也笑。直到後來把他鬥垮在地上,才算收場。
我跑回屋裏對表姨講那裏發生的一切。表姨說,我就知道會這樣,這個孩子活不長,老天爺,觀世音菩薩,行個好吧,讓他平安吧!她的樣子非常傷心。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表姨爹說是要帶我去一個工地,那兒差石匠,而且離鬼城冥府不遠。他一早帶上我,我就在工地等他做完事,然後他帶我往街上走。他指著山頂那些若隱若現的房子說,那是陰間地府,凡是人死了,都到那裏報到,做善事的升天或投個好人家,做惡事的,得下地獄下油鍋,受各種慘不忍睹的酷刑,永世得不到翻身。
我害怕又嚮往。那條鋪了青石塊的街,兩邊全是一兩層的房子,往山上走的小路真是鬼氣森森。但是爬了一半山,表姨爹忽然改變主意,不帶我上去。說小孩子看不好,女孩子看了更不好。
我不敢反對。
下山後,街上擺出小攤,都點起油燈,賣煮熟的紅辣子雞塊,說是雞避邪。他買了一個雞頭,叫我立即就吃。然後拉著我的手就走,說趕快,趁天還未黑,若天黑了,街上不會有人,全閉門閉窗。表姨爹帶我搭了一艘船,是一個拖輪,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我們上岸,重新走山路回村子。
長大後我去過那鬼城冥府好幾次,就在重慶下游豐都縣的長江北岸上。古木參天,有些古廟,神宮古石刻,非常特別。奈河橋得一步跨過才順當,還有鬼門關、黃泉路和十八層地獄,每隔幾年修些新玩意添些新顏色。最後一次把我嚇了一跳,對面整匹山修了供觀光的種種傳說中的景物,還有天堂仙境,玉皇大帝嶄新的雕像佔了半山,在長江上就可見到,好像發揚正氣,壓倒邪氣。那條古樸的街也越來越商業化。
記得那一夜表姨一直在怪表姨爹膽小。但是第二天,表姨就去山裏摘回艾嵩菖蒲,幾枝掛在門口,幾枝拿在手上點火燒,在我周身來回熏煙,熏得我只有閉上眼睛,淚直流。表姨用雄黃酒灑在門口窗子,說不然鬼會纏住我,這樣做過後,鬼會自動離開,知道認錯了人。為了保險,她在太陽下山後,叫我學她的樣,對著東山連連吐三次口水,然後跪在地上,對著西天磕三個頭。
天還漆黑,生產隊長就站在院門前叫出工了,等他們上了地裏,公雞才叫。
在表姨這兒,她讓我幫她扯線子,一件舊毛衣。我得邊扯邊繞在一個木凳上,紮成一束,洗了再重新織。毛衣,表姨織了兩件,一件給她的兒子。一件想必是給表姨爹的。那天晚上我已經躺在床上睡了,她的兒子也睡了,表姨爹還未回來。我看見她拿著毛衣,包著一些吃的就往外走。她走得很秘密,可我還是發現了。跟在她後面。我發現她竟然是去村邊的土屋。裏面住的就是那個被鬥的少爺。少爺見了她也不傻笑,眼睛盯得直直的,不過兩人沒有說話。
怕表姨發現,我就獨自回了,之後也沒敢問表姨。
那時每天我和當地孩子一樣去山上拾柴和打豬草剁豬草。每天吃晚飯很早,每家戶如此,為了省煤油燈,有時農田活忙了,吃飯晚了,就燒著麥桔桿和枯草,取爐火照明洗菜做事。往往一屋子都是煙,熏得人直咳嗽。
晚上一盞小油燈早早就吹熄。
第二年清明節很快就到了,我們幾家人到關口後山上給外婆外公上墳。一路上扔野菜團子,說是打惡狗餅,每人頭上繫根白布條,表示孝敬,祖宗保佑著,凡有厄運來臨,必先顯靈,讓後輩逃脫。他們剪了好些紙人紙馬紙牛羊,還糊紙房子紙床,在墳前燒掉,說是這樣親人在陰間可享受。
上完墳回來,我留在二舅家,他說要帶我去大石寨。我以為是村子裏的石寨,說我自己就去得。二舅說,村裏的是小石寨,江邊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邊山崖邊上,有十二層,高入雲裏。可是二舅給春耕病倒了,二舅媽就讓村裏一個遠房親戚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說沒去對了,因為那個地方早就被「鬧革命,破四舊」的知青封了,裏面的菩薩早就被砸得稀爛。
那個夏天結束的時候,表姨就在把家裏碎布收集起來,用麵粉漿糊,抹在碎布上,做布殼,她將布殼剪下修鞋樣,每天吃飯前趁著天光紮幾針。
那是八月的一個大太陽天,有人帶口信來:大舅接到二姐代母親寫來的信和路費錢,讓么姨送我回重慶上學。那一天我把村子跑了一個遍,最後我抱著表姨哭起來,表姨說,「乖女,你媽哪個會不要你。我就一直不信這點。」她也哭了,說真捨不得我離開。但是她為我能回重慶大城市而高興。
她和表姨爹把我送回關口,那天傍晚么姨也趕來了,她們一人拿出一支紅布鞋,紮得結結實實,么姨做的右腳上還繡了兩朵小小的豌豆花。她們讓五伸出腳來試,大了一些,說是要這樣,我腳長得快,上二年級還能穿。不過么姨說不全是她做的,因為她眼睛不好,二舅媽也紮了幾針。
我問怎麼一直不知道她們在為我做鞋子呢?
她們說心裏有這個預感,她們去神龕許了願的,這樣穿鞋的人才會一路平安,紅色也是圖個吉利,能走到天邊,越遠命就跟以前不同,起碼比她們的命好。
一群女人在大舅屋裏鬧嚷嚷時,二舅把我叫出來,偷偷塞給我十塊錢,我知道十塊錢是個大數字,我手中從來沒有捏過錢。所以說什麼也不要。但是一向好脾氣的二舅說,你不要,等一會就把你捆在屋裏,不讓你走。
我嚇壞了,趕緊收下。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到重慶,我把這錢交給母親,母親拿著錢眼淚就流出來。
么姨在重慶城裏很不習慣,她放心不下丈夫,就回去了。她走了,我的衣袖上還插了一根穿著線的小針,看著父親的鈕扣掉了,我就趕快縫上。家裏哥姐笑話我,不准我把針插在袖子上,認為這是鄉巴佬的作法,硬把針取走了。那雙紅布鞋,我從鄉下一直穿到城裏,穿到小學裏,同學圍著那雙鞋子看,手工做的,即使做得細工細活,他們也笑個不停。不過我不在乎。我的腳長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穿不了,剪掉後半截做拖鞋。等到我上初三那年,有一天我與姐姐下長江洗衣服,那雙鞋子就順水漂走了,我追不上,一個漩渦就吞沒了它們。
我很傷心。有一天晚上我夢見我回到關口,可是一個人也不認識。我跟著那下山的路,去找豐都的表姨,可是表姨也不在。過了幾年母親告訴我,表姨去世了,先是那少爺生病死了。一直到那時,我才知道,那少爺就是表姨的親生兒子,ㄚ頭生的,所以一直沒法說。一解放,她更不敢相認,那親生的兒子還很小,親眼看見父親及一家人被槍斃,嚇出病來。表姨就只好一直瞞下去。表姨臨死前才告訴么姨,么姨來重慶才說給母親聽,兩個女人關在房裏落了好多淚。
我是後來才明白,母親鄉下的親人是看在母親的面子上收留我,每家都困難,多一張嘴吃飯,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大家達成協議,每家分擔。
大姐是個大嘴巴,想必早就給我的親戚說清我是私生女的來歷,可是在那裏,他們就當什麼都沒有過,對我比對他們自家的孩子還好,如果只有一個葉兒粑,他們都寧肯自己不吃,讓給我吃。
如果我的母親不是突發愛心,把我從農村接回重慶城裏,讓我上學識字,我恐怕也就是一個農村婦女,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世界最不少的就是詩人作家。但對我個人而言,命運就不一樣了。我的三峽親戚們再好,在中國也是三等公民。母親若把我留在那裏,我現在也跟著因三峽大壩拆遷到新地,每天做農田,現在已經給孫子納鞋底了。
寫到這裏,我就非常害怕。
現在忠縣有一半在水中,每每坐船經過,心裏難過。想起小時聽過的故事,有一家人避逃災難,得到祖宗幫助,靠一張毯子沉入湖底。昔日鄰居想向這家人借一格犁耙。就對著湖連叫三聲他們家裏人的名字,我想借一個犁耙,不一會犁耙就升上湖而來。
如果真有先祖鬼魂,那麼有一天,當我也對著那個全世界的超級大湖,連連叫上三聲我那些親人的名字,那雙么姨親手納的紅布鞋會升上來嗎?那個沉在水底的村莊,那個小石寨,那個大石寨,我六歲時經歷的世界,在我整個灰暗的童年就像一線光,這一切都會露出水面嗎?
不管怎樣,清明快到,我該回到故里,順水放上些花,就是那雙紅布鞋上的豌豆花,讓花瓣沉沒到我的三峽親戚們的手裏。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自我教育(53種離別)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8 |
社會人文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自我教育(53種離別)
有一本書寫着一個人的過去,那太完美的過去,總難與今生相連。我在茫茫的夜裏,把一個個夢留給那本書,閉上眼睛,想像我的身影如貓一樣在夜裏來回走,彷彿在象棋格裏穿越,我沒驚動任何人。
本書是著名女作家虹影,以離別為主題的自傳體作品。虹影的寫作一本又一本總像重磅炸彈引發種種議論。在虛構和真實生活之間,她說所有的議論是因爲虹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爭議,非婚女身份、私生女的身份,注定了其寫作是這樣的,私生女和別人不同,因爲私生女不是婚姻的結果,而是絕對的愛情結晶,對情與性到了狂熱的程度。
若說虹影以前的作品是虛構,這本新書《自我教育》更拉真實。說到生活遠比小說更像小說,但是也更殘酷。小說家只是將生活的一種狀態用藝術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們讀得出來,因爲真實的生活表述出來後,變得更加猙獰可怕。
作者簡介:
虹影
享譽世界文壇的著名作家、詩人、美食家。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長篇《好兒女花》、《饑餓的女兒》、《K――英國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術師》等、詩集《沉靜的老虎》、散文《小小姑娘》等。現居北京。六部長篇被譯成30 多種文字在歐美、以色列、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出版。她的許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曾獲紐約《特爾菲卡》雜誌「中國最優秀短篇小說獎」、長篇自傳體小說《饑餓的女兒》曾獲臺灣1997 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K-英國情人》被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評爲2002 年Books of the Year 十大好書之一。2005 年獲意大利「羅馬文學獎」。2009 年被重慶市民選爲重慶城市形象推廣大使。
章節試閱
忠縣
我六歲時,連狗都嫌,黃皮寡臉,頭髮稀得打不起一個辮子。頭腦遲頓,連過路收破爛的老頭都驚奇,最後,母親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餘。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鬥鬧騰無人管,從三峽巫山農村回家,住了一陣子。不知為什麼事與母親大吵一頓,發狠說是要回鄉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說是行李,也不過是將家裏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個星期天,母親在堂屋裏悶坐了好久,突然對大姐說,你要走,那就順路把六六帶回我的老家忠縣吧。
後來我才明白母親心裏想的是什麼,她一直嘗試著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
我六歲時,連狗都嫌,黃皮寡臉,頭髮稀得打不起一個辮子。頭腦遲頓,連過路收破爛的老頭都驚奇,最後,母親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餘。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鬥鬧騰無人管,從三峽巫山農村回家,住了一陣子。不知為什麼事與母親大吵一頓,發狠說是要回鄉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說是行李,也不過是將家裏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個星期天,母親在堂屋裏悶坐了好久,突然對大姐說,你要走,那就順路把六六帶回我的老家忠縣吧。
後來我才明白母親心裏想的是什麼,她一直嘗試著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
»看全部
目錄
忠縣
星星閃爍
父親
十二歲
紅色筆記本
1095天
珂賽特
北京
大姐與二姐
天使
女孩
島國
英語教師
新加坡
少女
夜貓子家族
卡夫卡
蕭邦
馮涅格特
爪哇
粉絲
保羅
埃萊娜
旅館
樓梯
朋友
舞台
另一個女人
火車
靈山
詩人
阿多米
憂鬱症
威尼斯
上海
鬱金香
愛美者
姐妹
紙牌
夜市
雅加達
尼泊爾
千島國
喜馬拉雅山
老城牆
插花女
不明身份
弗里達
夫差
少年
水庫
馬爾他
香港
星星閃爍
父親
十二歲
紅色筆記本
1095天
珂賽特
北京
大姐與二姐
天使
女孩
島國
英語教師
新加坡
少女
夜貓子家族
卡夫卡
蕭邦
馮涅格特
爪哇
粉絲
保羅
埃萊娜
旅館
樓梯
朋友
舞台
另一個女人
火車
靈山
詩人
阿多米
憂鬱症
威尼斯
上海
鬱金香
愛美者
姐妹
紙牌
夜市
雅加達
尼泊爾
千島國
喜馬拉雅山
老城牆
插花女
不明身份
弗里達
夫差
少年
水庫
馬爾他
香港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虹影
-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3-01-01 ISBN/ISSN:97801939928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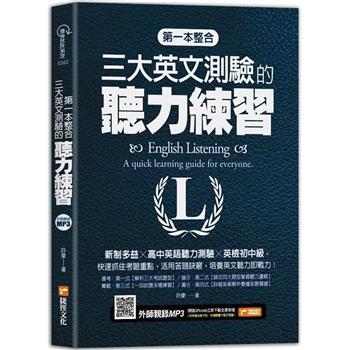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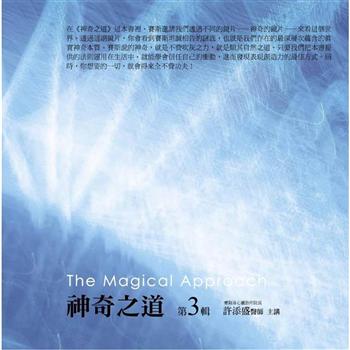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