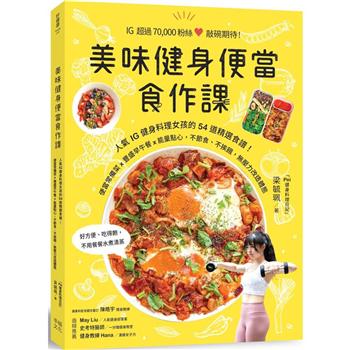世上有許多曾經在於某處、此刻在於某處、將來或者在於某處的人,我們不曾聽說、無緣識荊,甚而至於,將來也永遠不會知道。也有一些人,曾經的下落頗有疑問,此刻的蹤影不易找尋,將來的行藏更是無從預期,然而,我們對他們非常熟悉,熟悉其相貌、熟悉其性情、熟悉其一顰一笑、熟悉其一言一語,熟悉到想用自己的心思和力氣,為他在身邊的世界裏找一個篤定的位置。比如歇洛克.福爾摩斯。
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裏,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陸續寫下了這些他自己並不看重的文字。一百多年以來,數不清的讀者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喜歡上了他筆下的這位神探,喜歡上了神探的醫生朋友,喜歡上了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昏暗街燈,喜歡上了風光旖旎的英格蘭原野,喜歡上了各位蠢笨低能的官方探員,甚至還喜歡上了神探的頭號敵人、智力與他一時瑜亮的莫里亞蒂教授。更有一些讀者對神探的演繹法如醉如癡,不遺餘力地四處尋覓他和他的朋友在現實中留下的蛛絲馬跡,以至於最終斷定,他和他的朋友實有其人,柯南.道爾爵士反倒是一種偽託的存在。
神探的身影在各式各樣的舞台劇、電視和電影當中反復出現,又在萬千讀者的記憶之中反復縈迴。我們真的應該感謝柯南.道爾爵士,感謝他不情不願寫下了這樣六十個故事,為我們的好奇心提供了一座興味無窮的寶山。六十個故事如同一幅斑斕的長卷,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另一個民族在另一個時空的生活,窺見一個等級森嚴卻依然不乏溫情的社會,窺見一個馬車與潛艇並存的過渡年代,窺見一個又一個雖欠豐滿卻不失生動的人,窺見一鱗半爪,商品化程度較低的人性。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福爾摩斯全集(卷一)的圖書 |
 |
福爾摩斯全集(卷一) 作者:亞瑟.柯南.道爾爵士 / 譯者:李家真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3-1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298 |
小說/文學 |
$ 537 |
文學作品 |
$ 632 |
中文書 |
$ 632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英國小說家,因塑造歇洛克.福爾摩斯而成為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作家。《福爾摩斯全集》被譽為偵探小說中的聖經,除此之外他還寫過多部其他類型的作品,如科幻、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戲劇、詩歌等。柯南.道爾1930年7月7日去世,其墓誌銘為「真實如鋼,耿直如劍」(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
柯南.道爾一共寫了60個關於福爾摩斯的故事,56個短篇和四個中篇小說。在40年間陸續發表的這些故事,主要發生在1878到1907年間,最後的一個故事是以1914年為背景。這些故事中,有兩個是以福爾摩斯第一人稱口吻寫成,還有兩個以第三人稱寫成,其餘都是華生(John H. Watson MD) 的敍述。
譯者簡介
李家真
1972年生,曾任《中國文學》雜誌執行主編、《英語學習》雜誌副主編、外研社綜合英語事業部總經理及編委會主任,現居北京。譯者自序:「生長巴蜀,羈旅幽燕,少慕藝文,遂好龍不倦。轉徙經年,行路何止萬里;耽書卅載,所學終慚一粟。著譯者若為簡冊,或可等身;諷詠倘刊金石,只足汗顏。語云:非曰能之,顯學焉。用是自勵,故常汲汲於文字,冀有所得於萬一耳。」
序
序
福爾摩斯及其他(代譯序)
世上有許多曾經在於某處、此刻在於某處、將來或者在於某處的人,我們不曾聽說、無緣識荊,甚而至於,將來也永遠不會瞭解。對於我們來說,他們的離合悲歡,他們的喜怒哀樂,既不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也不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更不是銘心刻骨的記憶,僅僅只是,並不存在的虛空,如此而已。
也有一些人,曾經的下落頗有疑問,此刻的蹤影不易找尋,將來的行藏更是無從預期,然而,我們對他們非常熟悉,熟悉他或者她的相貌、熟悉他或者她的性情、熟悉他或者她的一顰一笑、熟悉他或者她的一言一語,熟悉到想用自己的心思和力氣,為他或者她在身邊的世界裏找一個篤定的位置。
這些人當中,就有歇洛克.福爾摩斯。
他也許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也許住在某條真實街道當中的某間虛擬公寓,也許擁有凡人難以企及的高超智力和凡人難以認同的智力優越感,也許擁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可欽信念和「無藝術即無意義」的可疑立場,也許擁有視邪惡罪行如寇仇的俠肝義膽和視他人疾苦如無物的鐵石心腸,也許擁有最為充沛的精力和最為怠惰的習性,也許刻板自律,也許佻脫不羈,也許是最不業餘的業餘偵探,也許是最不守法的法律衛士,也許擁有一個滋養思維的黑陶煙斗和一隻盛放煙草的波斯拖鞋,也許擁有一件鼠灰色的睡袍和一堆孤芳自賞的古舊圖書,也許,還拉得一手可以優美醉人也可以聒噪刺耳的小提琴......
他自己說:「我的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逃亡,為的是擺脫平淡庸碌的存在狀態。」 (《紅髮俱樂部》)同時又說:「生活比人們的任何想像都要奇異,人的想像根本不能與它同日而語。」 (《身份問題》)也許,就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他才會讓我們如此難以忘記,因為我們偶爾也會厭倦「平淡庸碌的存在狀態」,偶爾也希望看到生活之中的種種奇異,畢竟,連他的忠實朋友華生都曾經忿忿不平地對他說:「除了你之外,其他人也有自尊,搞不好還有名譽哩。」(《查理斯.奧古斯都.米爾沃頓》)
也許,文學形象之所以可以比血肉之軀更加動人,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告訴我們,人生之中,終歸有其他的一些可能。無從逃脫的此時此刻之外,終歸有一個名為「別處」的所在。
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裏,柯南.道爾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陸續寫下了這些他自己並不看重的文字。一百多年以來,數不清的讀者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喜歡上了他筆下的這位神探,喜歡上了神探的醫生朋友,喜歡上了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昏暗街燈,喜歡上了風光旖旎的英格蘭原野,喜歡上了各位蠢笨低能的官方探員,甚至還喜歡上了神探的頭號敵人、智力與他一時瑜亮的莫里亞蒂教授。更有一些讀者對神探的演繹法如醉如癡,不遺餘力地四處尋覓他和他的朋友在現實中留下的蛛絲馬跡,以至於最終斷定,他和他的朋友實有其人,柯南.道爾爵士反倒是一種偽託的存在。
神探的身影在各式各樣的舞台劇、電視和電影當中反復出現,又在萬千讀者的記憶之中反復縈迴。我們真的應該感謝柯南.道爾爵士,感謝他不情不願抑或半推半就地寫下了這樣六十個故事,為我們的好奇心提供了一座興味無窮的寶山。六十個故事如同一幅斑斕的長卷,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另一個民族在另一個時空的生活,窺見一個等級森嚴卻依然不乏溫情的社會,窺見一個馬車與潛艇並存的過渡年代,窺見一個又一個雖欠豐滿卻不失生動的人,窺見一鱗半爪,商品化程度較低的人性。
忝為這套巨帙的譯者,我喜歡作者時或淋漓盡致時或婉轉含蓄的文筆,更喜歡浸潤在字裏行間的浪漫精神,尤其喜歡的是,這種浪漫精神的兩個化身。人的浪漫,是真正懂得人的可貴在於人本身,男女之間的浪漫,何嘗不是如此。
以我愚見,如果說福爾摩斯代表.驚世駭俗的才能和智慧,華生就代表著驚世駭俗的理解與寬容,兩樣稟賦同樣難得,兩個妙人同樣可喜,他們兩個在文字的國度裏風雲際會,我們就看到了一段無比浪漫的不朽傳奇。
再寫下去,恐怕會破壞閱讀的趣味。止筆之前,請允許我引用一個經久不衰的笑話作為結尾:
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和華生醫生一起到郊外露營。享用完一頓美餐和一瓶美酒之後,他倆鑽進了帳篷。
凌晨三點左右,福爾摩斯推醒華生,如是問道,「華生,你能不能抬頭看看天空、再把你的發現告訴我呢?」
華生說道,「我看到了億萬顆星星。」
福爾摩斯接著問道,「很好,你從中演繹出了甚麼結論呢?」
華生回答道,「從天文學的角度來演繹,結論是宇宙中存在億萬個星系,很可能還存在億億顆行星。從占星學的角度來演繹,結論是土星升入了獅子座。從神學的角度來演繹,結論是上帝至高至大、我等至卑至小。從計時學的角度來演繹,結論是眼下大約是凌晨三點。從氣象學的角度來演繹,結論是明天的天氣非常不錯。你又演繹出了甚麼結論呢,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咬牙切齒地說道,「有人偷走了咱們的帳篷。」
這一次,我們的浪漫英雄終於看到了平庸至極的現實。
是為序。
李家真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