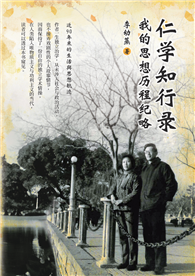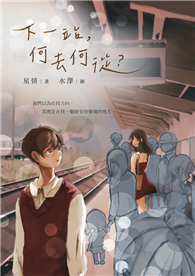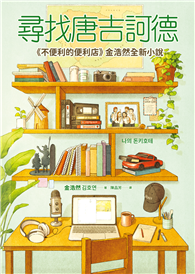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書 |
$ 246 |
中國歷史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2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
內容簡介
旗人入仕途徑多元,諸如恩蔭世職、充選侍衛,或考取筆帖式、內閣中書等,科舉僅是其中一種方式。杜祐寧從旗人應試制度談起,簡述旗人考試制度的建立與規定的調整,釐清旗人應試、除授、升遷等科舉入仕、任官的歷程。接著整理《題名錄》、《登科錄》、清人傳記等進士家族履歷相關史料,透過量化分析,觀察科場表現與家族政治、經濟環境的互動,呈現出清朝科舉與官僚結構、旗人群體之間的角力。最後進一步比較在京與駐防旗人的考試表現,釐清功名有無與旗人官員遷轉的關係,說明科舉對旗人、民人仕途的影響,具體論證旗人應試科舉時的優勢,以及清朝科舉「參漢酌金」的滿洲特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杜祐寧
2009年取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後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並取得學位,研究專長為清朝的科舉制度。著有〈幸出水火:清雍乾時期宗室隸屬包衣佐領的身分調整〉、〈同場一例:科舉制度與清朝旗人的仕途〉等學術論文。
杜祐寧
2009年取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後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並取得學位,研究專長為清朝的科舉制度。著有〈幸出水火:清雍乾時期宗室隸屬包衣佐領的身分調整〉、〈同場一例:科舉制度與清朝旗人的仕途〉等學術論文。
目錄
序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
第一節旗人考試辦法的建立
第二節旗人應試規定的調整
第三章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
第一節旗人應科舉的取中率
第二節旗人家族與科舉考試
第四章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
第一節旗人應鄉試的地域性
第二節旗人舉人的遷轉經歷
第五章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
第一節進士除授的旗民差異
第二節旗人進士與文武兼資
第六章結論
附錄
後記
徵引書目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
第一節旗人考試辦法的建立
第二節旗人應試規定的調整
第三章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
第一節旗人應科舉的取中率
第二節旗人家族與科舉考試
第四章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
第一節旗人應鄉試的地域性
第二節旗人舉人的遷轉經歷
第五章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
第一節進士除授的旗民差異
第二節旗人進士與文武兼資
第六章結論
附錄
後記
徵引書目
序
序
清朝皇帝宣稱,「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國的根本,旗人以精熟的騎射技能鞏衛政權,諸帝則在政策上給予旗人優遇,使之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特權。在國家採取旗、民分治的前提下,旗人獲得各種保障固為事實,但是其程度如何,以往多採「印象式」的描述,欠缺實證的研究。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加上史料數位化的進展,研究者得以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進行討論,當有助於釐清旗人的優勢所在,及其與民人差距的具體情形。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是讀書人進身之階,自隋、唐以降相沿不替,亦為歷史上統治中國的遼、金、元、清四個「征服王朝」所仿行。清朝任官,重視出身,以科舉出身者為「正途」,餘為「異途」;惟旗人入仕途徑多元,諸如恩蔭世職、充選侍衛,或考取筆帖式、內閣中書等,科舉只是一端。因此,清朝的科舉制度雖屬「清承明制」的一環,但加入旗人因素之後,另呈現「參漢酌金」的特色,探討旗人與科舉考試的關係,實不宜從漢人的舉業模式切入,也不能逕以特權保障概括。
清朝開科取士,始於順治二年(1645),國家對於是否開放旗人應試的規定幾經變動,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宣布准同漢人一體考試,以此進入仕途的旗人人數乃逐漸增多。論者以為,皇帝同意旗人與漢人同場競爭,是為展現族人的聰明才智實與漢人不分軒輊;或謂皇帝選任旗人官員,喜用有科舉功名者;或以旗人熱中應舉,是因制度設計與皇帝鼓勵所致,在在影響吾人對旗人投身舉業的認識。前人立論各有所據,然因旗人的錄取名額是與漢人分開計算,科甲旗人的仕途遷轉未必順遂,皇帝也不樂見旗人與文士爭名於場屋,凡此則既有觀點實有待進一步細究。
有關旗人以科舉入仕的議題,研究者先後不輟,貢獻良多,然多限於學術論文,而且取材不一,觀點互異,至於有系統的專著,迄今尚屬罕覯。本書是杜祐寧君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利用《題名錄》、《登科錄》和清人傳記等材料,採用量化分析方法,具體詳實地論證旗人在應試過程中的優勢,比較在京與駐防旗人的考試表現、科舉對旗人與民人的仕宦歷程的影響,以及功名有無與旗人官員遷轉的關係,所得結論具參考價值。著者不辭艱鉅,積數年之功,多方蒐羅,窮究盡微,在現有研究成果之上,益以個人創獲,對於學術研究當有貢獻。是為序。
清朝皇帝宣稱,「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國的根本,旗人以精熟的騎射技能鞏衛政權,諸帝則在政策上給予旗人優遇,使之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特權。在國家採取旗、民分治的前提下,旗人獲得各種保障固為事實,但是其程度如何,以往多採「印象式」的描述,欠缺實證的研究。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加上史料數位化的進展,研究者得以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進行討論,當有助於釐清旗人的優勢所在,及其與民人差距的具體情形。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是讀書人進身之階,自隋、唐以降相沿不替,亦為歷史上統治中國的遼、金、元、清四個「征服王朝」所仿行。清朝任官,重視出身,以科舉出身者為「正途」,餘為「異途」;惟旗人入仕途徑多元,諸如恩蔭世職、充選侍衛,或考取筆帖式、內閣中書等,科舉只是一端。因此,清朝的科舉制度雖屬「清承明制」的一環,但加入旗人因素之後,另呈現「參漢酌金」的特色,探討旗人與科舉考試的關係,實不宜從漢人的舉業模式切入,也不能逕以特權保障概括。
清朝開科取士,始於順治二年(1645),國家對於是否開放旗人應試的規定幾經變動,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宣布准同漢人一體考試,以此進入仕途的旗人人數乃逐漸增多。論者以為,皇帝同意旗人與漢人同場競爭,是為展現族人的聰明才智實與漢人不分軒輊;或謂皇帝選任旗人官員,喜用有科舉功名者;或以旗人熱中應舉,是因制度設計與皇帝鼓勵所致,在在影響吾人對旗人投身舉業的認識。前人立論各有所據,然因旗人的錄取名額是與漢人分開計算,科甲旗人的仕途遷轉未必順遂,皇帝也不樂見旗人與文士爭名於場屋,凡此則既有觀點實有待進一步細究。
有關旗人以科舉入仕的議題,研究者先後不輟,貢獻良多,然多限於學術論文,而且取材不一,觀點互異,至於有系統的專著,迄今尚屬罕覯。本書是杜祐寧君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利用《題名錄》、《登科錄》和清人傳記等材料,採用量化分析方法,具體詳實地論證旗人在應試過程中的優勢,比較在京與駐防旗人的考試表現、科舉對旗人與民人的仕宦歷程的影響,以及功名有無與旗人官員遷轉的關係,所得結論具參考價值。著者不辭艱鉅,積數年之功,多方蒐羅,窮究盡微,在現有研究成果之上,益以個人創獲,對於學術研究當有貢獻。是為序。
葉高樹
2022年2月12日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2022年2月12日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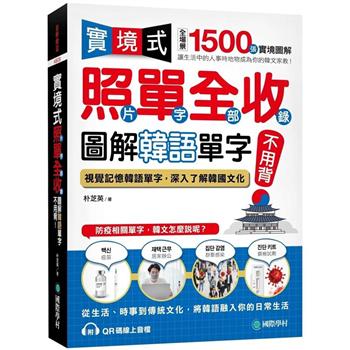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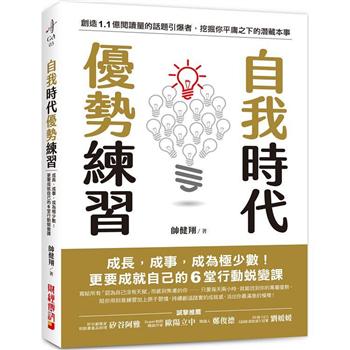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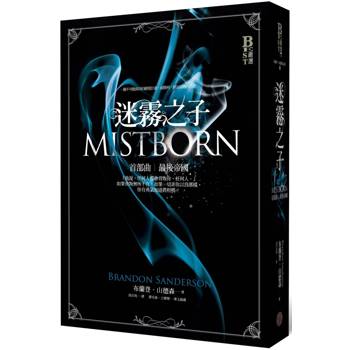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