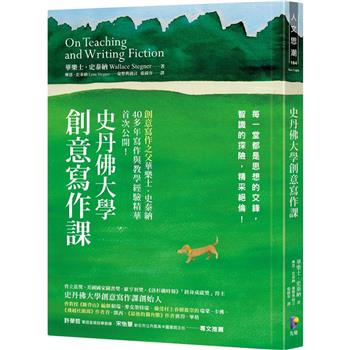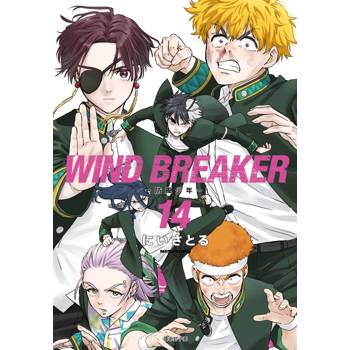改變了語言,是否就改變了面對世界的方式?
剝奪了語言,是否就剝奪了容身之處?
香港作家劉綺華第一部長篇小說
校長要求約聘中文教師伶與慧必須考過普通話的基準試,才有機會獲得續聘的資格。習慣以粵語教書的伶感受到威脅,處心積慮趕走慧。沒想到,慧以令人震驚的方式結束生命……
慧死了以後,沒人敢靠近她擺滿鏡子的座位,辦公室裡籠罩低迷的氣氛。伶接到媒體的電話,探問慧的死因,沒想到竟寫出對學校不利的報導。只是想要保有工作的伶,卻宛若慧的鏡像,投射出對生活的迷惘與憂慮。
不過是被要求換個語言教書,怎知道,這世界跟著變了樣?
各界好評
臺灣大學臺文所博士 路那 誠摯推薦
作家 韓麗珠
作家 陳浩基
作家 臥斧
劉綺華的《失語》,描繪了戰戰兢兢地生活,只關心自己前途的平凡人,如何在大環境下成為逼迫者與被逼迫者,攻守又是如何易位。她們不關心社會,只關心自己的前途,彷彿如此就能保得一生順遂平安。然而這道理應讓她們倖免於難的護身符,真的有這麼靈驗嗎?抑或,它只是還沒找到反噬的時機而已呢?──臺灣大學臺文所博士 路那
如果說文學是一種以虛構文本來記錄社會真實狀態的工具,《失語》絕對記錄了二〇一〇年代末期的現實香港。──香港作家 陳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