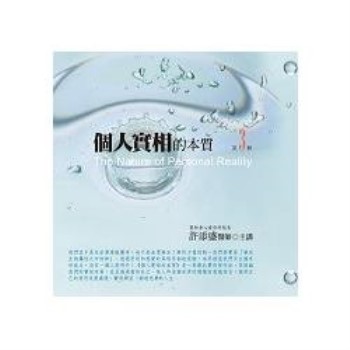這是一個寫在人類世時空下的樹豆多物種民族誌。樹豆是一個長於亞熱帶與熱帶區域的豆科植物,是全球主要的豆類雜糧之一。在台灣,樹豆主要出現在東部及南部原住民族以及六堆客家人的土地上;它近年也開始被賦予未來作物標籤,成為健康、文化與糧食安全的代表性作物之一。不過,樹豆是否真的帶來希望?本論文嘗試從物種而非人的角度,為樹豆架構世界。在這裡,混亂的感官性、共生的合作性以及中介的邊界性將會是貫穿其中的核心概念。
使用感官人類學的研究取徑,我在一位台坂部落老人家(vuvu)的農地上感受到了混亂與共生。這裡種植了樹豆和數十種其他的作物,在看似雜亂並堆著廢棄物的混作田中蓬勃生長。這塊田之所以混亂,是因為多數作物具有邊界性,而邊界區域的彈性與韌性讓物種得以相互合作與結盟。在混亂中,生產者作為排灣族人的文化規範,及自身的經濟、社會、生理以及情感等需求都得以被滿足。不僅如此,這塊混作田作為在地飲食系統的一部分,也提供在地族人日常飲食需求,透過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換與交易,田園的農產品也間接地、默默地支持著在地族人的食物主權(sovereignty)。本論文透過樹豆這個古老的作物,為排灣族在地農耕系統以及多物種民族誌多提供在地的範例,並以此說明樹豆的隱喻能為混亂與共生帶來希望的可能性。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樹豆知道:排灣族vuvu農地的混亂與共生的圖書 |
 |
樹豆知道:排灣族vuvu農地的混亂與共生 作者:林岑 出版社: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4-06-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79頁 / 15.5 x 21.5 x 1 cm / 普通級/ 全彩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樹豆知道:排灣族vuvu農地的混亂與共生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章 為什麼是樹豆?
一、為什麼是樹豆?
二、人類學的混亂與網絡理論
三、關於田野地:台部落與山上
四、研究框架、貢獻與限制
第二章 曖昧的樹豆史
一、樹豆的物種研究
二、台灣的樹豆
三、成為經濟作物
四、小結
第三章 混亂的美好生活
一、 尋找樹豆
二、 VUVU與山上的感官
三、 混亂的美學
四、 小結
第四章 食物與家、主權和邊界
一、 食物與家
二、 食物與主權
三、 重回混亂,看見邊界
四、 小結
第五章 樹豆知道
附 錄
參考書目
表目錄
表1 MUAKAI生命與事件表
表2 主要作物族語名與生長期
圖目錄
圖1 田野距離示意
圖2 台村農耕區
圖3 台排灣族人活動區域
圖4 樹豆世界分布地圖(SHARMA ET AL. 1981)
圖5 生物型共生固氮作用
圖6 耕田與部落的相對位置
圖7 輪作模式
圖8 混作田區概況
圖9 MUAKAI家族系譜
圖10 MUAKAI的種植邏輯
圖11 毛地瓜種植範圍
圖12 花生種植範圍
一、為什麼是樹豆?
二、人類學的混亂與網絡理論
三、關於田野地:台部落與山上
四、研究框架、貢獻與限制
第二章 曖昧的樹豆史
一、樹豆的物種研究
二、台灣的樹豆
三、成為經濟作物
四、小結
第三章 混亂的美好生活
一、 尋找樹豆
二、 VUVU與山上的感官
三、 混亂的美學
四、 小結
第四章 食物與家、主權和邊界
一、 食物與家
二、 食物與主權
三、 重回混亂,看見邊界
四、 小結
第五章 樹豆知道
附 錄
參考書目
表目錄
表1 MUAKAI生命與事件表
表2 主要作物族語名與生長期
圖目錄
圖1 田野距離示意
圖2 台村農耕區
圖3 台排灣族人活動區域
圖4 樹豆世界分布地圖(SHARMA ET AL. 1981)
圖5 生物型共生固氮作用
圖6 耕田與部落的相對位置
圖7 輪作模式
圖8 混作田區概況
圖9 MUAKAI家族系譜
圖10 MUAKAI的種植邏輯
圖11 毛地瓜種植範圍
圖12 花生種植範圍
序
推薦序
《樹豆知道:排灣族vuvu農地的混亂與共生》是建立在林岑的碩士論文基礎上,是近年來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最傑出的碩士論文之一,榮獲2022年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李亦園先生紀念論文獎」。這是一本試著從樹豆的角度觀看世界的多物種民族誌。本書充滿創新、饒富趣味且具有詩意,但這樣的嘗試是來自於樹豆的啟發,也深受種植樹豆的排灣族婦女的勞動和田園文化的薰陶。透過長期和排灣族vuvu在田裡工作,在彎腰、深蹲以及身體與土壤的相互作用中,林岑用身體感理解在排灣族混作田園中樹豆的存有意義,藉由樹豆的帶領,他認識多樣性的植物、動物、土壤、微生物、天氣,以及持續勞動的vuvu。
樹豆說話了嗎?人懂樹豆的話語嗎?樹豆可以成為報導人嗎?先打開書,讀讀看,或許風、樹、花、草都開始跟你互動了。在這本去中心化的多物種民族誌中,我看見了排灣族混作田園、在烈日中彎腰工作的vuvu,並理解樹豆和它的植物夥伴們在排灣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分享與食物主權實踐上的意義;也能讓人反思在當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經濟與永續環境的單薄想像。過往的排灣族研究大多從傳統人類學的視野出發,但這本書則提供了貼近土壤、從樹豆和女性勞動者的角度來理解排灣族,相信對排灣族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從這本民族誌中找到對話的可能。
林靖修(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樹豆知道:排灣族vuvu農地的混亂與共生》是建立在林岑的碩士論文基礎上,是近年來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最傑出的碩士論文之一,榮獲2022年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李亦園先生紀念論文獎」。這是一本試著從樹豆的角度觀看世界的多物種民族誌。本書充滿創新、饒富趣味且具有詩意,但這樣的嘗試是來自於樹豆的啟發,也深受種植樹豆的排灣族婦女的勞動和田園文化的薰陶。透過長期和排灣族vuvu在田裡工作,在彎腰、深蹲以及身體與土壤的相互作用中,林岑用身體感理解在排灣族混作田園中樹豆的存有意義,藉由樹豆的帶領,他認識多樣性的植物、動物、土壤、微生物、天氣,以及持續勞動的vuvu。
樹豆說話了嗎?人懂樹豆的話語嗎?樹豆可以成為報導人嗎?先打開書,讀讀看,或許風、樹、花、草都開始跟你互動了。在這本去中心化的多物種民族誌中,我看見了排灣族混作田園、在烈日中彎腰工作的vuvu,並理解樹豆和它的植物夥伴們在排灣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分享與食物主權實踐上的意義;也能讓人反思在當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經濟與永續環境的單薄想像。過往的排灣族研究大多從傳統人類學的視野出發,但這本書則提供了貼近土壤、從樹豆和女性勞動者的角度來理解排灣族,相信對排灣族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從這本民族誌中找到對話的可能。
林靖修(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