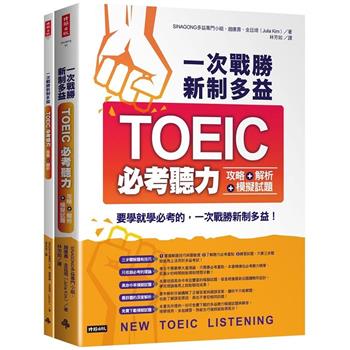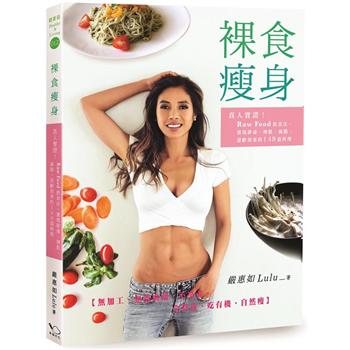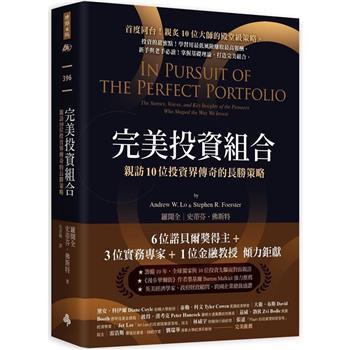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轉念就轉運,用心就開心。
★一位心理治療師的睿智人生思考,最想與親友分享的心靈禮物!
★2009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亞馬遜書店五顆星暢銷書,與《最後的演講》為讀者同時購買書籍。
★榮獲美國2008美好生活書獎(得獎書包括《最後的演講》《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知名網站「靈性和修為」評選為2008年最好的心靈書籍之一
用心活.用心愛.用心聽。一位心理治療師,三十年非凡人生,三十堂雋永課題,用心感動你。
「作為一個人的意義是什麼?」全美知名的心理治療師及談話節目主持人丹尼爾.戈特里布在最新作品《用心》的開頭如是問。而答案就在本書的字裡行間。
風靡了數百萬讀者及聽眾的丹尼爾,親切地講述了生命最深刻的教導是如何意外地來到我們的生活之中,身為一流的說故事專家,他帶給我們溫柔又感動的一課。
這些啟示來自於一位在自己生命過程中失去許多的作者。從三十三歲因脊椎神經受傷造成四肢癱瘓的那一刻起,丹尼爾發現自己面臨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在面對的問題。在重新建立其事業、家庭和生活的過程中,他發現到所有人類的共通點,包括渴望被愛、被理解及安全感。而他知道,生活的速度只會使我們的渴望離自己越來越遠。
在《用心》的章節中,丹尼爾毫不保留地將感動許多人生命的思想與情感分享給大家:為什麼孤獨反而讓我們覺得不孤獨?家長的壓力如何形塑孩子的未來,如何面對親人的離去......他反映出我們身為人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內心不願意浮出檯面的情感。最後,他成功地回答了最初的問題:作為一個人的意義是什麼?
他的回答──既具挑戰性又撫慰人心、既幽默又超越──勢必觸動每一位讀者的心。這是一本值得與親朋好友、工作夥伴分享,讓你一讀再讀、回味不已的動人心靈禮物書!
作者簡介
丹尼爾.戈特里布(Daniel Gottlieb)
執業的心理及家庭治療師、全美知名心理健康專家、談話節目主持人、專欄作家、講師及作家。他在美國費城國家廣播電台WHYY頻道主持的獲獎節目「家庭心聲」(Voices in the Family)已邁入第二十一年,《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可見到其知名專欄「真相」(Inside Out),他同時也是CNN和泰芮.葛蘿絲(Terry Gross)的Fresh Air等節目的主要來賓。
一九七九年,三十三歲的他因為一場車禍意外而四肢癱瘓,但生命的不凡經歷反而讓他更熱愛家庭與工作。三十年坐在輪椅上的生活,讓他得以深刻觀察人們的內心,並思考生而為人的意義,最新著作《用心》便是他對於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人生課題所提出的解答。
他育有兩女,還有一個外孫山姆,之前作品《給山姆的信》(Letters to Sam),已被譯成十一種語言,在全球各地銷售。著作還包括《家庭心聲》(Voices in the Family)、專欄結集而成的《衝突之聲.療癒之聲》(Voices of Conflict; Voices of Healing)。
作者網站: www.drdangottlieb.com
www.philly.com/philly/blogs/drdangottlieb
譯者簡介
謝明憲
台灣宜蘭人,台科大應用外語系畢。目前服務於台北「光中心」、真心之音「寧靜海」節目主持人及從事身心靈領域文字工作與翻譯。譯有暢銷書《秘密》(方智)、《情緒的驚人力量》(天下)、《比神更快樂》(方智)及審訂《吸引力法則》(方智)、《快樂,不用理由》(時報)等書。於《明報週刊》撰有「吸引力法則」相關專欄,並譯有《黑色公案》、《星星之夢》、《創造生命的奇蹟》等多種新時代心靈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