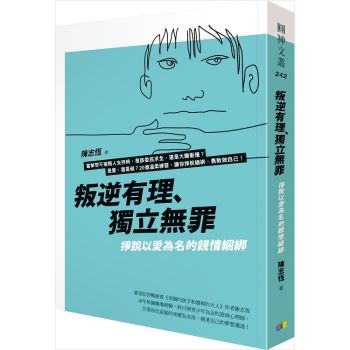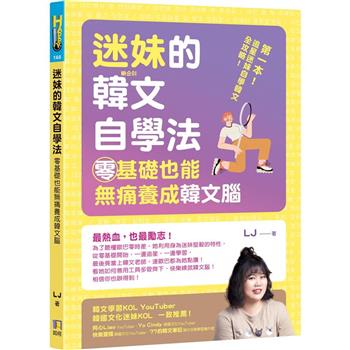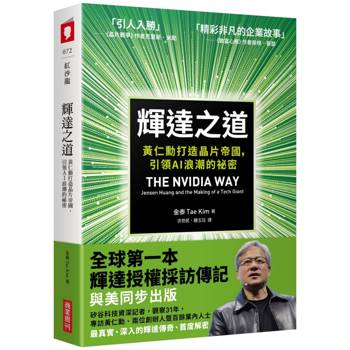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博客來、誠品年度百大作品《紙上城市》作者最新作品!兩位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共筆大作!
★2010年美國亞瑪遜YA類小說編輯選書第一名。
★2010年「好讀」網站YA類小說讀者票選第三名。
《兩個威爾》是由兩位明星級作家共同合作:約翰.葛林負責單數章節,大衛.賴維森負責雙數章節。故事從兩個威爾各自的觀點描述,藉由呈現兩名青少年的生活,探討青少年對「自我認同」的疑惑。
事實上,大衛.賴維森一直很想寫一個關於兩個同名男孩的故事。自從他在大學碰到與自己同名的男孩,並且因此衍生出一些周遭人誤認的趣事之後,他深深覺得「這之中一定有個故事」。
但是當大衛正式動筆之後,他發現自己需要一個合作夥伴而找上約翰.葛林,兩人一拍即合。在創作故事之初,兩位作者並未詳細討論故事內容與角色個性,只決定了兩個「威爾.葛雷森」必須意外在成人影視店相遇。沒想到這種新穎的創作方式不但行得通,而且兩位作者各自創作出了迷人的角色
艾凡斯頓與納波維爾這兩處芝加哥郊區相距不遠,但分別住在兩地的同名男孩——威爾.葛雷森與威爾.葛雷森,卻好似住在不同的星球上。
艾凡斯頓的威爾:
「只要遵守兩項規則,就可以完全避免哭泣:一,別太在意;二,閉上嘴巴。發生在我身上的每件不幸,都是因為沒有恪遵這兩項規則所致。」
納波維爾的威爾:
「我總是掙扎著該自殺還是殺死周圍所有人。這世上似乎只有這兩種選擇,其他都是浪費時間。」
一個寒冷的夜晚,在芝加哥市區某間成人影視店裡,兩名威爾陰錯陽差地相遇。當命運將他們引向意外的十字路口,兩名威爾.葛雷森的生命彼此交錯,並邁向未曾預期的方向。
兩條原本平行的人生道路,在名為「泰尼.庫柏」的十字路口交叉。泰尼是個身材龐大的美式足球攻擊線鋒,也是個性絕妙、才華洋溢的音樂劇創作者。
在新舊朋友的推波助瀾之下,威爾和威爾展開各自的戀情。同時,他們見證了一齣震撼人心的高中音樂劇演出。
嘗試→錯誤→嘗試→錯誤→嘗試→錯誤→嘗試→錯誤……兩個威爾在青春中摸索,為親情、友情、愛情等種種人際關係迷惘,希望找到理想的答案。
作者簡介
約翰.葛林 John Green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著有《尋找阿拉斯加》、《多樣的凱撒林》(暫譯)、《紙上城市》等,並獲得包括普林茲獎及普林茲榮譽獎在內的眾多獎項肯定。他也和弟弟共同企劃極受歡迎的影片部落格「Brotherhood 2.0」。現居於印第安納州。
歡迎參觀他的網站:www.sparksflyup.com和nerdfighters.com
大衛.賴維森 David Levithan
著有多本青少年書籍,榮獲眾多獎項,並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作品包括《男孩遇到男孩》、《清醒》、《愛情是至高法則》(以上均為暫譯書名)以及與蕾雪兒.柯恩合著的《愛情無線譜》等。另外,他也從事編輯工作,閒暇時間則過度耗費在攝影上。現居於紐澤西州。
歡迎參觀他的網站:www. davidlevitha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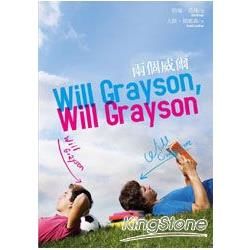
 2011/06/07
2011/06/07 2011/05/18
201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