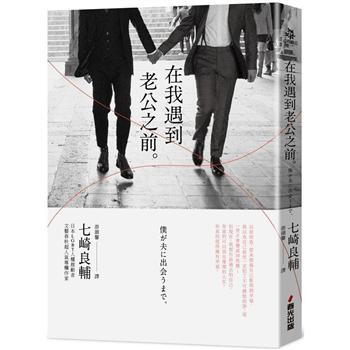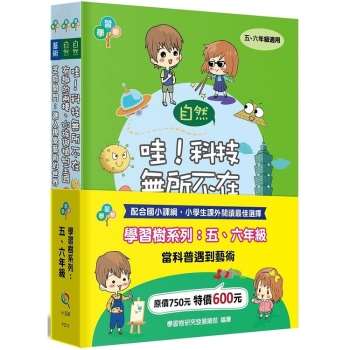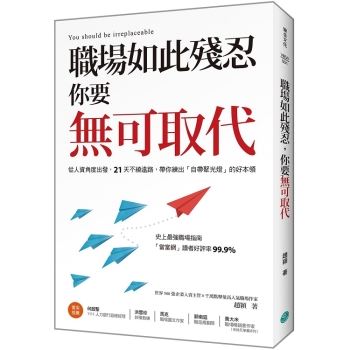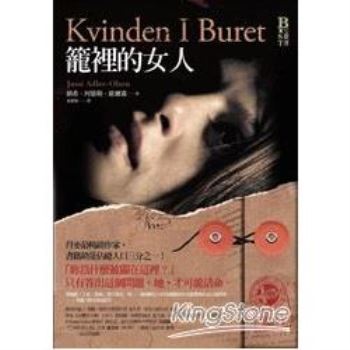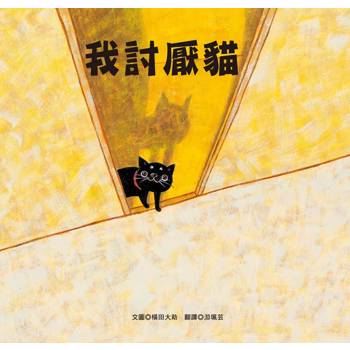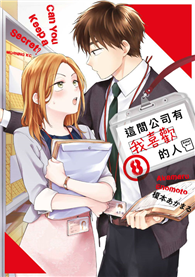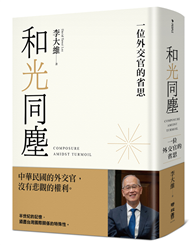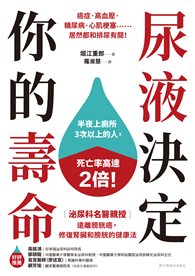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的圖書 |
 |
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 作者:皮國立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2-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1918-1920年的全球大流感被稱為「所有大流行病之母」,粗估全球至少五億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數更上看五千萬,是人類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相對於眾聲嘈雜的西方,東亞世界對於這場奪去千萬人性命的瘟疫史研究,卻異常安靜。2019年底開始肆虐世界各地的新冠肺炎(COVID-19),與全球大流感有許多相似之處,引起人們再度關注這段幾乎要被遺忘的疾病史。
今日的科學研究已經證實,1918年爆發的全球性流行瘟疫,其源頭正是H1N1型流感。這波疫情當時也衝擊到中國本土、日本、臺灣、東南亞等地。在許多既有的西方研究中,都未曾對中國的疫情做出全面的介紹與評估,反而多帶有偏見地認為,大流感造成中國難以估計的人口死亡與損害,而且該病的散播源頭正是中國,一如新冠肺炎爆發後那樣。
過往史家在研究中,或多或少的指出1918年大流感的影響,但多偏重世界疫情的論述,對中國疫情則僅有片段之著墨,缺乏基礎、深入的研究,難窺疫情全貌。 日本學者飯島涉曾坦言:「我們對中國當時流感擴散的狀況並不太清楚。」 是以我們目前需要一個對當時疫情全面考察的研究。
皮國立的這本《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在新冠肺炎仍肆虐不止的此刻,不僅「躬逢其盛」,得以和許多談論西方全球大流感歷史的名著對話,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中國與臺灣之歷史經驗,更為歷來僅從西醫角度討論或分析的書寫主流,另外開啟一扇中國醫學的視野,剪影這場流感大戲中許多過去未曾深究的細節,頗能讓人耳目一新,並體現了「疫病的危機其實就是轉機」,值得讀者省思。
本書中,作者交錯運用歷史文獻與取自民間日常生活的個案或報刊記載的實例,從而突顯了上層社會與基層大眾所構成的文化現象、歷史記憶,其中「對疾病文化的多元解讀與認識」尤其值得今日的我們給予關注與反思。
作者簡介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為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身體史、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等領域。
著有《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中醫抗菌史:近代中西醫的博弈》、《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等學術專書,並合編有《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藥品、疾病與社會》、《憶載航空城:大園落地生根的記憶》以及高中歷史教科書等等,另有學術論文、專書篇章等80餘篇。
Styletubation: A Video Intubating Stylet Technique fo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大師教你太極養生功:男女老少皆可練,越練身體越年輕
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3萬冊暢銷經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
體內針灸:第一冊(國際英文版)
自律神經失調有救了:為何很多醫師都治不好?25年臨床經驗!權威名醫給你有效的治療對策
五十肩,一定治得好!:徐子恆用千例臨床經驗找出真正關鍵,教你如何重拾健康肩膀!
70%的人都有自律神經失調?!(經典暢銷版):自律神經不自律,就是生活失控的開始!
脂肪魔術師:增脂、減脂、補脂,雕刻完美曲線
腎臟超圖解:慢性發炎、免疫失調、腎病變,權威名醫教你看懂腎臟求救訊號,立即提升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