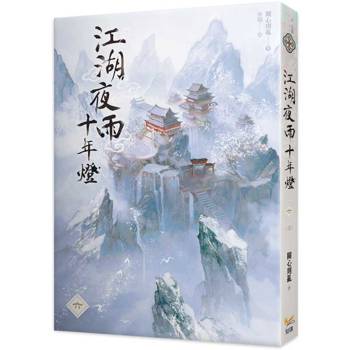作者簡介
蔡仁厚(1930-2019)
原籍江西雩都,歷任大學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會理事、常務監事、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顧問。早年即從學於當代哲儒牟宗三先生,一以貫之,逾四十年。教學之外,又勤於著述,專著如《孔孟荀哲學》、《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宋明理學》、《王陽明哲學》、《中國哲學史》、《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儒學的常與變》、《新儒家與新世紀》等書。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孔門弟子志行考述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孔門弟子志行考述
目錄
自 序
一、復聖顏子
顏子之學 顏子之德 顏子之志 顏子之才 顏子之喪
二、宗聖曾子
曾子之孝 曾子的志節 曾子的風義 曾子傳道 曾子之守約與全歸
三、孝友廉潔的閔子鶱
孝哉閔子騫 閔子的廉潔與識見 閔子的學養與情操
四、善言德行的伯牛
伯牛的德行 伯牛之疾
五、可使南面的仲弓
仲弓的身世 仲弓的器量 仲弓的造境
六、博藝善政的冉有
冉有的資性與才藝 冉有的政事 冉有之義勇
七、忠信勇決的子路
子路的性格 子路的政才 子路的善德與修養 子路之死
八、跅弛不羈的宰我
宰我的才氣 宰我之事齊與死難 宰我的身後
九、賢達敏辯的子貢
子貢的器能 子貢的方識 子貢之善學 子貢廬墓
十、嫻習禮樂的子游
子游習於禮 子游宰邑滿城弦歌 子游之知人 子游與禮運大同
一一、教授傳經的子夏
子夏之論學 可與言《詩》 子夏居西河教授 子夏傳經 子夏氏之儒
一二、志高意廣的子張
子張的大度 子張的志概 子張的行贊 子張氏之儒
一三、言似聖人的有子
有子忠勇愛國 有子的學識 有子的地位
一四、志通好禮的公西華
公西華的才能 公西華之知禮 公西華之養親
一五、清操自守的原憲
原憲為宰 原憲之貧 原憲的節操
一六、愚而日明的子羔
柴也愚 子羔的孝行 子羔的為政
一七、忍辱不辯的公冶長
公冶長可妻也 通鳥語的傳說
一八、三復白圭的南容
南容三復白圭 尚德哉若人
一九、鳴琴而治的宓子賤
子賤的治術 君子哉若人
二○、勞力教詔的巫馬期
巫馬期的志操 巫馬期的治績
二一、請學稼圃的樊遲
須也弱而能勇 樊遲之問學 樊遲學稼
二二、別啟宗風的漆雕開
漆雕開之篤志 漆雕儒之風
二三、行不由徑的澹臺滅明
行不由徑解 失之子羽致疑 澹臺滅明的特行
二四、憂懼而終的司馬牛
司馬牛的家世 司馬牛之從學 司馬牛憂懼而終
二五、胸懷灑落的曾點
曾點之狂 吾與點也
二六、顏路、琴牢、陳亢、申棖、林放
顏路 琴牢 陳亢 申棖 林放
二七、孔門弟子名表
二八、孔門師弟年表
參考書目舉要
一、復聖顏子
顏子之學 顏子之德 顏子之志 顏子之才 顏子之喪
二、宗聖曾子
曾子之孝 曾子的志節 曾子的風義 曾子傳道 曾子之守約與全歸
三、孝友廉潔的閔子鶱
孝哉閔子騫 閔子的廉潔與識見 閔子的學養與情操
四、善言德行的伯牛
伯牛的德行 伯牛之疾
五、可使南面的仲弓
仲弓的身世 仲弓的器量 仲弓的造境
六、博藝善政的冉有
冉有的資性與才藝 冉有的政事 冉有之義勇
七、忠信勇決的子路
子路的性格 子路的政才 子路的善德與修養 子路之死
八、跅弛不羈的宰我
宰我的才氣 宰我之事齊與死難 宰我的身後
九、賢達敏辯的子貢
子貢的器能 子貢的方識 子貢之善學 子貢廬墓
十、嫻習禮樂的子游
子游習於禮 子游宰邑滿城弦歌 子游之知人 子游與禮運大同
一一、教授傳經的子夏
子夏之論學 可與言《詩》 子夏居西河教授 子夏傳經 子夏氏之儒
一二、志高意廣的子張
子張的大度 子張的志概 子張的行贊 子張氏之儒
一三、言似聖人的有子
有子忠勇愛國 有子的學識 有子的地位
一四、志通好禮的公西華
公西華的才能 公西華之知禮 公西華之養親
一五、清操自守的原憲
原憲為宰 原憲之貧 原憲的節操
一六、愚而日明的子羔
柴也愚 子羔的孝行 子羔的為政
一七、忍辱不辯的公冶長
公冶長可妻也 通鳥語的傳說
一八、三復白圭的南容
南容三復白圭 尚德哉若人
一九、鳴琴而治的宓子賤
子賤的治術 君子哉若人
二○、勞力教詔的巫馬期
巫馬期的志操 巫馬期的治績
二一、請學稼圃的樊遲
須也弱而能勇 樊遲之問學 樊遲學稼
二二、別啟宗風的漆雕開
漆雕開之篤志 漆雕儒之風
二三、行不由徑的澹臺滅明
行不由徑解 失之子羽致疑 澹臺滅明的特行
二四、憂懼而終的司馬牛
司馬牛的家世 司馬牛之從學 司馬牛憂懼而終
二五、胸懷灑落的曾點
曾點之狂 吾與點也
二六、顏路、琴牢、陳亢、申棖、林放
顏路 琴牢 陳亢 申棖 林放
二七、孔門弟子名表
二八、孔門師弟年表
參考書目舉要
序
自序
二十世紀的人,失去了一個有意義的世界,也失去了一個真實的自我。「什麼是人格的型範」?這該是何等重要的事!而在今天,卻已成為一句迂拙的問話了。這真是一個虛無的時代,真美善的標準,學問的義法與分際,乃至於「意義」本身的意義,全都遭到極大的攪擾,而混亂了。我們可以這樣說,「由於眾生顛倒,乃造成顛倒眾生的逆流」。一個人不鄭重自己,便什麼都不鄭重了。這個時代之所以不可愛,照我看,主要是人們感到「日暮途窮」,因此就「倒行逆施」。當前的人類,是沒有「天地悠悠」的情懷,更沒有「天長地久」的信念了。所以一切都露「短命相」,一切都只是「苟」。孔子說:「君子無所苟而已矣」。所謂「志行」,亦只是「無所苟」而已。而孔門弟子,便正是一群「不苟」的人物。
孔子是一個有道的生命,他承奉天命來作昏沉無道的時代的木鐸。他的人格精神,使一群光明俊偉的青年深受感動;他走到那裡,他的人格精神之振幅,便擴散到那裡。大家追隨著他周流四方,失道絕糧,而卻心志彌堅,仰敬彌篤。他們嚮往著一個道德文化的理想,他們踐行著一個生命的浩浩大道。他們的活動,在華夏文化的國度裡映現出一幅美麗生動的畫面。只是充盈於那個畫面之上的彩繪與線條,不是丹青,而是貞定篤實的情志,撥亂返治的心願,與未喪斯文的信念。孔門弟子並沒有成就顯赫的事功,但他們弘揚聖道,傳續文化的德業,便已足以永世不磨了。當然,孔門諸賢的生活行事,有一些亦並不適合現代人去模倣學步─這也是不必要的。一個仰慕希臘哲人的人,難道要對他們的生活行徑亦步亦趨麼?同理,我們亦不應該以現代人的生活觀念去批評先賢。人類生活的基本理則雖然古今相通,但生活之迹,卻永遠是屬於時代的東西;該延續的便自然延續下來,不能存留的自然為各個時代的浪濤淘盡了。現在要緊的是,看我們對於這些生命人格能有多少了解;通過我們的了解,又能否使自己知所感發,以湧身百世上,見賢而思齊。
孔門諸子,都是天挺人豪。但平常大家只會說一句「孔門弟子」,「七十子之徒」之類的概括性的話,我們彷彿不太能夠感覺到他們的才情聲光與生命奇采。這個困惑,就我個人來說,是在十多年前讀了唐君毅先生的《孔子與人格世界》之後,纔恍然有悟的。唐先生分人格型態為六種:⑴純粹的學者、事業家型;⑵天才型;⑶英雄型;⑷豪傑型;⑸偏至的聖賢型;⑹圓滿的聖賢型。而孔門弟子都是有志於聖賢而拔乎流俗的豪傑之士。如像曾子,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又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何等豪傑氣概!而子路的豪傑氣,尤其常常表現在他的言行之間。堂堂乎的子張,「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此即肝膽照人,推心置腹的英雄襟度。子貢才情穎露,類乎天才。文學科的子游、子夏,較近於學者。政事科的冉有,則近乎長於計劃的事業家。顏子默然渾化,坐忘喪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與現實世界似乎略無交涉;對聖人之道,只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贊歎,此則特具宗教性偏至聖賢的超越精神。但他們都涵育在孔子的聖德教化之中,未嘗以天才、英雄、豪傑、宗教性之人格顯。他們的才情聲光,在孔子面前放平了,渾化了;他們的人格精神,在孔子的德慧感潤之下,同一化於孔子,而歸於永恆。我們常常感到論贊聖賢,措辭為難,這該是真正的原因所在。然而,仰慕與崇讚聖賢人格,和了解構成這個人格世界的人物之生平志行,總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事。所以我雖自度淺陋,深知僭妄,仍利用教學之暇,勉力寫成此書。
本書的「考」,大體食前人之功,雖費時費力,而創獲甚少;本書的「述」,則頗列私見,自謂有一得之愚。雖然所考的,未必「完全合乎事實」(這亦幾乎是不可能的);所述的,亦未必「周洽無誤」,更何況見仁見智,看法不同。不過,凡我所說,都是本乎我之所信,而我亦是抱著誠懇的願望,想來重現一個人格世界的。孔門弟子的精神面目,已在我們的印象裡封存得太久了,不僅是模糊而已。而多少年代以來,我們又不善於讀《論語》,以是,亦就很不容易接上孔門的德慧生命。在我讀到過的一些簡略而乾冷的弟子考之類的篇章裡,亦似乎不十分能夠接觸到這些人物的生命人格與性情志行。而這些,卻是本書想要盡心致力的地方;但到底能夠做到多少,則有待讀者的評判和明教了。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仲尼弟子列傳〉共載七十七人,其中年歲生平不可確考的竟又超過半數,可見史文有闕,自古已然。本書〈孔門弟子名表〉雖然亦根據弟子傳列敘七十七人,但正文所述三十人,則是以他們的名氏是否見載於《論語》以為準。《論語》不載而生平略可考見的,則附述於弟子名表備考欄內。另再作〈孔門師弟年表〉,自孔子生年起至孔子卒後五十四年止,擇要地記載孔子以及門弟子的生卒年歲與重要行事。二表之作,一方面是為了便於查考,一方面亦是想為讀者提供比較具體的歷史人物之時代背景,以加強讀書的效果,增添讀書的情味。
本書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一三、一四、一六、二一各篇,於五十五年二月起,絡續發表於香港《人生雜誌》;而子路一文,並由國立政治大學編入導師制用書之四:「大學生的修養」第三輯。茲當成書印行之際,併致謝忱。
今年農曆新年,是先祖父輔卿公謝世二十周年忌辰。他的愷悌慈祥,誠樸儉約,以及表現在生活事業上的勤奮、建構之精神,是我永遠仰念不忘的。現在謹以這本小書紀念他,是要永祈他在天之靈,隨時呵護我,支持我,使我奮勉不懈,以免辱沒了他的令德和家聲。
蔡仁厚自序於臺中寓舍 民國五十八年春月
二十世紀的人,失去了一個有意義的世界,也失去了一個真實的自我。「什麼是人格的型範」?這該是何等重要的事!而在今天,卻已成為一句迂拙的問話了。這真是一個虛無的時代,真美善的標準,學問的義法與分際,乃至於「意義」本身的意義,全都遭到極大的攪擾,而混亂了。我們可以這樣說,「由於眾生顛倒,乃造成顛倒眾生的逆流」。一個人不鄭重自己,便什麼都不鄭重了。這個時代之所以不可愛,照我看,主要是人們感到「日暮途窮」,因此就「倒行逆施」。當前的人類,是沒有「天地悠悠」的情懷,更沒有「天長地久」的信念了。所以一切都露「短命相」,一切都只是「苟」。孔子說:「君子無所苟而已矣」。所謂「志行」,亦只是「無所苟」而已。而孔門弟子,便正是一群「不苟」的人物。
孔子是一個有道的生命,他承奉天命來作昏沉無道的時代的木鐸。他的人格精神,使一群光明俊偉的青年深受感動;他走到那裡,他的人格精神之振幅,便擴散到那裡。大家追隨著他周流四方,失道絕糧,而卻心志彌堅,仰敬彌篤。他們嚮往著一個道德文化的理想,他們踐行著一個生命的浩浩大道。他們的活動,在華夏文化的國度裡映現出一幅美麗生動的畫面。只是充盈於那個畫面之上的彩繪與線條,不是丹青,而是貞定篤實的情志,撥亂返治的心願,與未喪斯文的信念。孔門弟子並沒有成就顯赫的事功,但他們弘揚聖道,傳續文化的德業,便已足以永世不磨了。當然,孔門諸賢的生活行事,有一些亦並不適合現代人去模倣學步─這也是不必要的。一個仰慕希臘哲人的人,難道要對他們的生活行徑亦步亦趨麼?同理,我們亦不應該以現代人的生活觀念去批評先賢。人類生活的基本理則雖然古今相通,但生活之迹,卻永遠是屬於時代的東西;該延續的便自然延續下來,不能存留的自然為各個時代的浪濤淘盡了。現在要緊的是,看我們對於這些生命人格能有多少了解;通過我們的了解,又能否使自己知所感發,以湧身百世上,見賢而思齊。
孔門諸子,都是天挺人豪。但平常大家只會說一句「孔門弟子」,「七十子之徒」之類的概括性的話,我們彷彿不太能夠感覺到他們的才情聲光與生命奇采。這個困惑,就我個人來說,是在十多年前讀了唐君毅先生的《孔子與人格世界》之後,纔恍然有悟的。唐先生分人格型態為六種:⑴純粹的學者、事業家型;⑵天才型;⑶英雄型;⑷豪傑型;⑸偏至的聖賢型;⑹圓滿的聖賢型。而孔門弟子都是有志於聖賢而拔乎流俗的豪傑之士。如像曾子,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又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何等豪傑氣概!而子路的豪傑氣,尤其常常表現在他的言行之間。堂堂乎的子張,「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此即肝膽照人,推心置腹的英雄襟度。子貢才情穎露,類乎天才。文學科的子游、子夏,較近於學者。政事科的冉有,則近乎長於計劃的事業家。顏子默然渾化,坐忘喪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與現實世界似乎略無交涉;對聖人之道,只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贊歎,此則特具宗教性偏至聖賢的超越精神。但他們都涵育在孔子的聖德教化之中,未嘗以天才、英雄、豪傑、宗教性之人格顯。他們的才情聲光,在孔子面前放平了,渾化了;他們的人格精神,在孔子的德慧感潤之下,同一化於孔子,而歸於永恆。我們常常感到論贊聖賢,措辭為難,這該是真正的原因所在。然而,仰慕與崇讚聖賢人格,和了解構成這個人格世界的人物之生平志行,總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事。所以我雖自度淺陋,深知僭妄,仍利用教學之暇,勉力寫成此書。
本書的「考」,大體食前人之功,雖費時費力,而創獲甚少;本書的「述」,則頗列私見,自謂有一得之愚。雖然所考的,未必「完全合乎事實」(這亦幾乎是不可能的);所述的,亦未必「周洽無誤」,更何況見仁見智,看法不同。不過,凡我所說,都是本乎我之所信,而我亦是抱著誠懇的願望,想來重現一個人格世界的。孔門弟子的精神面目,已在我們的印象裡封存得太久了,不僅是模糊而已。而多少年代以來,我們又不善於讀《論語》,以是,亦就很不容易接上孔門的德慧生命。在我讀到過的一些簡略而乾冷的弟子考之類的篇章裡,亦似乎不十分能夠接觸到這些人物的生命人格與性情志行。而這些,卻是本書想要盡心致力的地方;但到底能夠做到多少,則有待讀者的評判和明教了。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仲尼弟子列傳〉共載七十七人,其中年歲生平不可確考的竟又超過半數,可見史文有闕,自古已然。本書〈孔門弟子名表〉雖然亦根據弟子傳列敘七十七人,但正文所述三十人,則是以他們的名氏是否見載於《論語》以為準。《論語》不載而生平略可考見的,則附述於弟子名表備考欄內。另再作〈孔門師弟年表〉,自孔子生年起至孔子卒後五十四年止,擇要地記載孔子以及門弟子的生卒年歲與重要行事。二表之作,一方面是為了便於查考,一方面亦是想為讀者提供比較具體的歷史人物之時代背景,以加強讀書的效果,增添讀書的情味。
本書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一三、一四、一六、二一各篇,於五十五年二月起,絡續發表於香港《人生雜誌》;而子路一文,並由國立政治大學編入導師制用書之四:「大學生的修養」第三輯。茲當成書印行之際,併致謝忱。
今年農曆新年,是先祖父輔卿公謝世二十周年忌辰。他的愷悌慈祥,誠樸儉約,以及表現在生活事業上的勤奮、建構之精神,是我永遠仰念不忘的。現在謹以這本小書紀念他,是要永祈他在天之靈,隨時呵護我,支持我,使我奮勉不懈,以免辱沒了他的令德和家聲。
蔡仁厚自序於臺中寓舍 民國五十八年春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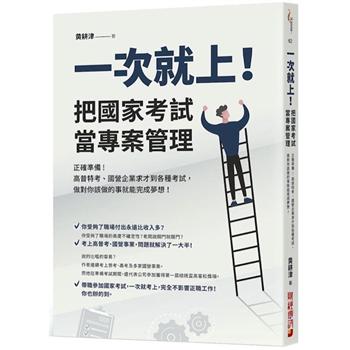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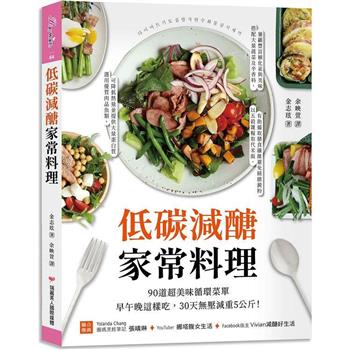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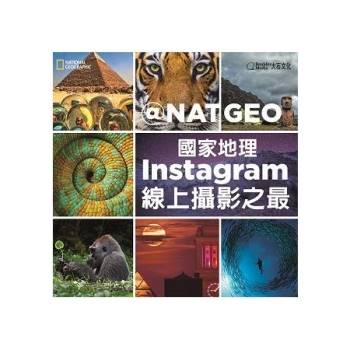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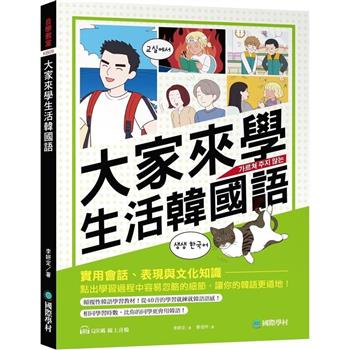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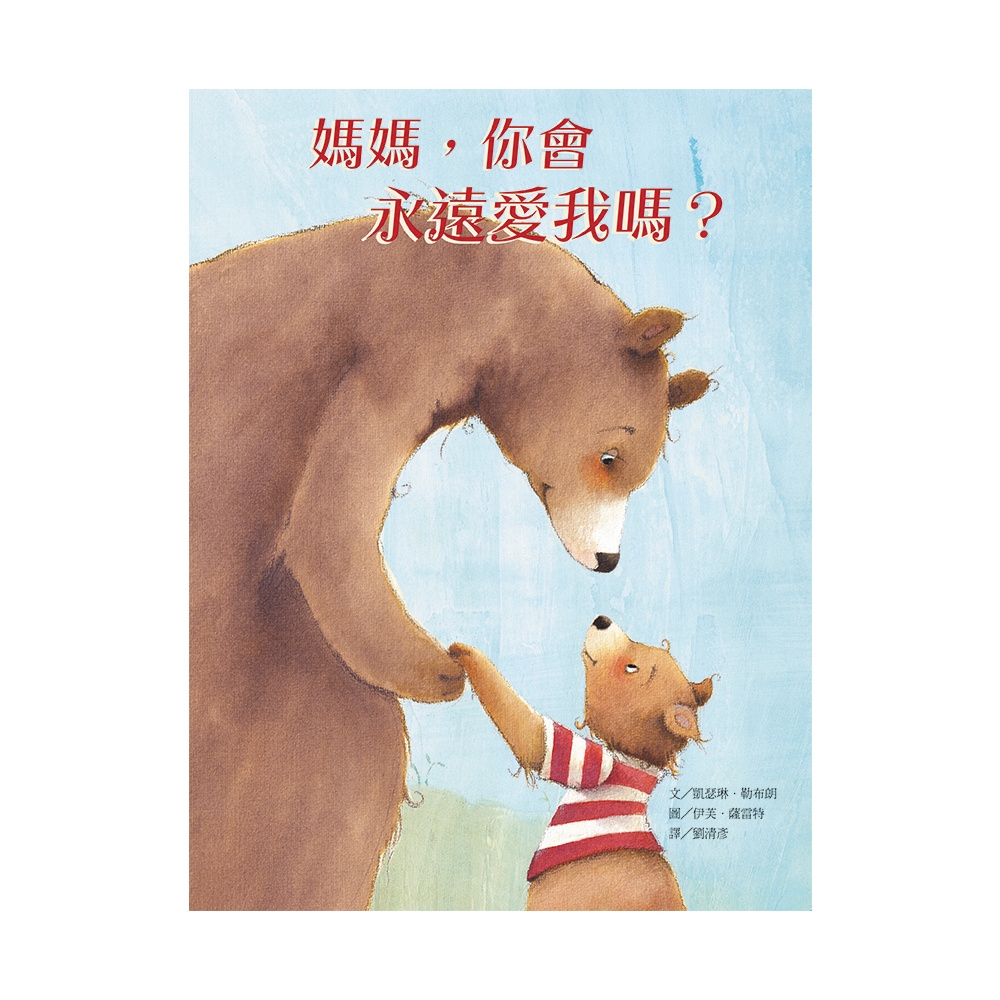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