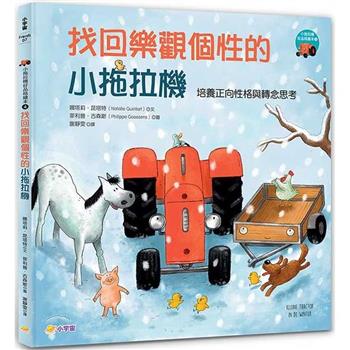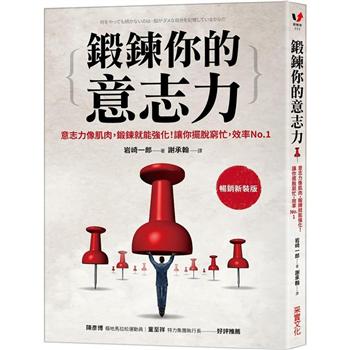推薦文一海星、蜘蛛與平行序列方程式 李偉文14
推薦文二利用海星幫你創價! 林信義18
推薦文三海星是整合全球競爭力的最佳對策 陳文龍24
推薦文四分權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黃志遠28
推薦文五你換到海星頻道了嗎? 趙義隆30
推薦文六集權或分權?看情境而定! 葉匡時34
前言愈分散愈活躍的力量
第1章 米高梅的錯誤與阿帕契之謎
資金雄厚的唱片公司打擊音樂分享軟體時,所向無敵的西班牙軍隊攻擊古老部落阿帕契人時,都遇上了一樣的怪事:他們施加的力道愈大,對手就愈壯大……
【重要案例與內容】
唱片業vs.音樂分享軟體納布斯特、卡薩、電子驢、電子騾
阿帕契人vs.西班牙軍隊∕集權vs.分權
第2章 蜘蛛、海星與網路總裁
乍看之下,蜘蛛與海星外觀很像,看起來都是從中央的軀體長出幾隻腳。但是消滅的方法卻全然不同,砍掉蜘蛛的頭,蜘蛛就死了;但如果把海星切成兩半,你會看到兩隻海星。
【重要案例與內容】
戒酒無名會∕美國氣象局∕音樂產業∕檢驗海星十大原則
第3章 海星之海
海星代表彈性、反應迅速的分權特性,在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已經蔚為不可小覷的新勢力。各種海星式組織、海星式決策、海星式概念不斷在工作中、商場中、生活中出現。
【重要案例與內容】
網路電話Skype∕分類廣告葛列清單∕阿帕契軟體∕維基百科∕火人節
第4章 五足鼎立
海星雖然深具優勢,但在五隻腳一起運作時,分權化的組織所能發揮的威力將最為強大。
【重要案例與內容】
英國廢奴運動∕美國女性平權運動∕海星的五隻腳:圈子、催化劑、意識型態、既存的網絡、鬥士
第5章 催化者隱藏的力量
海星組織的催化者與一般企業執行長都扮演領導人的角色,但兩者運用的方法或工具,卻截然不同。
【重要案例與內容】
維基百科的威爾斯∕善念機構的艾發瑞羅德瑞茲∕社會網絡達人霍夫曼∕反全球化激進分子薩吉∕青年總裁協會的馬丁∕催化者的工具∕催化者vs.執行長
第6章 善用分權化
海星組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但並不是毫無攻克方法。深入掌握海星特性,就能掌握摧毀海星敵人的方法。
【重要案例與內容】
動物解放陣線vs.美國調查局∕蓋達組織vs.美國政府∕迦美波拉信貸∕未來世代∕契努克外交∕打擊海星的三大策略:改變意識型態、把他們集中化、讓自己分權化
第7章 複合式特區:混血組織
純粹的海星組織非常難創造營收,更遑論獲利。但若運用到商場,集合分權與集權優點的混血組織,卻是最棒的賺錢機器。
【重要案例與內容】
第一類:將顧客經驗分權化:便宜賣二手電腦網站、eBay、亞馬遜網路書店、歐普拉讀書俱樂部、稅務年鑑網站、Google、IBM、昇陽電腦
第二類:將公司部門分權化:奇異電器、創投公司DFJ∕肯定試探詢
第8章 尋找甜蜜點
在集權與分權的連續光譜上,甜蜜點是佔據最佳競爭位置,能賺取最大利潤的點。有些產業的甜蜜點比較穩定,多數產業的甜蜜點則不斷變動,有時向分權方向移動,有時向集權方向移動。
【重要案例與內容】
彼得?杜拉克的金礦∕通用汽車vs.豐田汽車∕eBayvs.便宜賣網站∕唱片公司vs.音樂分享下載軟體
第9章 新世界
在這個網路串聯比跟鄰居聯絡容易的世界,海星隨時會出現在你身邊,搶走你的市場,只有認清新的遊戲規則,才能站穩生存與成長的腳步。
【重要案例與內容】
十大規則:規模不經濟∕網絡效應∕混亂的力量∕前緣上的知識∕每個人都想貢獻∕注意九頭蛇反應∕催化者原則∕價值觀即組織∕測量監看與管理∕打敗別人或被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