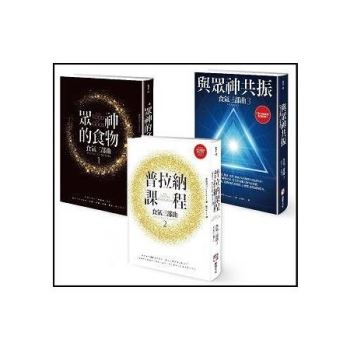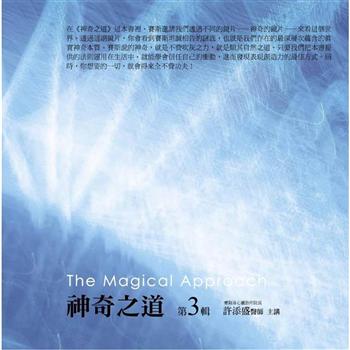什麼原因讓兩名凶手犯下滅門血案?當作家試圖剖析凶手的心靈時,他的目光、他的筆,比凶刀更加冰冷…… 這是文學史上最富傳奇也最冷血的書寫。1959年11月15日,美國南方小鎮發生滅門血案,吸引了作家卡波提的注意,他立即趕到當地,開始一連串訪談,包括對死者親友、鄰居、當地警局,以及最重要的──兩名殺人嫌犯。 往後五年半之間,卡波提全心投入於調查被害者一家、兩名凶手(狄克與貝利)的身世,並重建慘案發生經過,與近身採訪兩名嫌犯接受審判的過程。為了深入了解凶手的心靈,卡波提與嫌犯成為好朋友。有人說卡波提在兩人身上看見自己悲慘的童年,也有人說,卡波提最後愛上了凶手。 嫌犯自力救濟,四處發函抗議判決不公。但上訴官司最後沒打成,凶手仍然伏法,而描繪他們心靈狀態的《冷血》於1966年出版,成為美國最暢銷的文學經典,卡波提也藉此登上文學殿堂的巔峰,但他從此再沒能完成新的作品。
【暢銷紀錄】◎1966年,《冷血》出版後立即躍登紐約時報等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且佔榜一年多,短短期間即已創下三百多萬本銷量,1990年代前是美國史上最暢銷的書。◎2005年,出版將近40年的《冷血》再度躍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且又佔榜將近兩年。2006年影壇刮起卡波提熱,紛紛拍起「冷血告白」等電影,其中「柯波帝:冷血告白」並勇奪多項奧斯卡獎。


 2015/12/04
2015/12/04 2015/11/05
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