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是一群人,也是一種病毒,它瀰漫在文學世界裡,讓作家無法再下筆……
這是一位駝背宅男的故事,他整天宅在公司裡。若你以為他熱愛工作,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每當他的主管要分配任務給他時,他總是說:「恕難從命。」他還引用王爾德的話,解釋說:「什麼都不做是全世界最困難的事。」
這位宅男年輕時曾寫過一本小說,主題是關於「不可能的愛情」,但因為某種心靈創傷,他拒絕再寫。直到某一天,他開始寫日記,記錄那些和他同病相憐的作家封筆之謎。奇怪的是,他的日記裡看不見正文,只有腳註,好像正文被某種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本書是西班牙文學中最具獨創性的暢銷作家安立奎.維拉馬塔斯的代表作,小說主要以「看不見文本」的日記內容與五十二則腳註組成。這不是一本尋常的小說,而是混雜著事實與故事的奇特文體。書中所揭露的作家封筆之謎,就像小說一樣豐富而引人入勝。
作者簡介:
安立奎.維拉馬塔斯
Enrique Vila-Matas, 1948.3.31~
繼馬奎斯、尤薩之後當代最傑出的西語小說家之一。作品翻譯成數十國語言,廣受國際好評,奇妙的是,各國讀者對維拉馬塔斯作品的接受度極高,若不看作者簡介,常會誤以為他是本國作家,可見他的作品能引起普遍的共鳴。
維拉馬塔斯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20歲時為了躲避佛朗哥專制政權,移居巴黎;起初他以替雜誌採訪、在電影裡跑龍套等工作謀生,業餘則投入他熱愛的寫作,他曾說:「寫作,是修正人生錯誤的一種方法,保護我們不受生命無常的傷害與衝擊。」1977年發表第一本小說《預先告知的謀殺》(La asesina ilustrada)後,維拉馬塔斯便專事創作,自此不曾中斷。
維拉馬塔斯深受波蘭荒誕派劇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的啟發,逐漸形成跳躍式且諷刺意味深重的寫作風格,其手法成功地模糊了虛幻與現實間的界線,於現代文學中獨樹一格,作品至今已被譯成三十國語言。除了小說之外,維拉馬塔斯也撰寫文學散文與新聞評論。
《巴托比症候群》是維拉馬塔斯的代表作,被譽為「西語文學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說」(西班牙《ABC報》),並獲選為法國書商年度好書。其他獲得文學獎肯定的作品,尚有《垂直的旅程》(El viaje vertical, 1999)獲羅慕洛.加列哥斯國際小說獎,這是拉丁美洲最高榮譽的文學獎,先前得獎者包括了馬奎斯、尤薩等;《蒙塔諾之惡》(El mal de Montano)獲法國梅迪西斯獎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文】
我不寫,故我在◎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
這是一本沉默與喧嘩並陳之書,兼具波赫士的機智靈巧、卡爾維諾的寓言詩意,以及安伯托.艾可的華麗雄辯。作者以充滿趣味的筆調,剖析「我不寫,故我在」的弔詭情境,引領讀者穿梭在古往今來許多傑出的作家與作品之間,抽絲剝繭創作的奧祕泉源。
對所有作家而言,得了「巴托比症候群」無異是宣告死刑,但本書卻由此出發,在那一片虛空、無語和黑暗之處,挖掘到生命與書寫所必然存在的致命深淵,讓所有喜愛創作的人讀起來,都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
【推薦文】
不存在的完美之作◎何致和(小說家)
安立奎.維拉馬塔斯這位西班牙文壇怪傑,在《巴托比症候群》這本怪書中,以思考角度與寫作手法的雙重創新,展現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知識涵養。這部著作以註腳先行,正文並不存在,書中貌似正文的日記或筆記,竟成為了註腳的註解。而中譯本為服務讀者,又在註腳與成為註腳註解的內文中加上大量註釋,讓本書的複雜性又多加一層,成為「註中有註」的有趣現象。
大量自由度極高的註腳,雖說已僭越正文而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正文,事實上也已讓那部「不存在」的文本隱然成形。作者從「為什麼不寫作」這個問題出發思考,與如此多黑暗的文學靈魂打交道,究底說來探尋的還是「為什麼要寫作?」
在寫與不寫之間,充滿太多不同的類型與典範,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半途而廢,找不到全體適用的單一答案。故事中的主角對「未完成」心生嚮往,並非想美化怠惰或拯救造紙所需的樹木,而是如班雅明一般,不把陳述事實或發布信息視為文學的基本特性。不能完成的作品,是否才是完美之作?思考這個問題可說等同於思考文學藝術的神性,而作者在書中針對這點做了相當細膩精彩的論述。無論是汲汲想創作出完美的寫作者,或汲汲尋找完美之作的讀者,都不妨先好好細讀玩味《巴托比症候群》這部了不起的作品。
名人推薦:
【推薦文】
我不寫,故我在◎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
這是一本沉默與喧嘩並陳之書,兼具波赫士的機智靈巧、卡爾維諾的寓言詩意,以及安伯托.艾可的華麗雄辯。作者以充滿趣味的筆調,剖析「我不寫,故我在」的弔詭情境,引領讀者穿梭在古往今來許多傑出的作家與作品之間,抽絲剝繭創作的奧祕泉源。
對所有作家而言,得了「巴托比症候群」無異是宣告死刑,但本書卻由此出發,在那一片虛空、無語和黑暗之處,挖掘到生命與書寫所必然存在的致命深淵,讓所有喜愛創作的人讀起來,都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
【推薦文】...
推薦序
【導讀】
文學末世啟示錄◎張淑英(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巴托比症候群》,維拉馬塔斯的第十八部作品,也是西班牙知名文學雜誌《幻想》(Quimera)由讀者票選的二○○○~二○○九年十本具代表性的小說排序第二名。《巴托比症候群》以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為楔子,敘述一位上班族,在千禧年到來之前,克服自己二十五年來未曾提筆的心靈創傷,用書寫一個月的日記的方式(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八月七日),另增頁腳眉批,評論一些「看不見的文本」,開啟了一連串他對文學的探索與詰問,解釋作家創作與不創作的理由。《巴托比症候群》闡述的寫書情結,宛若《紙房子裡的人》(La casa de papel)的尋書經歷──作者多明格茲(C.M Dominquez)引用康拉德的《陰影線》(The Shadow Line),交互指涉,牽引出愛書人的蒐藏之旅與心理的癡迷/謎。有「巴托比症候群」的作家,則彷彿被一條陰影線遮蔽切割,在是/否寫作間游移又猶疑。
《巴托比症候群》敘述西方文壇少產、多產或不產的作家,例如魯佛、韓波、沙林傑、阿爾發、葛哈克;或是瓦爾澤、儒貝爾──等等;他們如何構築負面思維,身(深)陷「『不』的迷宮」,以致於終生遲遲不創作;或是經典一出手,就此封筆;或是享盡盛名卻毫無著作;或是著作等身之後頓悟,斷然拋棄文學。「拒絕、放棄與沉默」似乎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症狀三部曲,好似所謂的「魔咒」,緊箍作家的手與頭。另外一群人,例如瑪麗安娜.榮格、特拉文、品瓊則是神祕的「藏鏡人」,不輕易暴露身分,讀者無從得知這好作品抑或壞作品的主人是誰。
維拉馬塔斯透過《巴托比症候群》尋奇,也提供了不少名人軼事:文壇健筆如貝克特、希梅涅茲、托爾斯泰、塞萬提斯、王爾德等人,也有倦勤向文學說「不」的境遇(或在愛妻辭世時;或在自己撒手歸西前;或飲酒買醉取代筆耕)。這裡面,每一位作家向文學道別的經歷都是一則獨特的作者生平導覽,串連出巴托比群像,儼然是文人小百科。在邁向新世紀當兒,維拉馬塔斯不免俗地運用後設小說和互文性的技巧,以黑色幽默的筆觸反思經典作品與現代文學、作家創作的路徑與困境:寫或不寫;能(會)寫或不能(不會)寫;為何創作,怎樣文學;這是所有執筆的作家共同面臨的宿命與抉擇。
文學是一個千古大哉問的議題,寫作也是一種風險。在維拉馬塔斯之前,許多作家也都提出類似的質疑和省思。梅爾維爾的「巴托比」,原是一位律師事務所抄寫員,這樣的角色,和阿根廷作家馬可.德涅比(Marco Denevi)的〈快樂的謄寫員〉(El escriba feliz)更貼近。德涅比在這篇極短篇中諷刺作家不一定要會寫作,只要有一位具有文學素養、稱職的潤飾文膽即可,他們是共生共榮的連體嬰。「快樂的謄寫員」以揶揄名作家夥伴自娛「愚」人,而「名作家」為名利甘受戲謔。維拉馬塔斯用了不一樣的體例重述德涅比嘲諷作家的虛榮與盲點,指出此種「名譽」與「榮耀」是荒謬的。一個「名字」與一篇「文字」之間會形塑一種從屬和所有權的關係,變成創作的窒礙。
西班牙詩人政治家甘波阿莫(R. de Campoamor)寫實風格強烈的詩風,在領航時期書寫的〈誰懂寫作!〉(!Quien supiera escribir!)詩篇傲視同儕,道出他個人對韻文書寫和詩風的獨到見解,但是他的作品卻在唯美的現代主義風潮披靡下迅速被煙沒。在大江東去的浪濤裡,甘波阿莫的際遇可也是「巴托比症候群」的作家之所以不再寫作的疑慮?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erez-Reverte)的《大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指出大師如大仲馬,亦不諱言他有一個蒐奇出點子的寫作團隊,以便應付連載小說每日刊登的壓力。瓜地馬拉小說家蒙特羅梭的寓言故事集──《動物禪》(或譯《黑羊》,La oveja negra y demas fabulas),除了《巴托比症候群》裡提到的〈最聰明的狐狸〉(身無分文又帶憂鬱性格,於是決定當作家!),還有兩篇涉及寫作主題:一篇是〈想當諷刺作家的猴子〉:猴子為了洞悉人性而廣結善緣,最後卻因交遊廣闊、諸多顧忌而寫不成任何一篇諷刺故事;另一篇〈寓言作家和他的書評家〉,描述寓言作家完全同意書評家犀利嚴苛的批評,以致於書評家已無話可說。蒙特羅梭這簡短精要、鞭辟入裡的寓言集,猶如凹凸鏡,讓寫作的糾葛一一顯影。巴特的《寫作的零度》試圖扭轉激進文學的結構主義的論述,或是「作者之死」的辯證,則間接在文學批評層次平添作家的「巴托比症候群」。
《巴托比症候群》一開始是解析「不寫作的作家」的症狀,好似宣示文學末日的悲劇;漸次地,作者不斷延伸,擴充探索的範疇,進而描述「寫不完」的作家的現象,例如加達和艾南德茲等人,在創作的歷程中,似乎永遠意猶未盡,致力雕琢「沒有結局的藝術」,創造「未完」與「待續」的謎團。這是一種技巧的鋪陳,也可能是作家的瓶頸。從第三十章起,開始延伸耙梳「反巴托比症候群」,喬治.西默農、羅伯特.穆齊爾,甚至加達都是「反巴托比」的作家,正如維拉馬塔斯說:「一開始我可能在寫停止創作的作家,最後我更著重的是,那些活著卻停止寫作的人。」因此,也有必要凸顯另一端對位的作家的樣貌。小說中,維拉馬塔斯寫出千面作家的性格與容顏,甚至虛構了何柏.得韓(維拉馬塔斯的「他我」);偏執狂貝雷斯--這位作家,因擔心被剽竊而不寫。維拉馬塔斯在這兒影射了今年六月辭世的諾貝爾文學獎薩拉馬戈創作靈感的來源。文學大師如薩拉馬戈,也有波赫士所謂的「生命之虎」──難以超越的無限。維拉馬塔斯解析這幾多症候群的意圖,即為替寫作找尋出路,讓末世的憂心轉化為期望的啟示錄。也是小說一開始便有的伏筆:
再不堪、再痛苦的經歷,每個人都難免想要透過記憶,找回那些突然湧上心頭的片段與感動。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寫作」。
特別是在這個道德日益淪喪的年代,人們的眼光總是冷漠、迴避。而「文學」,即使我們再怎麼逃避、忽略它存在的價值,它依舊是不讓過去遭人遺忘的良方。
又如,作者引用德爾.朱帝切的小說,在他闡釋「寫作之不可能」後,仍試圖開拓新視野,提出追尋新理想的可能,而推論出「寫,總還是比不寫好」的結語。即使小說最後認為托爾斯泰以巴托比的告別式離開人間,末世的滄桑也正意味啟示的轉折,從「不」的迷宮中解脫出來:「做你所當做」。維拉馬塔斯曾說了一個矛盾修辭,說他之所以寫作是為了不想當作家,只為了讓人讀他。他在寫作與作家之間又畫出一條陰影線。其實,所有的讀者都是不寫作的作家,而讀者,沒有「不」的迷宮;閱讀,是最精緻且價廉的旅行,有讀者,就有作家。
【導讀】
文學末世啟示錄◎張淑英(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巴托比症候群》,維拉馬塔斯的第十八部作品,也是西班牙知名文學雜誌《幻想》(Quimera)由讀者票選的二○○○~二○○九年十本具代表性的小說排序第二名。《巴托比症候群》以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為楔子,敘述一位上班族,在千禧年到來之前,克服自己二十五年來未曾提筆的心靈創傷,用書寫一個月的日記的方式(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八月七日),另增頁腳眉批,評論一些「看不見的文本」,開啟了一連串他對文學的探索與詰問,解釋作家創作與不創作的理由。《巴托比症候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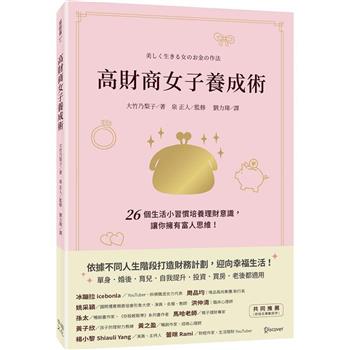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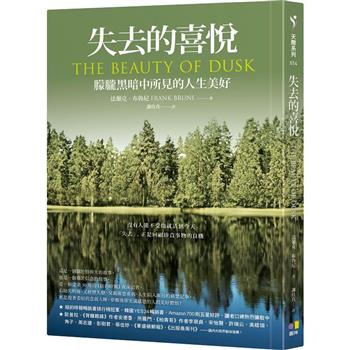









西班牙鬼才作家安立奎‧維拉馬塔斯藉由一個曾有寫作夢想,但中斷寫作達二十五年的主人翁,某日忽然興起研究「巴托比」作家的想法,便一頭栽入巴托比世界的故事。巴托比是一群拒絕世界的人,出自赫曼‧梅爾維爾的小說《錄事巴托比》,敘述一個抄寫員,生活一成不變,總是否定別人的要求,抱持一種巨大的負面態度在過活的人。這樣的態度,發生在寫作上,於是造成了一群巴托比作家,也就是拒絕寫作的人。 書中討論了許\多巴托比,他們有的是極早就已成名,卻斷然拒絕繼續寫作,如韓波;有些是知識淵博的思想家,卻終生未曾出版一本著作,如波比‧巴茲冷。這些作家都有自己成為一位巴托比的理由,有些已成名的作家,害怕他人的期待,怕之後的作品會走下坡,於是無法再繼續寫作;有些則認為寫作無法達到心中的完美,導致有將作品留在「虛無」才是完美的想法;或是等待作品完成的期待感,更甚於作品真正完成的力量;也有的作家以「拒絕」、「放棄」、「沉默」加總而來的極端念頭,藉以表達對這個世界文化已經生病的抗議;又或者是不被認同的作品,於是作家以停止寫作表達對這個拒絕他的世界的不滿;等待靈感;江郎才盡;激情過去……等,這種種的想法,都是巴托比作家面對自己不再提筆的理由。主人翁愈是探尋這些巴托比症狀,愈是發現自己也深陷巴托比「拒絕」的泥淖,因為答案的核心只會愈來愈偏離該有的中心,每個作家都有他們自己不寫作的理由,於是這個研究無法統整出一個綜合的原因和標準,只會愈來愈無頭緒,愈來愈加大,於是故事的主人翁認為面對這個說不完的故事,決心要離開故地,去外地發展,他認為像日全蝕一樣,一點一滴走向黑暗,永遠都是最好的結局。 這或許\是一個無俚頭的故事,因為所要探尋的竟是「不」的本質,「不」的答案只會是否定,不會是肯定。所以這註定是個沒有結論的探尋,但就在這「否定」的假設中,讀者卻可以看到許\多多采多姿關於作家的事實,用「實」來填滿這個巴托比議題的「虛」,使得本書變成了一本內容豐富又具有幽默氣質的書。看著主人翁不斷在這些「不」的問題上打轉,其認真的態度及敘事的口吻,具有滑稽的喜感。但面對這個嚴肅的巴托比議題,他又能言之有物,切中核心的去討論。演奏者通常都知道,最能顯露演奏功\力,就是快板慢板兼融的曲子,除了成熟的技巧,還要有充沛的情感,這通常也是最難表現的。本書的創作,就像是一首快慢兼具的曲子,「虛」「實」不斷的交錯出現,並融合了「嚴肅」與「輕鬆」的態度,讓本書成為一本深度與厚度都驚人的經典之作,深奧卻不艱澀難懂,是一本讀完後還會會心一笑的小說。 書中揭露的「巴托比」概念,也讓讀者重新認識這個詞彙,甚至運用到更多面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某種領域上的巴托比,小時候半途而廢的樂器學習,或是長大後追逐趨勢的進修風潮,成千上萬的巴托比拒絕了當初自己的選擇,然後被歷史拋在腦後。歷史學家總是研究特殊的人,以分析名人偉人的獨特性來藉此了解歷史的通則,本書藉由研究一些名作家,但卻引導出了更大的議題,巴托比是沒有通則的,就像這世界的每個人都是巴托比,這世界的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如此,但生命並不是消極性的,故事的主人翁告訴我們,他已經實現並達到了自己的目標,「我,曾經存在」、「活過的生命都是值得的」,所以他才能目空一切的慢慢消失,於是積極其實是戰勝了消極,如同托爾斯泰的遺言一樣:「做你所當做的,無論發生什麼事。」唯有認真的活過生命的人,才有資格驕傲的拒絕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