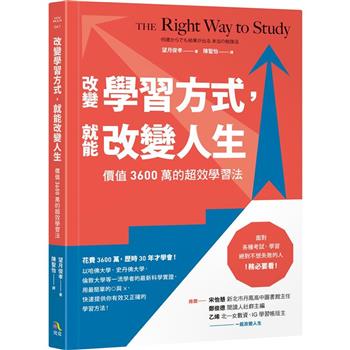當她曾對我閃耀著光芒的雙眼,漸漸歸於暗寂,
我卻在另一雙眼眸之中,再次尋到了她……
在乍見貴族千金克勞黛的那一瞬間,尼可拉斯便注定要一輩子為她癡狂,只因他的心已深深被她姣好的氣質與青春的胴體給徹底征服了!身為宮廷畫家的他敏感多情、才華洋溢,但這並不能改變他與她之間身分懸殊的差距,難以跨越的鴻溝,注定了兩人無法相愛的命運。
帶著她凝視他時眼眸中盈滿的渴望與悲傷,尼可拉斯默默承受著克勞黛即將奉父母之命嫁給他人的痛楚,來到布魯塞爾繼續他未完成的繪畫工作。在這兒,日夜思念心上人的尼可拉斯卻意外遇見了另一個美麗的女孩──艾莉埃娜,而她的活潑開朗也宛如救贖般地讓尼可拉斯暫時忘卻了情傷。然而,就在一切逐漸安定下來之後,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卻又讓尼可拉斯再度陷入痛苦之中──艾莉埃娜竟與克勞黛面臨相同的命運,她也將被迫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男人……
作者崔西.雪佛蘭以純真的女人和象徵情慾的獨角獸為藍圖,編織出一個屬於創作熱情和執著追求愛情的動人故事;作者細膩的刻畫與獨特的詮釋方法,更讓貴族千金與宮廷畫家的戀情,藉由一幅幅美麗細緻的壁毯,娓娓訴說著亙古流傳的動人愛情故事!
作者簡介:
崔西.雪佛蘭 Tracy Chevalier
一九六二年出生於美國首府華盛頓,一九八四年遷居英格蘭。一九九四年她獲得英國東安哥拉大學創意寫作碩士學位。
崔西的處女作《純藍》即一舉榮獲史密斯文學獎年度新人獎,《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與《天使不想睡》則是她備受讚譽的個人代表作。她的作品一貫以舊時代女性試圖突破環境限制、改變自身命運為主題,細膩敏銳,深刻動人。
崔西目前與丈夫及兒子定居於倫敦。
譯者簡介:
盧玉
河南魯山人。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譯有《一輪月亮與六顆星星》、《朝聖》、《哈!小不列顛》、《比利時的安愁》、《愛情法則》、《伊莉莎白的祕密》、《莫妲》等書,現為專業譯者。
章節試閱
『那麼,你對「南錫之役」知道什麼?』里昂問。
我聳聳肩。『那有什麼關係?所有戰役還不都一樣,不是嗎?』
『這就像是說所有女人都一樣。』
我微微一笑。『我再說一次──所有戰役都一樣。』
里昂搖搖頭。『我可憐你未來的妻子。現在你說,你的壁毯裡要畫什麼?』
『馬匹、穿甲冑的戰士、軍旗、長矛、劍、盾牌、鮮血。』
『路易十一要穿什麼?』
『當然是穿甲冑嘍,或許在他頭盔上會有一根特別的羽飾。說實話,我不知道,不過我認識可以告訴我這些事情的人。應該會有人拿著皇室軍旗,我想。』
『我希望你的朋友們比你聰明,可以告訴你,路易十一並沒有參加「南錫之役」。』
『噢。』這就是里昂.勒.維越的作風──讓他周圍所有人出醜,除了他的老闆。你是不能讓尚.勒.維斯出醜的。
『好。』里昂從口袋拿出幾張紙,放在桌上。『我已經和大人討論過壁毯的內容,也做了些測量。當然,你必須再去做更精確的測量。就是這些。』他指著他大致畫出的六個長方形。『這裡和這裡可以掛兩幅長畫,另外還有四幅比較小的。這是戰役的順序。』他仔細地解說這場戰事,為每幅壁毯提示畫面──雙方陣營的集結、最初的攻擊、兩個混戰的場面,接著是『大膽』查爾斯 之死,以及勝利一方的凱旋遊行。雖然我聽他說著話,也在紙上畫草圖,但是一部分的我卻站在一旁,不明白自己同意做的是什麼事。這些畫中不會有女人,不會有微細和精緻的東西,不會有我可以輕易畫出來的東西。這筆錢我不但得辛辛苦苦地賺,還得花上好長一段時間。
『畫好了以後,』里昂提醒我,『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我會把畫帶到北方給織工,他的底圖畫家會把畫放大,用來織壁毯。』
我應該高興不用把馬畫得很大,然而我卻想保護我的作品。『我怎麼知道這個底圖畫家能夠勝任?我可不要他把我的圖樣給糟蹋了。』
『他不會改變尚.勒.維斯決定了的事,只會讓設計和壁毯的製作變得更好。你沒有畫過很多壁毯嘛,是不是,尼可拉斯?只有一幅盾徽吧,我相信。』
『那還是我自己放大的──我根本用不著底圖繪者。這一份工作我一定可以自己來。』
『這些壁毯和盾徽是很不一樣的,它們會需要有一個合適的底圖畫家。等一下,有件事我忘了提,你要確定這些畫裡一直都有勒.維斯家的盾徽,大人堅持這一點。』
『大人打過這場仗嗎?』
里昂笑了。『無疑的,在「南錫之役」時,尚.勒.維斯遠在法國的另一邊,替國王做事。這不要緊的,你只要把他的盾徽畫在其他人拿著的旗幟和盾牌上就行了。你該去看看那場戰役和其他戰事的圖畫,你可以到『舊寺廟』街上的傑哈德印刷廠去,他的一本書裡有「南錫之役」的版畫。我會告訴他你要去。好啦,我就讓你去測量這間房了,如果有問題,儘管來找我。聖枝主日 之前把你的草圖拿給我看──如果我希望改動,你會需要有足夠時間去改,再讓大人看。』
顯然里昂是尚.勒.維斯的眼睛,我必須使他滿意,而如果他看了喜歡,尚.勒.維斯也會。
我忍不住要問最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挑我來做這件事?』
里昂把他身上的素面棕袍拉緊。『我沒有。要是由我來挑人,我會找個畫過更多壁毯的人,或者直接去找織工──他們的手邊有很多設計圖樣,可以直接使用,那樣價錢比較便宜,而且他們很擅長設計。』里昂一向坦白。
『那為什麼尚.勒.維斯挑選我?』
『你很快就會知道了。那麼,明天來找我,我會準備好文件給你簽,還有錢。』
『我還沒有同意條件呢!』
『噢,我想你已經同意了。有些委託工作是藝術家不會拒絕的,這就是其中之一,尼可拉斯.德斯.安諾桑。』他看了我一眼,然後離去。
他沒說錯。一聽我的語氣,就知道我想接下這份工作。不過這些條件還算是不錯,事實上,里昂殺價殺得不多。突然間我懷疑他是不是仍然用巴黎里佛來算。
我把目光移到我將要大肆妝點的四壁。兩個月要畫出二十匹馬和騎士!我站在房間一端,朝另一頭走去,數出十二步,然後橫過房間,數了六步,再把一張椅子拉到牆邊,站上去。不過就算我盡量把手往上伸,離天花板還是遠得很。於是我把椅子放回去,猶疑了片刻,登上橡木桌,再往上伸手,但是離天花板還是有一個身高的距離。
我正在想要到哪裡找一根長桿子去量高度,忽然聽到身後有一陣哼歌的聲音,於是轉過身,只見一個女孩子站在門口看著我。這是個可愛的女孩──皮膚白皙、額頭飽滿、長鼻子、髮色如蜜、眼睛明亮。我從沒看過這樣的女孩子,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妳好哇,美人兒。』好不容易我終於說出口。
女孩笑了起來,蹦蹦跳跳地跑過來。她穿著一襲簡單的藍裙,一件緊身上衣,方形領、窄袖子。衣服的剪裁得宜,毛料質地細緻,但是並不華麗。她也圍著一條樸實的圍巾,一頭長髮幾乎披散到腰間。和打掃壁爐的女僕相比,她明顯優雅得多,不可能是女僕。或許是侍女吧?
『我們夫人希望見您。』她說完轉身就跑走了,仍然笑著。
我沒有動。我從多年的經驗中得知,只要待在原處不動,小狗、獵鷹和女士就會自己回來找你。我聽見她的腳步聲踩在隔壁房間的地板上,然後就停住。過了一會兒,腳步聲又起,她出現在門邊。『您要過去嗎?』她仍然在笑。
『我會去的,美人兒,只要妳肯陪我走,不要急急忙忙走在我前面,好像我是一隻妳必須逃離的惡龍就行啦。』
女孩又笑了。『來吧。』她招了招手,這次我從桌上跳下。我必須加快步伐,才能趕得上從一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的她。她的裙子不住拍動,彷彿一陣神祕的風將她吹著走一樣。靠近她,可以聞到一種香甜又辛辣的味道,隱約還有股汗水味。她的嘴在動,好像在嚼著東西。
『妳嘴裡有什麼啊,美人兒?』
『牙齒痛。』女孩伸出舌頭,粉紅的舌尖上有一顆丁香。看到她的舌頭,令我慾火高漲,我想往她身上撲過去。
『啊,那必定很痛了。』我可以吸吮她的舌頭,讓她好受一些。『好,夫人為什麼想要見我?』
女孩盯著我,感到很有趣的樣子。『我猜她會自己告訴你。』
我慢下腳步。『急什麼?她應該不會在意我們在路上聊一會兒吧?』
『你想要談什麼呢?』女孩轉身要登上一個圓形樓梯座。
我跳上樓梯,站在她面前,阻擋她往上走。『妳喜歡什麼樣的動物?』
『動物?』
『我不希望妳把我想成一條惡龍,我想要妳把我想成別的東西,妳比較喜歡的東西。』
女孩想了想。『那或許是長尾鸚鵡。我有四隻,牠們會吃我手裡的食物。』她繞過我跑到我上方的階梯,但沒有再往上走。沒錯,我想,我的傢伙已經準備好,她要來一探究竟了。再靠近些,我的小乖,看看我的配備,摸摸我。
『我不要做鸚鵡,』我說,『妳當然不會把我想成一隻嘎嘎亂叫的學人精吧!』
『我的鸚鵡才不會亂叫。不過,你是個畫家,不是嗎?你的工作不就是模仿真實的東西嗎?』
『我會把東西變得比真實的還要美麗。不過呢,好姑娘,有些事情是油彩也無法改善的。』我繞過她,又登上三級階梯。我要看她會不會走過來。
她果真走過來了。她的眼睛依然清澈、圓睜著,但是她的嘴角露出了會心的笑容。她用舌頭將嘴裡的丁香從一邊臉頰推到另一邊。
我要擁有妳。我心想。我一定要。
『也許你是頭狐狸,』她說,『你的頭髮棕中帶點紅色。』
我噘起嘴。『妳怎麼這麼狠心?我看起來很陰險嗎?我會去欺騙人嗎?我只會走旁門左道,不懂得光明正大的道理嗎?我情願是條狗,趴在女主人腳邊,永遠忠心不貳。』
『狗太要人注意了,』女孩說,『而且牠們都會撲上來,用牠們的爪子把我的裙子弄髒。』她又繞過我,這次她沒停下來。『來吧!夫人在等著了,我們不能耽誤她。』
我得快點了,我在其他動物上頭浪費太多時間了。『我知道我想成為哪種動物了。』我喘著氣,在後頭追著她。
『是哪種動物呢?』
『獨角獸。妳知道獨角獸的事嗎?』
女孩不屑地哼了一聲。她已經走到樓梯最上層,正打開另一個房間的門。『我知道牠喜歡把頭放在少女的大腿上。你喜歡做這種事嗎?』
『啊,別把我想得這麼粗俗。獨角獸做的事比這優雅多了,牠的角有種特別的力量,妳知道嗎?』
女孩放慢動作,看著我。『牠會做什麼事?』
『如果一座井被下了毒……』
『那裡就有座井!』女孩停下步子,指著一扇窗戶外的庭院。一個更年輕的女孩子正倚在一座井邊,朝井裡看去,金色陽光灑在她的頭髮上。
『吉妮老愛那樣,』女孩說,『她喜歡看自己的倒影。』這時我們看到女孩子朝井裡吐了口口水。
『如果你們那座井被人下毒,美人兒,或者被人像吉妮那樣子弄髒了,獨角獸可以過來把牠的角伸到井水裡,水就會回復清澄了。妳認為這怎麼樣呢?』
女孩用舌頭移動了嘴裡的丁香。『你要我認為怎麼樣?』
『我要妳把我想成妳的獨角獸。有些時候,像妳這麼一個美人兒都會有髒汙。每個女人都會,這是夏娃的懲罰。不過妳可以再次變純潔,每個月,只要妳讓我照料妳。』一次又一次與妳燕好,讓妳又哭又笑。『每個月妳都可以回到伊甸園。』就是這最後一句話,我每次獵豔都能得逞──只要使出樂園這一招,似乎都可以讓她們落入圈套。她們懷著能夠找到樂園的希望,總會張開她們的雙腿。或許有些人就果真找到了也不一定。
女孩子笑了,這一回笑得很刺耳。她準備好了。我伸手去捏她,算是兩人說定了。
『克勞黛?是妳嗎?什麼事耽誤了妳這麼久的時間?』遠處一扇面對我們的門開了,一個女人站在那裡瞪著我們,兩隻手臂叉在胸前。我立刻放手。
『對不起,媽媽。他來了。』克勞黛往後退,朝我比一比。我彎腰行禮。
『妳嘴裡有什麼東西?』女人問。
克勞黛把口裡的東西吞下去。『丁香。我牙痛。』
『妳應該嚼薄荷──那對牙痛要好得多。』
『是的,媽媽。』克勞黛又笑了起來──或許是笑我臉上的表情吧。她轉過身子跑出房間,把房門在身後摔上。房間響起她腳步聲的迴音。
我不寒而慄。我剛才竟然想要引誘尚.勒.維斯的女兒。
過去我來福爾街的房子時,只有從遠處看過勒.維斯的三個女兒,看著她們跑過院子、騎馬離開、和一群女人走去聖日耳曼德佩。井邊的那個女孩自然也是她們之一──要是當時我多加留意,在我看到她的頭髮和態度舉止時,一定就會明白她和克勞黛是姐妹,那麼我就會猜到她們是什麼身分,就絕不會告訴克勞黛那個獨角獸的故事了。但是我卻沒有想到她的身分──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跟她上床。
只要克勞黛把我說的話告訴她父親,我準會被趕出去,這個委託工作也沒了,我也就再也見不到克勞黛了。
但我比先前更想要她,而且不只是要和她上床。我想要和她一起躺著、跟她說話,觸摸那張嘴、那頭髮,逗她笑。我猜想她是跑到房子的哪個地方了,我是絕不准去到那個地方的──一個巴黎的畫家不可能和貴族的女兒在那裡。
我定定站著,思索這些事。或許我站得太久了,門口的女士動了動,垂在她腰間的念珠碰到袖口的釦子,發出了聲響,讓我從思緒中跳脫。她正看著我,彷彿已經猜到我腦子裡想的事,不過她什麼話也沒說,只把門推開走進去,我也跟著走進去。
我曾經在許多仕女的寢室裡畫過微細畫,這間房也沒有多大不同,房裡有一張栗木床,床上掛著藍色和黃色的絲綢布縵,還有圍成半圓形的橡木椅,椅子上還有繡花的椅墊。靠牆有張小几,擺滿了瓶子和一個珠寶盒,還有幾張衣櫃。一扇開著的窗,框住聖日耳曼德佩的景色。聚在屋角的是她的侍女,正做著刺繡的活兒,她們一起對我微笑,看來不像有五個人,倒像是一體的。我暗罵自己竟然還以為克勞黛是她們當中的一個。
珍涅芙.德.南特爾──尚.勒.維斯的妻子,這幢房子的女主人──在桌前坐下。她顯然曾經和她女兒一樣美麗,雖然現在她仍然是個秀麗的女子,有飽滿的額頭和細緻的下巴,只是克勞黛的臉是心形,而她的臉已經成了三角形。當了尚.勒.維斯的妻子十五年,使她的線條變得深刻、下巴堅毅、額頭也添了紋路。相對於克勞黛那雙清澈的梨色眼,她的眼睛就像是黑醋栗。
她至少有一項勝過女兒,那就是她的衣著比較華麗──奶油色和綠色的織錦布上,有精細的花葉圖樣。她的頸部戴著精緻的首飾,頭髮用緞帶和珍珠編成辮子。她絕對不會被誤認為侍女──她的穿戴顯然就是要人伺候的貴婦。
『你剛剛跟我先生在大廳裡,』她說,『討論壁毯。』
『是的,夫人。』
『我猜他想要畫一場戰役。』
『是的,夫人。「南錫之役」。』
『壁毯上會有哪些場面?』
『我不確定,夫人。大人只告訴我要畫壁毯,我需要先畫些素描,才能肯定。』
『會有人員嗎?』
『當然,夫人。』
『馬呢?』
『有的。』
『血呢?』
『我沒聽懂,請再說一遍,夫人。』
她揮揮手。『這是一場戰役,會有鮮血從傷口流出來嗎?』
『我猜想是的,夫人。「大膽」查爾斯將會戰死,當然的。』
『你打過仗嗎,尼可拉斯.德斯.安諾桑?』
『沒有,夫人。』
『我要你想像自己是個士兵,只要想像一下就好。』
『可是我是宮廷的微細畫家呢,夫人。』
『這我知道,不過你就暫時假裝是一名在「南錫之役」打仗的士兵吧。你在那場戰爭裡丟了一條手臂,然後你坐在大廳裡,做我和我丈夫的客人。在你旁邊的是你的妻子,是你那個年輕漂亮的妻子,她幫助你面對少了一條手臂所產生的困難──掰開麵包、扣上劍扣、上馬。』珍涅芙.德.南特爾頗有節奏地說著,彷彿正在唱一首搖籃曲。我開始覺得自己在一條河上隨波漂流,不知自己要漂往何方。
她會不會有一點瘋了?我心想。
珍涅芙.德.南特爾兩臂交握,把頭歪向一邊。『你在用餐時,看到這些壁毯,上頭畫著使你失掉一條手臂的戰役。你認出「大膽」查爾斯被殺的畫面,你的妻子也看到從他傷口迸出的鮮血。你看到的每個地方都有勒.維斯的旗幟,但是尚.勒.維斯人在哪?』
我努力回想里昂方才說過的話。『大人在王上身邊,夫人。』
『是的。在這場戰役中,我丈夫和國王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的宮中,離南錫很遠。好,身為這個軍人,你明明知道尚.勒.維斯沒參加「南錫之役」,卻又看到這些畫裡到處都是他的旗幟,你會作何感想?』
『我會認為大人是國之重臣,才能陪伴君側,夫人。他的建言要比他的戰技重要。』
『啊,你可真是圓滑,尼可拉斯。你比我丈夫還更像外交官,不過這答案恐怕並不對。我希望你仔細想想,實在地告訴我,這樣一個軍人會怎麼想?』
現在我知道我在這一條言語的河流上要漂向哪裡了,我不知道一旦我停泊在岸邊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生氣,夫人。他的妻子也會。』
珍涅芙.德.南特爾點點頭。『對呀,這就對了。』
『可是也不能因為……』
『此外,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兒們在招待客人餐宴的時候看著血腥的屠殺場面。你見過克勞黛,你會希望她一邊吃東西,一邊盯著一匹馬腹的某個刀口,或者是一個頭被砍掉的人嗎?』
『不希望,夫人。』
『那就不要讓她看到。』
在角落的那些侍女對著我嬉笑。珍涅芙如願地把我帶到這一步。她比我畫過的大多數貴族女人都要聰明,因為這一點,我發現我想要討她歡喜,而這可能會是件危險的事。
『那麼,你對「南錫之役」知道什麼?』里昂問。我聳聳肩。『那有什麼關係?所有戰役還不都一樣,不是嗎?』『這就像是說所有女人都一樣。』我微微一笑。『我再說一次──所有戰役都一樣。』里昂搖搖頭。『我可憐你未來的妻子。現在你說,你的壁毯裡要畫什麼?』『馬匹、穿甲冑的戰士、軍旗、長矛、劍、盾牌、鮮血。』『路易十一要穿什麼?』『當然是穿甲冑嘍,或許在他頭盔上會有一根特別的羽飾。說實話,我不知道,不過我認識可以告訴我這些事情的人。應該會有人拿著皇室軍旗,我想。』『我希望你的朋友們比你聰明,可以告訴你,路易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