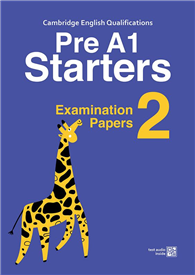每個故事都是一場表演,讓我們目眩神迷!──華盛頓郵報
轟動國際文壇《少年Pi的奇幻漂流》創作的起點!
楊‧馬泰爾嚴選短篇小說代表作!
我們用故事記憶這世界,重新創造它、擁抱它。
讓我來告訴你幾個故事:一段以時間為軸、跨越了疾病與死亡的動人生命故事;一名酗酒的清潔工,與他在破敗廢墟內奏出美妙天籟的人生故事;一位典獄長,和因他而掙扎著死了千百回的絞刑犯的人性故事;一座製造出『一直用到進天國的鏡子』的機器,以及感傷又喜悅的回憶故事……
故事一說出口,便有了自己的生命,而當今最受矚目的作家楊.馬泰爾更用他獨特的優雅與原創性,賦予了它們超凡的生命力!毀滅與創造、戰爭與音樂、死亡與官僚、抽象的記憶與現實的物質……這四個故事主題各異,卻都深深撼動人心,而充滿創意的寫作形式與雋永有味的情節,在在顯示楊‧馬爾泰的創作才華,早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之前,即已令人驚豔!
作者簡介:
楊.馬泰爾Yann Martel
外交官之子,一九六三年出生於西班牙。幼時曾旅居哥斯大黎加、法國、墨西哥、阿拉斯加、加拿大,成年後作客伊朗、土耳其及印度。畢業於加拿大特倫特大學哲學系,其後從事過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包括植樹工、洗碗工、警衛等。
二十七歲始以寫作為生。曾兩度造訪印度想要寫作,結果旅費用盡,幾乎無以為繼。但是馬泰爾有一天來到孟買附近的一個小鎮,忽然文思泉湧、欲罷不能,情節內容一一浮現。他花了六個月的時間造訪印度南部所有的動物園,並深入了解當地生活,隨後回到加拿大,開始鑽研各宗教教義,而他的曠世奇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逐漸成形。該書出版後立即讓國際文壇為之驚豔,不但全球已熱賣突破七百萬冊,更贏得英國文壇最高榮譽『曼布克獎』、德國出版界最高榮譽『德國圖書大獎』等六項國際大獎,以及十幾項大獎的提名和年度好書推薦!英國出版社並特別與英國《泰晤士報》、澳洲《年代》雜誌共同舉辦了一項國際插畫競賽,由第一名得主為本書繪製全新彩色插圖,推出精美的『繪圖版』。《少年Pi的奇幻漂流》目前並已被改編拍成電影。
馬泰爾另著有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真相》,處處可見其獨特的原創性與細膩優雅卻充滿力道的敘事風格。
自二○○五年開始,他成為加拿大薩克其萬大學的駐校學者,目前也定居於該地。
譯者簡介:
張定綺
台大外文系研究所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研究。曾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文版資深編輯、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筆譯組召集人,曾任職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譯著甚豐,屢獲新聞局評鑑為優良中譯作品。
章節試閱
我認識保羅不算久,兩人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多倫多東郊洛鎮的埃力斯大學相遇。我曾經休學,到印度工作和旅行,認識保羅那一年,我二十三歲,正在讀大學的最後一年。保羅剛滿十九歲,是個大學新鮮人。我立刻喜歡上保羅自然流露的聰明與好奇心,還有他對什麼事都存點懷疑的態度。我們一拍即合,經常在一起廝混。我年紀比較大,閱歷比較多,講話一派老夫子的權威,保羅則像年幼無知的門徒般聆聽──只不過他會挑起一邊眉毛,把我的誇大其詞迎面丟回來。然後我們會哈哈大笑,拋開這些角色。我們的關係很清楚:非常好的好朋友。
後來,第二個學期才剛開始,保羅就病了。他早在聖誕節便開始發燒,從那時起,他就染上了一種根除不了的乾咳。最初,他──我們──都不以為意,感冒、空氣太乾燥──無非就是這些因素吧!
情況慢慢變糟,現在我想起很多當時根本不放在心上的跡象。保羅吃飯總剩下食物,還有一次抱怨拉肚子,以及不能用體質單薄解釋的精神不濟。有一天我們上圖書館,正爬著樓梯,不過二十五級,爬到頂端便停下腳步。我還記得我們停步的唯一理由就是保羅上氣不接下氣地要求休息。他體重好像也輕了,冬天穿著厚重的一堆衣服,實在很難判斷,但稍早之前,他確實比較壯碩。確定發生問題後,我們談論這件事,我扮演醫生,說:『我們來看看……氣喘、咳嗽、體重減輕、容易疲倦。保羅,你患了肺炎。』我當然是開玩笑。我懂什麼?但他果然是得了那方面的病。肺囊蟲肺炎,簡稱PCP。二月中旬,保羅到多倫多去看他的家庭醫生。
九個月後,他死了。
愛滋病。他在電話上對我宣佈,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他離開了將近兩星期,說他剛從醫院回家。我驚訝得有點頭昏。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想到我自己。他有沒有在我面前割傷過自己?如果有,是怎麼處理的?我有沒有用過他的杯子?分享他的食物?我試著確認他的身體系統跟我的身體系統之間,可曾有互通的管道存在。然後我才想到他。我想到同性戀行為和嗑毒。但保羅不是同性戀,雖然他沒有直接跟我談過這種事,但以我對他熟識的程度,連一點曖昧的形跡都沒有。我同樣無法想像他吸食海洛因上癮。總而言之,情況不是那樣的。三年前,他十六歲的時候,跟父母到牙買加度聖誕假期,一家人出了車禍。保羅斷了右腿,失了不少血,在當地醫院接受輸血。六個車禍目擊者到醫院志願捐血,其中三人的血型符合。打了幾通電話,做了些調查,結果發現這三人中有一人,出乎意料地在兩年後治療肺炎時死亡,驗屍證實此人有嚴重的弓蟲性腦炎──可疑的併發症。
保羅的家在富裕的羅斯岱爾地區,那個週末我去探望他。我其實不想去,我壓根不願意想這件事。我問──我想以此為藉口──他是否確定他父母願意接待訪客?但他堅持要我去,我只好去了。我開車去多倫多,找到那兒。我對他父母的猜測沒錯,因為剛開始那個星期,受傷最重的不是保羅,而是他的家人。
得知保羅恐怕已遭病毒感染的那天,他父親傑克終日一語不發。隔天一大早,他父親從地下室取出工具組,在睡袍外罩上冬季外套,走到車道上動手破壞自家的汽車,因為在牙買加發生車禍的時候,是他開的車,雖然車禍不是他的錯,而且他們當時開的是另一輛租來的車。傑克用榔頭敲碎了所有的車燈和玻璃窗、把整輛車拆成廢鐵和垃圾、把鐵釘敲進輪胎,還從油箱裡吸出汽油,澆在汽車裡外放火燒車。這時鄰居叫了消防隊,隊員趕到現場滅火。警察也來了。他父親結結巴巴地說明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大家都非常諒解,警察沒起訴就離開了。他們只問他要不要去醫院,而他不要。所以,那就是我到達保羅家位於街區邊緣的大房子時看到的第一樣東西:一輛燒毀的賓士車,上面鋪滿了滅火泡沫。
傑克是個勤奮的商業律師,保羅把我介紹給他,他微笑著跟我握手說:『幸會!』然後好像就沒別的話要說了。他的臉很紅。保羅的母親瑪麗在臥室,學校剛開學時我見過她。她年輕的時候取得麥基爾大學人類學的碩士學位,是高段的業餘網球好手,到過很多地方旅行,現在則在一個人權組織兼職。保羅以母親為榮,母子關係非常好。瑪麗極具才幹且精力充沛,但現在她以胚胎的姿勢清醒地躺在床上,看起來像個縐巴巴的氣球,所有的活力都從她身上流光了。保羅站在床旁,只說:『我母親。』她幾乎沒有反應,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保羅的姊姊珍妮佛是多倫多大學社會系的研究生,她表現傷痛欲絕的方式最容易理解,眼睛發紅,臉頰浮腫──看起來糟透了。我無意搞笑,但就連喬治H,他們家的拉不拉多犬也非常難過。牠硬把自己塞進客廳的沙發底下,抵死不肯出來,不停嗚嗚哀鳴。
結果是星期三早晨出來的,從那時起(我星期五去的),他們全家包括喬治H在內,全都粒米未進。保羅的父母沒有去上班,珍妮佛沒有去上學。他們想睡就睡,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有天早晨,我發現保羅的父親睡在客廳地板上,衣著整齊,裹著波斯地毯,一隻手向沙發底下的狗兒伸去。除了瘋狂爆發的來電交談聲外,整棟房子非常安靜。
這一切的核心是保羅,他沒有反應。在一場家中成員都被傷心痛苦壓垮的葬禮中,他是葬禮的指揮,以專業的鎮定和麻木的同情處理一切事務。直到我住在他們家的第三天,他才開始有所反應。但死亡無法被人理解。保羅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但他摸不著箇中涵義。死亡超乎他的理解,那是抽象的理論。他談論自己的狀況,就像談論一則國際新聞。他說:『我快要死了。』就像在說:『孟加拉有渡輪翻覆。』
我本來只想待一個週末──因為還得上學──但最後住了十天。期間我做了很多打掃房屋和烹飪的工作,他家的人沒什麼感覺,不過沒關係。保羅幫我忙,他喜歡這樣,因為這樣他才有點事做。我們把車吊走,更換被保羅父親破壞的電話,我們把房子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們替喬治H洗了澡(牠叫喬治H,因為保羅非常喜歡披頭四合唱團,他小時候每次遛狗都自言自語:『就在這一刻,所有人都不知道,喬裝改扮的披頭保羅和披頭喬治走在多倫多街頭。』他鎮日夢想著在大都會球場或其他類似的場所演唱〈救命!〉)。我們還去採買食物,督促全家人進食。我所謂的『我們』或『保羅幫忙』──實際上指的是我做所有的工作,而他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戴普松和磺胺藥物抑制住保羅的肺炎,但他還是很衰弱,氣喘吁吁。他走動起來像個老頭子,每個動作都很緩慢而吃力。
這家人經過一段時間才克服震撼。保羅生病期間,我注意到他們一共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部分發生在家裡,痛苦逼得太近,他們以各自的方式退縮:保羅的父親專門破壞堅固的東西,像是桌子或電器;保羅的母親神智不清地躺在床上;珍妮佛關在房間裡哭;喬治H則躲在沙發底下哀鳴。第二階段多半在醫院,他們圍在保羅身旁互相打氣,談話、哭泣、互相鼓勵、說說笑笑、講悄悄話。最後來到第三階段,他們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我想你可以稱之為正常,是某種無視死亡存在而度過整天的能力,臉上帶著鎮定、勇敢又有點麻木的表情,那樣的勇氣因為天天都需要,所以變得既悲壯又平凡。這家人有時得花幾個月經歷這三個階段,有時則只要一小時。
我不想談愛滋病對人體的影響,就想像一個人因為生病變得很慘──然後愈來愈慘好了(你無法想像那種逐漸剝蝕、瓦解的過程)。翻開字典查『肉體』(flesh)這個字──一個豐滿的字──然後再查『融化』(melt)。
這還不是最壞的部分,最慘的是因此構築的防禦心理,一種叫做『我不會死』的病毒。被它感染的人最多,因為它專門攻擊活人,那些圍繞在垂死者四周、深愛他們的人。我很早就感染這種病毒。那天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保羅在醫院,他在吃晚餐,全部的晚餐,吃到餐盤乾淨得發亮,即便他一點也不餓。我看著他用叉子把最後一顆豌豆送進嘴裡,還在吞嚥前刻意把每一口食物嚼爛。這會幫助我的身體作戰,每一小口食物都會發揮作用──他心裡正這麼想。每個字都寫在他臉上、身上、整面牆上。我很想尖叫:『別管那顆他媽的豌豆了,保羅。你快死了!死定了!』但舉凡與『死亡』有關的字眼、衍生字、同義字,我們現在交談時都刻意迴避,所以我就坐在那兒,表情一片空白,憤怒在胸中翻騰。每次看到保羅刮鬍子,我的心情就更壞。他下巴上不過長了幾根柔軟的嫩鬚,他生來就不是毛髮濃盛的人。儘管如此,他還是天天刮鬍子。他每天都塗滿一臉小山似的刮鬍膏,再用拋棄式刮鬍刀刮掉。這幅畫面逐漸鐫刻在我的記憶裡:健康忽好忽壞的保羅穿著醫院的衣服站在鏡子前,左右轉頭,把臉上皮膚這邊拉拉、那邊拉拉,一絲不苟地做一件徹底沒用的事。
我那學年搞砸了,不論聽講或上討論課,我都經常蹺課,也沒辦法寫任何報告。事實上,我連書都讀不下去:我翻開康德或海德格,瞪著同一個段落,發呆好幾個小時,想知道裡頭寫些什麼,努力集中注意力,卻一無所獲。在此同時,我開始憎恨自己的國家。加拿大散發一股平淡無聊、自得其樂、與世隔絕的臭味,加拿大人從脖子以下都埋在物質主義裡,從脖子以上都是美國的電視節目。到處都看不到理想主義或嚴謹的生活態度,只有死氣沉沉的庸碌。中美洲、原住民、環保或雷根治理下的美國,加拿大各方面的政策一律讓我反胃。這個國家沒有一樣討我喜歡,完全沒有。我等不及想逃走。
有一天,在一堂哲學──我的主修──討論課上,我負責報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教授是個非常聰明而體貼的男老師,他打斷我,要我說明一個他沒聽懂的觀念。我沉默下來,看著大家坐著的這個擺滿書本的舒適房間。那一刻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就在那一刻,從我的迷惑之中升起一股無法遏止的力量,我被憤怒和憤世的情緒沖昏了頭。我尖聲大叫,隨即起身把厚重的黑格爾課本從緊閉的窗戶扔出去,宛如一陣風般衝出了教室,使出全身力量把門砰的一聲甩上,還對精雕細琢的門板狠狠踢了一腳。
我試圖向埃力斯大學辦理休學,但我錯過了限期,因此提出申訴,出席一個委員會──『大學部名次與申訴委員會』。我休學的理由是保羅,但是當名次與申訴委員會的主席油滑地壓低聲音,要我說明『心情悲痛』是什麼意思時,我看著他,打定主意,絕對不會把保羅的痛苦像個橘子般剝皮分瓣獻出去。不過這次我沒有吵鬧,我只說:『我改變主意了,我要撤回申訴,謝謝你費心。』然後就走了出去。
所以,那年我被當掉了。我不在乎,我到現在還是不在乎。我在洛鎮打混,那是打混的好地方。
但我真正要告訴你的,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主旨,其實是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那不是保羅的家族,他姓阿特西。那也不是我的家族。
事情是這樣的,保羅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病情穩定時就回家,但我印象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住院。在他病情發展的過程中,化驗與治療成為他生活的重心。我會去探望保羅,週間都跑到多倫多去看他一、兩趟,週末通常也去,而且天天打電話給他。我去到那兒,如果他精神夠好,我們就去散步或去看場電影或戲劇。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只是坐坐。保羅和我都不介意光是坐在那兒,聽音樂、想各自的心事。
不過我開始覺得,我們該用這段時間做點什麼。我的意思不是穿上羅馬長袍,對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做出哲學性的思考。早在我們知道他生病之前,我們上學期就做過這種事。那是大學生的特權,不是嗎?你們整晚不睡直到天亮,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聊?還有,當你們讀完第一遍的笛卡爾、巴克萊或艾略特,除了這些,又能聊什麼?不管怎麼說,保羅才十九歲。你十九歲時是什麼樣子?就像一張白紙,充滿希望、夢想和不確定,充滿了未來,人生觀卻幾乎等於零。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兩個必須做點有建設性的事,從一無所有之中創造一點東西,從無意義中創造意義,除了靠一張嘴胡謅些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之外,也要超越這一切,使自己具備那樣的意義。
我仔細思考過這件事。我有很多時間思考:春季時我找到擔任全洛鎮園丁的工作,這種工作讓我雙手忙碌,頭腦卻很自由。
想到這點子的那一天,我正推著柴油剪草機,橫過鎮公所前的草坪,耳朵上戴著工業專用耳罩隔絕噪音。兩個詞讓我驀然停下腳步:薄伽丘與《十日談》。我在印度的時候,曾經藉著一個破破爛爛的版本,讀過這部義大利經典名作。概念如此簡單:翡冷翠城郊一棟孤立的別墅;外界都籠罩在黑死病威脅下;十個人湊在一起,希望苟全生命;他們講故事給彼此聽,藉以打發時間。
就這樣,想像力施展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法,薄伽丘在十四世紀辦到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也可以照辦:我們互相講故事給對方聽。但這次生病的是我們,而不是外界,我們也不逃避這世界。正好相反,我們要用我們的故事記憶這世界,重新創造它、擁抱它。是的,以說書人的身分相聚在一起,擁抱這世界──就這麼辦,這就是保羅和我打破空虛的方法。
這點子我愈想愈喜歡。保羅和我可以創造一個家族的故事,一個大家族,故事變化無窮,但保持相關性,前後一貫,又能生生不息。可以是個加拿大家族,背景訂在現代,考察歷史與文化也會比較簡單。我必須堅定地引導,不讓故事淪為單純的自傳。我也要做充分準備,在保羅太衰弱或沮喪時,一個人就可以把故事講下去。我還得說服保羅,讓他知道別無選擇,講這場故事不是遊戲,跟看電影、聊政治不屬於同一層次。他必須明白,除了故事以外,其他一切都無意義,就連他僅有恐嚇自己作用、充滿絕望的存在主義念頭也一樣。唯一算數的是想像力。
但想像力不會憑空出現。如果我們的故事要有力量、廣度與深度,要避免過分貼近事實、脫離天馬行空的思考陷阱,那就需要有個結構、某種綱領,某種我們盲人能用白手杖探測得到的界石。我絞盡腦汁尋找這樣的結構。我們需要的東西必須既堅定又無束縛,既限制我們,也給我們帶來靈感。
我在收拾草屑時想通了:我們要利用二十世紀的歷史。我的構想是用二十世紀當模型,從每年選取一個事件做為象徵性的綱領。整個故事分成八十六段插曲,隨著世紀漸進的發展,從每一年選取一件大事,每段插曲要與這件大事相互呼應。
想通如何利用我與保羅共度的時間,使我精神大振。
我小心地說明給保羅聽,當時我們在醫院,他正在做化驗。
『我不懂,』他說:『你說「象徵性的綱領」是什麼意思?故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家族仍然存在,我們挑選與情節平行發展的歷史事件,引導我們編這個家族的故事,就像喬伊斯寫的《尤里西斯》與荷馬的《奧德賽》互相平行。』
『我沒讀過《尤里西斯》。』
『無所謂。重點是,小說所有的情節都發生在一九○四年的某一天,地點在都柏林,書名卻來自一部古希臘史詩。喬伊斯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尤里西斯十年的漂泊,跟他的都柏林故事平行對照。他的小說是《奧德賽》隱喻的變形。』
『既然我沒看過,我們何不把那本書朗讀一遍?』
『因為我們不僅要做觀眾而已,保羅。』
『哦。』
『首先,我們必須決定這家人住在哪裡。』
保羅以空洞的眼神望著我,心中仍疑慮──也很疲倦。我堅持這件事,甚至有點不高興。我沒有開罵,但隱約有點火藥味。他臉一歪就哭了起來,我立刻道歉。好吧,我們朗讀《尤里西斯》,這點子多好啊!然後──有何不可?──繼續讀《戰爭與和平》。
我已經走出他的病房,正要踏進電梯,走廊上忽然傳來一陣大喊。
『赫─爾─辛─基!』
我露出微笑。你知道,保羅跟我心有靈犀。我們都很年輕,年輕可以很極端。我們還沒有被習慣與傳統束縛,只要我們高興,隨時可以重來。所以,故事的地點就訂在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很好的選擇,我們都沒去過的遙遠城市,遠比就在我們眼前的城市更容易在想像中玩弄。我回到保羅的房間,他的臉仍因為大聲喊叫而泛紅。
我問他那家人姓什麼。他嘟起嘴巴,瞇著眼睛思索了一會兒,然後發出聲音:『羅卡馬提歐。』什麼?『羅卡馬提歐,羅─卡─馬─提─歐。』我不是很同意,聽起來不像真正的姓氏。聽起來像北歐姓氏的名字比較好,不是嗎?但保羅堅持:羅卡馬提歐──羅─卡─馬─提─歐,他重複道──這是一個有義大利血統的芬蘭家族。那就這樣吧!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找到了,也命名了,他們的故事等著被娓娓道來。我們定了一些規則:由我決定接受哪些虛構部分,禁止使用一看就知道是自傳的素材。故事發生在現代,一九八○年代中期。每段插曲都要在我們一次會面期間講完,而且必須一以貫之,循序漸進地跟二十世紀某一年的某件大事有相似之處。我們要輪流講故事,我負責奇數年,保羅講偶數年。最後,我們同意羅卡馬提歐是兩人之間的小秘密。
我得說明,你不會讀到赫爾辛基羅卡馬提歐家族的故事,某些私密內容不能公諸於世,大家知道它們存在就夠了。敘述羅卡馬提歐家族的故事很困難,尤其是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們剛開始編故事時勇敢又有力,經常辯論或打斷對方,我們的智巧和創意有時連自己都感到意外,也常哈哈大笑──但當你的健康並非處於顛峰狀態時,重新創造一個世界是很累人的事。保羅絕非不願意──他用一個字或哼一聲表示反對,或要我改變方向──而是無能為力,甚至聆聽都會使人疲倦。
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故事往往以耳語敘述,但講給你聽的時候不是耳語。在愛滋病蔓延的年代,我所保留的──在頭腦以外的──就只有這份紀錄。
我認識保羅不算久,兩人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多倫多東郊洛鎮的埃力斯大學相遇。我曾經休學,到印度工作和旅行,認識保羅那一年,我二十三歲,正在讀大學的最後一年。保羅剛滿十九歲,是個大學新鮮人。我立刻喜歡上保羅自然流露的聰明與好奇心,還有他對什麼事都存點懷疑的態度。我們一拍即合,經常在一起廝混。我年紀比較大,閱歷比較多,講話一派老夫子的權威,保羅則像年幼無知的門徒般聆聽──只不過他會挑起一邊眉毛,把我的誇大其詞迎面丟回來。然後我們會哈哈大笑,拋開這些角色。我們的關係很清楚:非常好的好朋友。後來,第二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