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童年,是秘密》
當我正看著比爾.布萊森的新書時,老婆在飯桌上教她的外甥女寫功課,當然,這個叫「美眉」的三年級小女生,聽著窗外公園裡某基督教團體園遊會傳來的歌聲,面對造句與一整行一整行得一筆一筆寫出來的功課,充滿了無奈。她每三秒鐘用手指梳理長髮一次、每五秒幌一次右腳、每二十八秒轉頭對我扮鬼臉一次。老婆顯然瀕臨發怒邊緣,她壓下所有的火氣,用聽似溫和的口吻說:
「美眉,以前二姨和大姨、三姨放學回家都馬上寫完功課,晚上在盞小小燈泡底下繼續念書耶。」
此時三年級的美眉誇張地嘆了口氣,她抬頭用無辜的眼神望著二姨說:
「人家要喝水,要加冰塊。」
三公尺外另一張桌子旁的我,忽然有如被閃電擊中,什麼,我親愛的老婆小時候那麼用功?她究竟懂不懂「童年」的意思,或她根本在欺騙美眉、欺騙我、欺騙她自己?
我的童年呢?功課,嗯,想起來了,我的書包不見了。從學校回家(台北市吉林路的長安國小到林森北路的欣欣大眾百貨)這段路上,我得應付起碼五攤的聚會,先在學校操場想法子一大腳把足球踢到法國去,讓三年級的小鬼哭著喊,老師,他把我們的球踢不見了。再到校門口向掛在腳踏車後座的兩桶冰淇淋,流起碼兩公分長的口水。接著轉到新生北路和長安東路口(如今的建國高架橋底下),打半個小時的躲避球。眼見天色不對勁,才趕緊回家,不幸地,必然在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口前遇到大頭,兩人滾在地上幹一架,直到我啃他剃得發青的大頭,事情才在他的哭聲中結束。到家門口,先溜到隔壁沈伯伯家的後院,攀上牆偷瞧老媽回來沒,或她看起來心情怎麼樣,我再大搖大擺正式回家。
推開門我這麼說:
「媽,我回來了。」
別小看這幾個字,要講得理直氣壯,充滿朝氣與自信,如此老媽可能忘記要我的成績單,可能忘記先揍我再開飯的張家儀式,但這天她把我從頭到腳瞄了五百遍,才用我老婆對她外甥女的類似口吻說:
「你的書包呢?」
那個書包從此消失,沒有被我找回來,也沒有仁人君子撿到後送去警察局。為此,我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摸著剛被雞毛撢子刷了十下的紅腫屁股,我仍得出門去找書包,沈伯伯坐在他家門前乘涼看報,見到我就笑得剛鑲的金牙暴現於黃昏之中,閃射出刺眼光芒。
他笑著說,小傢伙,這回又闖什麼禍?
沒理他,我得在晚飯前設法找回書包,任由沈伯伯在我身後嘲笑。喔,我還聽到他自顧自在那裡跟唱平劇似的:
「童年,童年呀。」
那個書包代表我的童年,它的失蹤也跟童年一樣,從此一去不返,只有在心情最平靜的時候,才能偶而想起那個時代,它意味的是活力、自由、不知不覺掛上嘴角的微笑,與,最後的失落。
因為失落,我們經常將童年藏起來,除非最親近的人,否則絕不公開,這是為什麼在孩子眼中,父母一生下來就是大人,不知道他們也曾假裝感冒不上學,不知道他們甚至有個類似大頭、阿呆的綽號。
童年,是秘密。
看過比爾.布萊森作品的人大概都知道,無論歲月在身上增加多少脂肪、奪去他多少頭髮,他永遠都是個長不大的大孩子。他習慣性將吃苦當冒險(在旅程之中)、將歷史當成趣味的數據(在整理資料時),那麼這個人的成長過程想必很不堪回首?終於布萊森不怕他孩子甚至孫子的譏笑,公開了他童年秘密,寫在《閃電男孩的輝煌年代》裡。
二次大戰是人類最接近滅絕的時刻,幾千萬人死在戰場,猶太人與中國人慘遭大量的屠殺,不過在戰後,卻也是人類共通經驗最接近的時候,新的生活用品不停闖進我們的家庭,好奇之外,也使我們首次體會,原來無論處於地球哪個角落,人類正大步地朝彼此靠近。
於是當布萊森幻想自己是漫畫世界裡的閃電小子,以他得到的「威力聖戰袍」凝聚出「閃電能量」,消滅掉他討厭的傢伙時,我則披著從家裡扯下來的窗簾,跳躍於如今台北中山北路的老爺酒店屋頂上,手中的木劍朝天空一指,把萬惡的小學老師電擊成烤了三小時後的小木偶。喔,那時的老爺酒店是排二層樓的舊公寓,都有閣樓、都有天窗,而且還都是我同學家,所以他們的屋頂就成為一代英豪張阿呆行義仗義的地方。
當美國眾議員麥卡錫藉著反共招牌而推動白色恐怖時,小布萊森感受到這股無形壓力,卻擔心的是送報途中哈德曼家的那頭叫杜威的狗。他每天必須想法子躲開杜威,然後得到之後輕鬆的二十四小時,第二天早上再設法跑給杜威追。
那時遠在台北的張阿呆被調查局約談,那位叔叔這麼問:
「你怎麼有這張郵票?看得懂上面寫的字?」
我趕緊用有限的字彙,顫抖地念出:毛澤東是人民的紅太陽。
「你們看,」叔叔對著我老媽、我老師、我所有的親戚朋友和鄰居說,「共產黨都已經滲透到這個小朋友的腦殼裡了。張小朋友,告訴我,你們班上有幾個集郵呀?」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其實那時我很慚愧,不僅因為我把全班的名字都給了叔叔,腦海裡更出現電影中飛機轟炸城市的畫面、出現電視新聞裡美國試爆核彈的畫面、出現我媽邊哭邊拿著掃帚打我的畫面。啊,萬一哪天共產黨打台灣,竟然全是我的錯。白色恐怖那麼具體,它在同一時期出現在世界各地,像感冒、像小兒痲痺,像,電視機,也像電影裡男女主角,在幾個世紀人們的引頸期盼中,竟然真的親嘴了。
布萊森在十三歲時試圖於年度市集的表演帳蓬內,看看脫衣舞娘脫衣後的舞踏。不幸那年只准十四歲以上的人買票。他痴痴等候一年,當他滿十四歲時又去排隊買票,卻見售票處貼著告示,十六歲以上才能觀賞。
女人,對於那個時代的男孩,是另一種月亮,高高掛在那裡,始終無法仔細看清它的模樣。畢竟布萊森混了進去,使他對真實世界有了體認,一如我在許多年前,一直以為女人的某些部分是像簽字筆抹黑般醜陋,也一如若干年後,某些後進男生以為女人身上真的有馬賽克似的圖樣。男孩的成長過程,如此的相似,不論在太平洋的哪一岸。
照例,布萊森用他詼諧的筆法寫出他的童年,我必須說,當一切都帶著點朦朧、帶著點不確性,乃至於帶著點馬賽克,即使白色恐怖是幼稚,即使披風大俠與閃電小子是大人的夢魘,那仍是最美好的歲月。
這本書想傳達的並非寫實的童年紀錄,而是後現代的自由拼圖。把心胸打開,讓思想飛翔,如同小飛俠,我們都能飛起來。
同時,是的,我的那個書包,說不定它墜入時光隧道,等著我哪一天想通童年並未消失,只是躲在內心深處等著我的呼喚。然後我漂浮在黑洞中大聲叫喊,書包會碰地跳到眼前。沈伯伯的臉也出現,他依然帶著笑容說:
「童年,童年呀。」
張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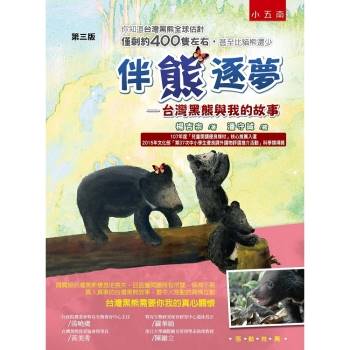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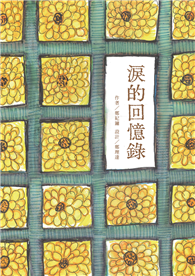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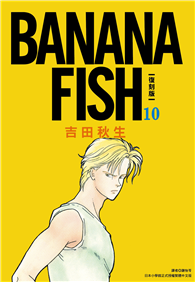
本書是比爾布萊森較新的作品,原文出版時間是2006年,繁中翻譯本一直到2011年才引進,對於比爾布萊森的書迷而言,距離上本繁中譯本的出版的2003年,可說是到了引頸期盼的地步,當然這幾年之間,台灣書商有翻譯了幾本作者比較另類的書,像布萊森之英語簡史、布萊森之英文超正典、萬物簡史(全四冊),但這些書的屬性比較不同,偏向科普與純英文文學應用(但也從這裡可以看出比爾創作的多元性)。 本書算是作者的自傳,只不過他寫的是自己還是兒童時的1950年代(比爾是1951年出生),用一個兒童與青少年的角度去陳述自己得生活成長點滴,並藉由他的兒時回憶去描述出那個五零年代的部份面貌。美國的五零年代(泛指二戰後到越戰爆發前大約1946-1965這段期間)對這個地球的人類而言,應該算是空前絕後的「史上最幸福的時空」,五零年代的美國年年都有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而且完全沒有一場戰爭發生在美國本土,不到十年的期間美國建立了未來幾十年全世界貧困人民夢想的生活方式,如家家有汽車,郊區有庭院的獨棟木屋、周日渡假、方便的購物中心、四通八達的馬路系統,廉價且方便的水電天然氣供應,大量電視電影娛樂,性解放,沒有通膨的物價、股價長期多頭…..那個時代的美國人稱得上是人類史上最幸福的一群,換句話說,1950年代的美國白人可以說連笨蛋腦殘者都可以過得比同期間甚至幾十年後的其他世界人們的生活。 比爾布萊森在本書所描述的就是這樣的美國,那是一個最美的時代,但是對我們台灣讀者而言,五零年代的美國一直是我們所陌生的,因為咱們開始接觸大量美國文化是在1970年代末期,那時候我們開始聽美國流行樂,看美國電影,到美國留學,頂多思想比較自由派的台灣年輕人會去接觸1967年以後反戰的東西,更別提現在更年輕的人;絕大多數人對於1950年代的美國是陌生的,或是被咱們台灣當年獨裁政府將1950年代的美國洗腦成冷戰反共的堅強中心,透過這本書可以清楚地瞭解那個人類史上最輝煌最快樂最幸福的1950年代的美國的整個時代的縮影。 其實我相當討厭傳記式文章,通常傳記文章多半充滿歌功\頌德甚至還會牽扯到一些神蹟之類的鬼扯蛋,除了自欺欺人騙騙無知讀者之外,絕大多數的傳記完全不值得一讀,因為多數的傳記的撰寫目的有兩種,一是作者請寫手寫一些讓他自己或他的家人員工追隨者自我感覺良好用的,二是勵志目的,這些傳記的撰寫一來不具有時空感,譬如許\多傳記一定要寫成從小刻苦耐勞立志向上,而完全不去提他的富裕家境(台灣的國民黨高官的傳記最喜歡來這一套),不然就是寫那些天生有缺陷而奮發向上的典範如汪洋中的一條船或居禮夫人之類的書。 不過這本比爾.布萊森不算偉大但也並非無名之人的傳記,我就相當欣賞,因為作者所提到的都是在當代相當尋常的生活且沒有讓人感到遙遠,另一方面作者願意把他童年所幹的狗皮倒灶和光怪陸離的怪事分享出來,譬如作者談到他童年時去愛荷華州的博覽會的唯一目的就是去看上空脫衣舞孃的露奶舞蹈,若換成咱們台灣那些道貌岸然的馬姓政要、李姓家同、洪*蘭等人寫的傳記的話,肯定又要寫他們從小就從事保釣等愛國行動,不然就是小就愛看「咆哮山莊」等名著,否則就是小時候就培養對四書五經的興趣才會讓他們在今天成為人人搖頭的老頑固等偉大事蹟。 比爾在本書「戶外遊樂場」一章中,寫出當年美國兒童對過時遊樂場的種種恐懼,如他寫到: 「每年夏季學校放假,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父馬把小孩送到市區北邊一個可怕的商業區內的一個小遊樂場河濱樂園,在你的口袋塞進兩塊錢,教你好好玩,八個小時後再來接你回家。河濱樂園是個令人聞之喪膽的地,它的雲霄飛車是有史以來最不牢靠最恐怖的建築,它的車廂裡外積滿三十五年來撒潑出去的爆米花和乘客劇烈嘔吐的穢物…車廂運行後過一陣子你就可以看到嘔吐物和陳年鳥糞的混合結晶體如雨般紛紛落下。」 「在河濱樂園的任何一個地方,特別是在你落單時,你一定會被一樣被放置在樂園中的更大塊頭的大小孩海扁一頓,並經常會搶走你的長褲、門票、鞋子,所以常常有孩子穿著鬆垮的內褲苦著臉在園內遊蕩,或站在雲霄飛車底下哭泣,無助地望著他的牛仔褲掛在離地四百呎高的木架上飄揚…」 「我知道有許\多孩子苦苦哀求他們的家長,不要把他們扔在河濱樂園,他們的一雙小手會緊抓著車門不放,這些大人必須拖著一雙腿從汽車走到遊樂園門口,所以會在地上留下一道六吋深的溝痕。他們把小孩丟在園區內….那種場面就像被活捉送進獅子籠一樣悲慘。」 其實比爾的文章雖然有誇大或帶點尖酸刻薄,但他往往能一針見血地寫出你我內心深處的真正聲音,和真實面貌,比爾敘述到他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後童年時期,他倒是很誠實地坦承他整天想的事情不外乎性愛、裸體女人、偷抽菸和偷喝酒等等正常行為,不像一般傳記中的少年那種假到作嘔的「見義勇為」或「醉心於書法練習」之類的怪胎行為。 然而,這本比爾布萊森的兒時自傳,對於太平洋彼岸的華人,的確讀起來會有相當文化背景的時空隔閡,他文中所鋪的一些「梗」如當年的卡通、零食或流行事物,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很難體會,就好比我若寫台北花博的「空心菜」傳奇這個梗,外國人或後代人應該很難體會吧!比爾寫的這本傳記並沒有把它寫成庸俗的「成長歷程」,也沒有刻意去刻畫「家庭親情大倫理」這種三流韓劇俗套,雖然五零年代的美國對我們而言很遙遠,但本書至少可以帶來讀者充沛的閱\讀樂趣,更方便的是,這本書無須如同啃讀磚頭小說般地從頭到尾一字不漏的閱\讀,隨便翻任一章篇便可津津有味地渡過捧腹的短暫書蟲片刻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