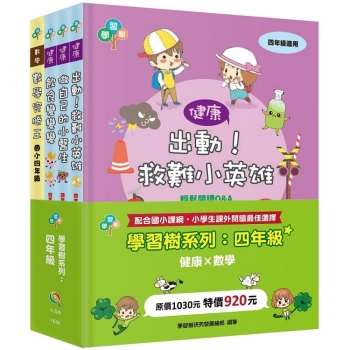我們快樂嗎?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或者我們,才會發現自己絕不會是最快樂的人。
亨利.米勒稱作家是「向內長的腳趾甲」。
艾瑞卡?張說:「我們坐在哪里鬱悶很多年,從肚臍眼裏挖東西,但只經歷了出版後的反高潮。」
這是寫作人命定的境遇嗎?「寫」是個漫長的期待,你的熱能、荷爾蒙在被預支,當結果到來時,只有疲憊和空虛。如果這是個反高潮,真正的高潮已在初初執筆的一刻出現過了?
也許有些誇大其詞,事實是,這正是寫作的特性,在真實的人生裏,我們學會輕描淡寫,輕描淡寫我們的情感,令人感到鬱悶的恰恰是這一點。
寫作作為生活方式,並非是最好的,「最好」是個引人走入歧路的詞。或者說,我沒有找到更適合於我的生活方式,我為此迷惘。同時,我沒有因為寫作而放棄什麼,就這一點,我是個平庸的寫作人,難道我想面面俱到嗎?好像又不是。我的日程表中寫作的時間很少,一星期有三個半天已經很順利了,那是在手頭有東西寫的時候,有時候,兩三個月都在「不寫」,然而,「想寫」的感覺卻跟著我。
對於我,有「寫作」的願望,比「寫作」更有意味,生存意義因為它而有所提高,這種說法好像很空泛。確切的感覺是,當我進入寫作狀態,便開始遠離現實,是的,我找到了遠離現實的方式。用卡爾維諾的說法:想開闢一個不同的空間,自然還有別的更充實、更個人的方法。寫作於我,是唾手可得,瞬間便能構築的另一個空間。
因之,寫作生涯很像持續著的青春期,假如說反叛故土渴望異鄉是青春期的特徵,伴隨著焦慮和不安寧的靈魂。
談到寫作,一定要提到其他寫作人對我的影響。
幾乎整整兩世紀的西方作家影響過我,不僅在寫作上,也是我成長歲月需要的蛋白質和維持生活素。我經歷過兩次瘋狂閱讀時代,先是文革後期的地下閱讀世界,我的中小學教育幾乎是在那個不再教授知識的時代結束,圖書館被封了,經典小說上了「毒草」黑名單,於是我們這代人便跟著「毒草」的指引,讀了許多經典書籍,想起來那些最精彩的書都是在陰暗角落,在常常是鬼鬼祟祟的狀態下獲得,而且多半是破破爛爛,經過無數次傳閱早已封面封底連同書名和作者名一起遺失,沒頭沒尾的小說,直到進大學,可以堂而皇之坐在圖書館閱讀,直到那時,,我才有機會把一本本名著被遺失的開頭和結尾補上,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經結束,高考剛剛恢復,我是高考恢復後的第二屆大學生,那是個令我今後人生常常要追懷的政治解凍時期,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湧入,我們在一片廢墟上反省和感悟,是可怕的信仰破碎過程,獲得的是精神解放而不僅是文學教育。這第二次的瘋狂閱讀已拋開十九世紀經典小說和老師開出的書單,是一次現代主義的洗禮。意識流荒誕派新小說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所有現代後現代流派不分先後一起湧入,真是一場現代文化的盛宴。
能夠列舉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寫作上給我影響的是法國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說《來去何匆匆》的?述方式,便是模仿蜜雪兒?布托爾的《變》。佛朗索娃?薩岡的《那樣一種微笑》、《你好,憂愁》、《你喜歡勃拉姆斯嗎?》令我對題材的微小產生信心。瑪格利特?杜拉的《琴聲如訴》,使我從此迷戀現代主義所呈現的破碎、廢墟的美感。
有評論家認為,我的作品與張愛玲的小說有某種共同的藝術特徵。事實上,我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機會讀到張愛玲的小說,可歎的是,當年文學史的缺損令我這個中文系畢業生對張愛玲毫無所知。我想說的是,張愛玲的深刻與尖銳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後才能感受,她的小說沒有詩情,沒有烏托邦,幾近於豪華的文字講述的卻是一個腐爛的人生,張愛玲的洞察力是對於後來作家的挑戰。如果說有什麼共同點,那麼這一個讓她在其中生活,愛,並且書寫的城市,也給我同樣的機會。只是我的上海和她的上海已相隔整整五十年。
在本集子中收入的四個中篇小說,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一個極其動盪充滿變化的時代,我所說的動盪和變化,是指整個大陸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改革時代,從極權時代進入消費時代,過往的價值觀正在粉碎,被禁錮的欲望獲得解放,但同時,黑匣子被打開了,我們的精神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以為快樂將隨著新生活一起到來,可為何抓獲的卻是一個個悲劇呢?我的小說講述的便是這樣一些故事。
有人認為我的小說肯定了某種物欲,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訴人們,你得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價。當然,欲望是人性,是社會前進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語文化制約,在直面它的時候,已經有了道德態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說僅僅為了「警世」,我希望能客觀地展現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他們經常需要選擇,為了一些在旁人看來是卑微的願望,他們舍此取彼,讓心靈飽受煎熬,這一刻的人才最富人性。也許,人性本來就是卑微的,和時代的大而化之比起來?也因此,讓我看到自己寫作的價值,刻畫人性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這也能稱為追求。我還想說,沒有選擇的人生是不人道的,這便是我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時對我筆下人物的肯定。
也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是悲觀的,可面對時代變遷我們的歡欣和嚮往還記憶猶新,為何我的故事卻是悲哀的?
我是在文革中成長,那個時代給我最厚重的陰影是,沒有個人,只有群體,人們生活在群體的謊言中,冠冕堂皇的理想後面,是殘暴的獸性的張揚,多麼可怕的「群體」!當社會更加物質化的時候,也更加人性化,消費時代是個人化的時代,表明了某種無所不在的個人選擇,是對群體化意識的消解。今天人們對於物質的巨大熱情,充滿了當年物質匱乏的恐懼,也是人性受壓之後的反彈,這種物欲的需求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我想展示的是,人們必然在沈溺中失卻自己,又在掙扎中找會自己。人的精神是在與自己的抗爭中變得強大。
然而,人的確又是渺小的,和時代的潮流相比,過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經濟潮流,你永遠無法選擇你嚮往的時代,你永遠有生不逢時的感覺,要說悲觀,這才是我的悲觀。
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