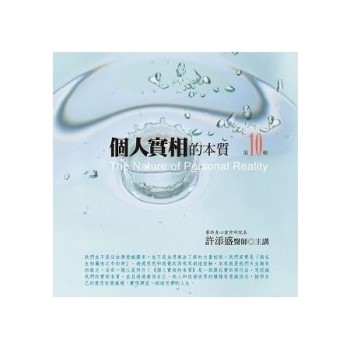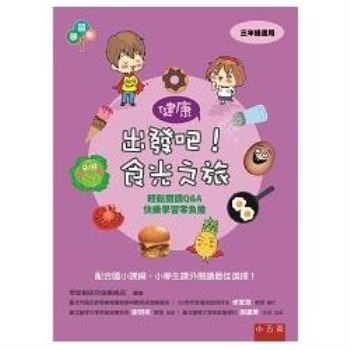一點秋心萬樹丹(代序)
其實是知道今天中秋節的。海外無節慶,忙了一個上午給學生上完課,腳步匆匆回到辦公室,秘書告訴我:有一位學生等候了你好久,今天是你的「辦公室談話時間」吧?我心裡打了個突:並沒有任何學生的事先約定呀。上得樓來,果然見一位個子高高的男學生笑咪咪守在我的門前,開口說:蘇老師,認得我吧?我是李逸斌。──李逸斌?我大吃一驚,這是我到耶魯後教過的第一撥學生,掐指算算,他畢業離校至少也有四、五年時間了。
趕緊讓進屋,他握著我的手,老師老師的叫得親切,第一句話,就幾乎要把我的淚水勾下來:老師,今天是中秋節,我帶了一小盒月餅,從紐約過來看看你。他果然從隨身的包裡掏出一盒月餅,輕輕放到我的桌子上。看著我手足無措、久久沒能從驚詫和感動中緩過神來的樣子,他連忙說:當然,不是專程來的,我的女朋友正在讀耶魯法學院,我常常回來看她。不過想到今天是中秋節,就特意過來看看老師。
幾年不見,這位華裔小夥子長高長壯了,還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跟我絮絮說著他在紐約投資銀行的工作,從前一個中文班的同學現在還常有聯繫,不時相約見面吃飯,常常還談到老師,那一年的中文課真有意思,非常感謝老師讓我們愛上了學中文……等等等等。窗外的樹葉剛剛開始泛紅,話語綿綿在耳際流過,我一時竟有點恍惚:覺得這像是一個錯置了地方的中秋故事──這裡,可是「酷」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國,這位喝洋風洋水長大的ABC孩子,何來這麼一番「月餅敬師」的溫情呢?便想起他當初在班裡其實不算一位頂拔尖的學生,但喜歡提問題,喜歡在課堂練習中用古怪字眼開同學的玩笑……。
我切開月餅,沏上茶,和他一起吃著談著,回憶著當初課上的種種趣事,各個同學畢業後的去向,誰誰因課結緣成了佳偶,誰誰從北京回來後現在又再回到中國去工作……「連我爸媽都不相信我能學好中文,現在公司要我管中國大陸方面的業務呢,真沒想到,中文變得這麼有用!」他大口大口啃著月餅(一副美國孩子啃漢堡的樣子),質樸的笑容裡帶點羞澀,「老師總告訴我們,要從中文裡看到一幅幅圖畫。我就記得你說過,中國文化裡重視『圓』──中秋月亮的圓,月餅的圓,和團圓的圓,都是同一個圓……」…………
一轉眼,秋深了。一整個秋天,這盒多少年來第一次在異國中秋節收到的月餅,始終在我眼前縈繞不去,便一直想把這個中秋故事寫下來,卻總覺得找不到合適的切入點。這幾天,新英格蘭秋天滿坑滿谷的金碧火紅,燒得人心頭抖顫。燃在樹頭的,飄在空中的,踩在腳下的,都是這樣彷彿從調色盤裡直接淌流下來的鮮麗顏色,便驀地想起晉人陸機的詩句:「及子春華,後爾秋暉」,心裡頭,好像一下子被點亮了──秋天,是一種老師的心情,也是一種父親的心情。學生來了,去了,聚了,散了;樹葉綠了,紅了,開花了,結實了,我們,也就漸漸步上人生的秋季了。栽樹人是重視春天而淡忘秋季的。
因為樹葉兒女離枝飄散的季節,其實是一個收穫的季節,也是一個互道珍重的季節。但是,秋收冬藏的日子,同時也是昭示來年的日子。那盒學生送我的中秋月餅,或者,既可以看作是綠葉對於樹根的致意,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生命在另一個生命裡的延續吧。每想到這一點,就對自己身擔的這份似乎普通平凡的工作,增加了幾分虔重、幾分尊敬。套用龔自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名句意蘊,我把自己隨口杜撰的句子寫在下面:天風海雨入斑斕,醉紫沉紅話重山。 幾分濃淡幾分墨,一點秋心萬樹丹。
蘇煒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於耶魯澄齋
推薦序 我的耶魯同事蘇煒 孫康宜
我一向非常佩服我的耶魯同事蘇煒,所以這一次能有機會推薦他在九歌出版的新書,心裡感到由衷的喜樂。在此我願意把我所認識的蘇煒介紹給臺灣的讀者。
首先,我佩服蘇煒,因為他不但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已出版過不少作品),同時也是一個少有的模範老師。我之所以稱他為「模範老師」,並非僅指他在教學上所付出的那種不尋常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他是以愛心來教育學生的。在〈一點秋心萬樹丹〉那篇自序裡,蘇煒把自己作為一個老師的心情比成「秋心」:
秋天,是一種老師的心情,也是一種父親的心情。學生來了,去了,聚了,散了;樹葉綠了,紅了,開花了,結實了,我們,也就漸漸步上人生的秋季了……樹葉兒女離枝飄散的季節,其實是一個收穫的季節,也是一個互道珍重的季節。但是,秋收冬藏的日子,同時也是昭示來年的日子……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生命在另一個生命裡的延續吧。
蘇煒對教學所持的這種「秋心」可以說是由種種師德凝聚成的一顆熱心,其中既有教學的耐心和責任心,也有他對與他交往的很多人都常有的關心和喜心,凡跟他選過課的學生,大多能感受到他們蘇老師這種愛教書,更愛交結學生的特殊情懷。許多耶魯學生告訴我,他們因為選了「蘇煒老師」的中文課而「愛上了中文」,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學業選擇和生命情調。就如蘇煒在這本書中那篇〈語言改變生命〉的文章裡所說,他的教學經驗「往往就是目擊一個學生怎樣進入一門陌生語言、又和這一門語言所附屬的文化歷史相抵牾、相適應、最後融化其中,然後被一種語言整個兒改造自己的文化個性以至生命軌跡的全過程。」
本書首輯「校園教趣」寫的就是蘇煒本人在耶魯教學的各種心得和樂趣。其中文章之生動、語言之富吸引力,令我想起美國作家彼得‧赫斯樂(Peter Hessler)於二○○一年出版的一本名著《河城》(River Town)。彼得‧赫斯樂在該書中描寫了他到四川教中國學生學習英文的種種經驗,書剛一出版就得到《紐約時報》和Time Literary Supplement等報的好評。著名作家哈金也極力讚賞該書,說彼得‧赫斯樂的書「坦白、熱情、極富洞察力」(suffused with candor,compassion,insights)。蘇書中「校園教趣」一輯,雖篇幅較短,我覺得也同樣寫得「坦白、熱情」和富有「洞察力」。更讓人感到鼓舞的是,蘇煒和彼得‧赫斯樂都同樣透過他們的語言教學改變了學生們的「生命」。我尤其欣賞蘇煒的這句話:「進入一個語言,就是進入另一條生命的河流。」此話正好是對彼得‧赫斯樂《河城》一書和蘇煒本人教學成果的最佳總結。
我欣賞蘇煒,還因為他擁有一顆詩人的赤子之心。這一點,我想讀者自可從本書的每篇文章中感受出來。例如,他「捧著一顆心」閱讀劉再復的《漂流手記》; 他被鄭振鐸冒著生命危險去保存民族典籍的熱情感動得「淚水溼潤了」眼眶;他為章詒和的回憶文章「動容落淚」;他被另一位耶魯同事康正果的自傳感動得「泫然欲淚」。蘇煒最喜歡晚清詩人龔自珍,特別欣賞他那「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詩境,但卻沒有龔自珍那種「空山徙倚倦遊身」的落寞之感。即使今天生活在海外,蘇煒仍對中國民族的前途滿腔關懷,也對在異域的土地上再造家園興趣盎然,所以他不只從未因過上了流亡生活而淒惶寂寞,甚至把他周圍流亡的一群組織在一起,給群體的活動增添了很多的樂趣。但同時,他又有他的憂患意識,對中國一百年來在許多方面的「原地踏步」狀況,他深感憂慮:
今天念及孫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叮嚀,真讓人汗顏赧愧:辛亥革命迄今將近一百年了!「反右」、「文革」,也已過去三、五十年了!我們仍在面對、仍無以釋解二十世紀初年或革命勝利初年,先賢先哲就已經提出的諸多課題。(〈亂世的「舊德」和「敗者」的骨格風采〉)
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蘇煒一貫持讚賞表彰的態度,所以他書中撰有專文,論述了臺灣才子沈君山堅持自由良知,分析了小說家張大春勇於呈現歷史真相,評介了龍應台的「三不主義」。蘇煒之所以特別尊敬這幾位具有獨立精神的臺灣知識分子,顯然是因為他們都有很強的「歷史感」──他們大多不屑於僅僅在黨派的恩怨是非上打筆仗,而有興趣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社會語境中作文章。可惜這樣的眼光,卻是現在很多報刊網絡上弄文的人所缺少的。在有關鄭振鐸的那篇文章裡(〈夜讀西諦〉),蘇煒曾這麼說道:「雖然中國歷史悠長,當代中國歷史、中國政治包括中國男人中最欠缺的,恰恰就是這個……歷史感。」
蘇煒本人顯然對這種「歷史感」頗有感悟,所以章詒和文章裡的「舊德」深深地打動了他善感的心:
在我們這些深受「五四」新文化與革命教育影響的一代人、幾代人眼裡,「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舊道德,從前是「棄之如敝屣」,今天也是視之如舊痕舊夢,實在何其隔膜久遠了。章詒和散文寫了六個父輩朋友(及其親屬)……我注意到,支撐這些「舊人物」在艱難歲月裡同舟共濟、相濡以沫活下去的,不是別的,恰恰正是那些被整個社會漠視、淡忘多時的「忠孝節義」的傳統風範與「舊行」「舊德」。
此外,蘇煒也非常支持新時代的女性主義。例如,他十分景仰曾在耶魯戲劇系求學的才女林徽因,他以對比的方式,突顯出林徽因的真實形象,「比同時代寫《致小讀者》時的冰心要剛健,比《莎菲女士》時代的丁玲要幹練,比寫《呼蘭河傳》時的蕭紅要柔韌,更比張愛玲、陸小曼、王映霞等民國名女人要顯得清爽新亮。」同時,他把林徽因稱為「現代中國追求女性獨立自由、充分展示女性才情光華的女性主義第一人」或「最前鋒人物」。這也從側面點染出耶魯大學在現代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發展及傳播上所占的重要地位。眾所周知,耶魯是美國各長春藤大學中第一個發起接收女生入學的學校。巧合的是,耶魯那個紀念女生成就的「女人桌」正好為林徽因的侄女林櫻(Maya Lin)──也是耶魯校友──所設計。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林徽因的家族代表了耶魯「女性主義」的傳統。
我為我的耶魯同事蘇煒感到驕傲,因為他每天都在努力深入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傳統。他甚至努力向他的耶魯學生們學習,他一邊耐心地修改他們那些可愛的病句──例如「我很病」,「我一定要見面她」,「我對他不同意」,「我要使平靜別人的痛苦」等病句──一邊被他們的精彩故事感動得「淚光瀅瀅」。他從他的美國學生身上讀到了西方人的單純、質樸和誠實。
對蘇煒來說,人生因此就充滿了無窮無盡的趣味了。盼望讀者們也能以欣賞這種趣味的心情來閱讀這本書。
二○○六年九月十日寫於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