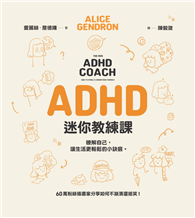文學民主的實踐
一九七八年三月,鄉土文學論戰方歇,小說家、中華日報副刊主編蔡文甫創辦了九歌出版社,成為出版界「五小」中的老么。
歷經時潮的衝激,「五小」中的老大純文學出版社已經停業,創辦人林海音也已歸道山;大地出版社讓出了經營權;爾雅和洪範,都還堅守文學崗位,努力經營著;而九歌出版社,依然意氣風發,準備在創社三十週年的二○○八年,以更豐碩、亮麗的成績,向世人展示九歌奮戰不懈的人文英姿。
《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即是九歌創社三十年的獻禮之一,分文類(詩、散文、小說、評論)精選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以後出生的台灣作家各三十位的作品,總計收入一二○位作家。
這裡所謂「台灣文學」,係指在台灣出生、生活的作家寫出來的文學,作家特指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者,有本籍台灣,亦有外省第二代及從海外來台求學、工作及生活者。「三十年」指九歌創社迄今(一九七八 ~ 二○○八);至於「菁英」,則是編輯委員的認定與選擇,凡此皆有必要略作說明。
十年前,為慶祝九歌創社二十年所編印的《台灣文學二十年集》亦分四卷,選二十年間各文類作家二十位的作品,那時並沒有用「菁英」字眼,「二十年集」是中性的,但事實上各卷只選二十位,選的當然是編輯群認為相對比較好的,這一次決定更明確表達編選意圖││選出編輯委員心目中的文學「菁英」。請先看我們在去年三月八日所議定的「編輯體例」:
一、《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以下簡稱「本集」)套書之編印,旨在慶祝九歌出版社創社三十週年,並反映在此期間(一九七八?二○○八)台灣文學之表現及其成就。
二、本集依文類分詩、散文、小說、評論四卷,書名分別為《新詩30家》、《散文30家》、《小說30家》、《評論30家》,除散文、小說分二冊外,餘皆為一冊;由各卷主編負責編選。
三、本集所選作家為戰後世代(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以後出生者),各卷作家以出生年為序,皆不重複;為與《台灣文學二十年集》(以下簡稱「前集」)略作區隔,後十年已停筆之作家未選入。
四、入選作品以發表於此三十年間者為限,不與前集重複,同時考量文學質地與讀者接受度。
五、本集前有總序,由召集人執筆;各卷皆有主編所撰序言;所選各家皆有作者小傳、 風格特色及照片。
看過《台灣文學二十年集》的人都會發現,這兩次編選的基本思維並沒什麼不同。人的部分挑選戰後出生者,入選作品則是在九歌成立以迄編選之際寫作或發表的。這其實是把九歌一家出版社和戰後台灣文學史聯結思考,但不是要編九歌文庫的選本,而是精選台灣文學作品。
實際的作法是,由九歌邀約四位對台灣文學發展有長期觀察的文學工作者,和九歌編輯部代表組成編輯委員會,在《台灣文學二十年集》的基礎上擬定《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的編例,由四編委分別負責詩、散文、小說、評論四文類,各自提出預選及備選作家名單,人數一定要超過三十,再開會詳細討論,決定入選名單。
主編可能會有他的堅持,但他必須說服其他的人。事實上當所有的名單經過彙整,我們彷彿也就看到了在時間的流動過程中,這一塊土地上的許多不同類型的寫作者,持續或間斷地寫作之身影。有共識的比較多,有少數需要共議共決;還有跨文類寫作現象,本諸「皆不重複」的原則,當然會有一些歸屬的討論,這時總盼能兼顧其寫作傾向及社會普遍的認定。
《台灣文學二十年集》計收入八十位作家,《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要收入一百二十位。我們一開始就沒主張前集所收要全數保留,一方面是編輯結構已略有調整,另一方面是經過十年的演變,主客觀條件皆有所增減,就像我們明寫在編例上的「後十年已停筆之作家不入選」。這個條例意味著「後十年」的表現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比對前後兩集的入選狀況,《新詩三十家》去三加十三,《散文三十家》去八加十八,《小說三十家》也是去八加十八,《評論三十家》去七加十七。總的來說,在前集的八十位作家有二十三位不見於後集,比率近三成,增加的是六十三位,這相當程度反映出一種典範更替現象,從歷史發展變化的角度來看,這也很正常,建議讀者合觀前後二集,基本上我們認為這些作家在此三十年間的表現都很有可觀。
前面提到跨文類寫作現象,也有必要進一步說明。《評論二十家》中的龔鵬程和王浩威,在《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中移到《散文三十家》,楊照則改列《小說三十家》。另外,原預選名單中,新詩類也列入蕭蕭和劉克襄,經討論,蕭蕭收入評論類,劉克襄改在散文類;評論類原也在預選名單中的李敏勇、簡政珍、龍應台,前二人編入新詩類,龍應台則進了散文類(也有極少部分作者無意願參與此項選集)。
在入選作家中,年紀最長的是小說類中出生於一九四五年的施叔青,最年輕的是新詩類中一九七八年出生的楊佳嫻。女性作家占有三成五,其中小說類男女各半,但新詩類女性只占六分之一;以出生年算,一九六五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有二十八位,比率二成三。大體合乎台灣文壇的基本分布狀況。
在最早的編輯會議中,關於入選作品,我們確定了如下的原則:「散文每家二篇,儘可能一長一短;詩維持四至五首,不選長詩;評論一人一篇,以大眾比較能夠接受為原則;小說也是一人一篇,可節選長篇」;但由於編選之事,必須尊重作家,尤其是我們決定請入選者提供若干作品以備選,在互動過程中可能會有變數,這個部分我們請各卷主編負責處理,九歌編輯部來協助。
如所周知,九歌在創社不久即編印年度散文選,近幾年且加入了年度小說選和童話選,可視為針對文學表現的反映及時進行經驗總結的作法,有助於典律生成,兩度大手筆編印《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規畫「新世紀散文家」、「名家名著選」、「典藏小說」、「典藏散文」,乃至於出版《新詩三百首》、《小說教室》、《散文教室》等,都可以看出九歌出版社面向台灣文學的歷史建構,特有參與的熱情與提供史料的用心。
從《台灣文學二十年集》到《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在「選文以定篇」的實踐過程中,出版者、編選者和作者共同參與了台灣文學歷史的書寫,然而在文學民主的時代精神下,我們咸信,另外任何一組編輯群,可能編出或多或少不同的選集,因此,我們期待得到讀者的批評及一切具建設性的討論。
二○○八年三月
家國與私密混聲
以近三十年來的小說表現,編選出具代表性的三十位戰後出生作家,這是一個蒐尋範圍極大的區域,設定為「三十」即表示必有遺珠,在編輯委員決議以「台灣文學二十年集」為藍本,考量「文學質地與讀者接受度」的基本方針下,對後十年仍持續創作的作者予以肯定,再加入這十年間寫作成績可觀,且近期仍有作品發表的作者,有了這些基本準則,名單逐一浮現。
選入的作家中,較資深者,大都經歷六○年代到八○年代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互為頡頏的時期,在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技法與內容上各有所長,並歷經轉變,確立個人風格或不斷的自我挑戰,持續創作事業。中生代作家在八○年代中期引領後現代思潮,影響台灣小說寫作策略,這本時間長達三十年的選集,除可見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發展脈絡,亦可看出中生代與新生代作家,受八○年代中興起的後現代思潮與後殖民思潮影響的痕跡。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開放的言論和資訊傳播的發達,促使社會朝向多元發展,後現代多元、跨國、解構、商品化、拼貼、懷疑、去中心的體質移植到小說,使小說家大炫美學技藝,顛覆寫實,去故事,拆解結構,在形式上或夾?夾議或多音合奏,或魔幻或拼貼,書寫者及文學媒體群起迎向西方理論潮流,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加以解嚴後政治情勢變化和島內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挑起後殖民文學的爭論,身分認同和台灣主體意識,形成小說的重要內容,至此後現代與後殖民交相糅合並置,使得近十幾年來的台灣小說,雖然在出版類型多元的書巿沒有得到熱烈的回響,實際上已到了百花爭妍,各自表態各自探索各自書寫的齊放狀態。
就議題特色而言,多元並陳,八○年代抬頭的女性意識書寫,到了九○年代已變身為女性情欲與政治權力的微妙角力,女性作者融入大論述書寫,爭取權力詮釋的發言權,大異於八○年代的情愛書寫;同志與酷兒書寫開啟性別跨界身分流動的書寫;都巿時尚與旅行書寫,去歷史中心放眼跨國文明;原住民小說作者紛紛出手,以小說為史,記錄族群歷史與文化歷程;馬華作家以離散書寫遙望出生之地;後殖民敏感的族群身分探尋、家族歷史採影,成為晚近另一股特殊的寫作潮流,為家族與國族的曖昧關係交相論述,無論是資深作者或中生代、新生代作者,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分別以家族為源頭,探溯作者的安身所在或國族詮釋。
為紛亂的台灣下註腳,是一股由身分認同延伸出來的對台灣命運的焦躁與探尋,一系列以百年台灣書寫為名的小說紛紛出爐,作者立意為台灣的定位尋找解釋或出路。
就書寫態度而言,資深作家大都身懷社會意識,能站在一個高度觀看社會發展,觀察社會問題,以文章為寄寓;年輕的作者,則以私密的角度抒發思懷,行文多一己生活周邊情事的切切私語。六○年代以後出生的作者,或是因為成長期間正值解嚴與社會多元發展,腦中還殘留舊體制的規約,E社會的無所禁忌又迎頭來擊,壯年時期逢政治意識形態分立、經濟衰頹,精神價值與現實生活都處在崩解的狀態,反映在小說中,顯露焦躁與憂鬱氣質,與前輩作家同樣追尋起身分與家族史時,表現手法與切入點就有極度的不同。幸而寫作是極為個人的,作家本應有所殊異才能各成特色,唯是因成長年代的時代氛圍不同,而彰顯出來的不同特質,也頗耐人尋味,是觀察一個世代文學發展可資研究參考的。
就寫作美學而言,從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延續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興起,寫作技藝與內容益形複雜,資深作家有回歸寫實創作者,也有大膽創作以實驗為尚者,甚而脫離小說模式,挑戰小說的書寫格局,試圖另尋表達途徑,在虛構與現實中疊合出心像圖影。近期大量興起的類私小說書寫,作者暴露個人生活,不論寫生活,寫感情,寫家族,寫死亡,都有將個人故事借小說顯影,散文跨界小說的現象。
小說作者若能拋棄已有的理論,不因循西方轉介的理論,另闢書寫形式與美學表現,無非是台灣小說凸顯自我特色之始,唯其寫作出版本身,即包含讀者的參與,作品能否成為社會資產,需要讀者的共鳴與認同。
在文學發展的大趨勢中,作家本有個別的殊異,即使六○年代以後出生的作者多喃喃私密之作,其中也不乏以客觀冷靜立場為大環境發聲者,五○年代出生的作者雖多家國之憂,也可見其焦躁憤怒的情緒借題發揮。因此在千禧年後,家國論述與去歷史轉而陳述私密內視情感的作品並行,或交揉成台灣現象顯影,或在紛亂的社會價值觀中透過書寫自我救贖,台灣作者面對的是越發複雜的社會,將會繳出什麼成績,值得期待與觀察。
選集裡的三十位作者各有書寫特色,有寫作多年持續不懈者,有跨文類表現皆優異者,有中斷寫作多年,近年又復筆,佳作不斷者,也有年輕的七○年代出生,寫作數年即已表現出強烈的個人特色者。「三十」當然不是絕對的名單,這裡未納入類型小說作者,也未納入已有數篇佳作,但近十年未有有力新作的作者,這份名單應是隨著作者的創作能量與時俱變的。
選入的作品,因尊重作者的意見,先由作者初薦數篇,編者選定其中一篇,未參與初薦的作者,則由編者選定,經作者同意。編選的作品包含數千字的短篇到超過十萬字的長篇,主要希望能全面注意到小說作者擅長的篇幅,真實呈現台灣小說作者的創作活力與特色。況且近十年來,短篇小說不局限於一萬字上下的篇幅,本選集因應書寫現象,以作品精采為主,不以字數設限。但選集的篇幅有限,中長篇小說採節錄的方式,即使是節錄,仍力求該節錄的片斷具有內容上的完整性,所以各篇選出的字數各有長短,為讓讀者了解該中長篇的整體輪廓,編者在簡介中分別對各作品略做陳述。
身為編者,在編選的過程中,常時與作者的群書為伍,務盼在簡介的部分力求精準,唯每位作者文多精采,著作眾多,字數有限的簡介畢竟難以盡述精華,編者未曾盡興,也請有興趣的讀者各取所需深入作者完整的著作,一方面可以糾正編者主觀的簡介產生的訛誤。
短短數月的編選過程,這些作者這些書佔據了我的牆角與心靈,即將完成編選的此刻,已無限眷戀擺書的窗邊角落,許多個早上,我在窗邊的陽光或雨聲中密集閱讀,游思在作者羅織的虛實之間。掩卷之際,竟是游思未歸。
二○○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