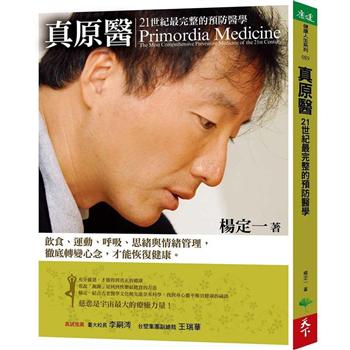沒有神的世界裡,人只能一輩子都在尋找,尋找一個人,和他說一句知心的話,一個人內心的洪流,其實已經足夠淹沒整個世界﹗──劉震雲
從《手機》的真話之難尋與說謊之必要,到《我叫劉躍進》人際間的偶然與必然,鬼馬作家劉震雲費時三年創作《一句頂一萬句》為生而為人,「覓知音」之必要。
賣豆腐的楊百順與工人牛愛國祖孫兩人不約而同地失去生命唯一能吐露心聲的知音後,傷心之餘下,一個出走,一個回歸,他們尋尋覓覓,與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試圖表達內心的矛盾與無助。從荒野的鄉村到繁忙的大都會,由20世紀中葉到新世紀初,不論是高高在上的縣長、鎮長,還是老師、理髮師、屠夫、染坊工、傳教士等尋常百姓,當說話成了唯一的溝通管道,語言又無法直達核心,孤獨便永遠如影隨形!
尋常人的事件,串連成不平凡的故事。中國大陸首刷四十萬冊,劉震雲說這是目前為止,他最滿意的作品。
獲獎記錄:
1、新浪網2009年上半年最佳圖書獎
2、2009年人民文學獎
3、《華商晨報》評為“2009年年度十大好書”
4、新浪網評為“2009年年度十大好書”
5、《京華時報》評為“2009年年度十大好書”
6、中央電視台“子午書簡”評為2009年年度最佳圖書
7、《光明日報》評為“2009年年度十大好書”
8、「楊曦淪品牌榜中榜」評為2009年年度好書
9、「長江出版集團」評為“2009年度最有影響好書”
10、被新浪網評為2009年年度作家
11、搜狐網評為“2009年年度十大好書”
12、獲《當代》長篇小說論壇2009年度五佳獎
13、獲《當代》長篇小說論壇2009年度最佳獎
作者簡介:
劉震雲,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於河南省延津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7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塔舖》,引起文壇注目,主要作品:《手機》、《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一腔廢話》、《一地雞毛》等。共四百多萬字。作品多次獲文學獎、被評介、改編和翻譯;《一地雞毛》改編成電視劇,被視為經典劇集;《手機》改拍為電影,獲全年賣座第一的紀錄,在台灣出版,並獲出版人小說家隱地等大力讚許。知名作家王朔稱劉震雲是唯一能對他構成威脅的人。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10-01-10 華文獎項 >> 湖北“2009年度最有影響10本書” >> 《一句頂一萬句》獲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攜17種經過出版社推薦、專家初評、網上投票選出的精品圖書來到北京,邀請在京主流媒體,在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進行終評,以投票方式選出了“2009年度最有影響10本書”。
2010-01-05 華文獎項 >> 新浪中國2009年度好書 >> 新浪文化讀書頻道發布了2009年度“新浪中國好書”,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等當選新浪中國好書榜十大好書。
名人推薦:
推薦序:劉震雲猜想/傅月庵
之 一
劉震雲的家鄉,離海幾萬里,幾代人沒見過海的。他卻忍不住就想衝浪。衝浪有技巧,你不能在浪後,那樣衝不起來,也不能離浪頭太近,那樣一下就被浪給打趴了。你得維持在浪前幾公尺,讓浪推著你跑,這樣才能乘風,才好破浪。劉震雲不是一開始就衝海浪的。他先在河裡玩,玩兒風浪板,玩《一地雞毛》,大家都說他有潛力,會使風;然後看到了海口,又玩,玩兒《溫故一九四二》,大家說,危險哪,快回頭;他不聽,還玩, 還開始脫衣服,朝大海直衝過去。他玩兒《故鄉麵和花朵》,玩得騰空翻了個滾,大家看不懂,嚇壞了,認定這傻小子肯定要遭滅頂。但他咕嚕咕嚕吐了幾口水,還繼續玩,且拉出一票朋友一起玩,玩兒《手機》、玩兒《我叫劉躍進》,玩得幾層樓高的浪頭直在背後追著他跑,海邊圍觀者如堵,大家都說這小子有種,特行!誰知一個大轉身,他蹲下身來,擺了個向下縱躍的跳水姿勢,口裡念念有詞。大家急忙用望遠鏡看,從嘴型猜想,似乎是:「咱再玩些別的?」「玩些別的就玩些別的。」—他潛水了,想看看能掀起這麼高浪頭的海底的那個到底是什麼?於是有了《一句頂一萬句》。
之 二
《一地雞毛》從一塊餿掉的豆腐談起,談來談去,總不外乎尋求解決生活資源的問題。此時的劉震雲,不折不扣,就是個「唯物論」者;到了《故鄉麵和花朵》,儘管背景、人物、地點都大不同,劉震雲主要觀照的,仍是物質,但他也發現,一天二十四小時,鄉人不停在覓食,手在動,腦筋也在動,且是不得不快速地動著,上天下地胡思亂想,以便平衡覓食求生的煎熬與痛苦。劉震雲想理解鄉人都在胡思亂想些什麼?於是從物質走向精神,從胃部走入頭部;《手機》和《我叫劉躍進》,表面講的還是生活與生存, 底下卻搞起思維邏輯了。劉震雲想知道手機怎樣讓人心口不一,讓人得講一大堆錯假廢話,來扭曲遮蔽真實,好求生存找活命。他也想知道,劉躍進的腦袋到底該怎麼想如何轉才能絕處逢生、死裡逃生?「胡思亂想」與「胡說八道」之間到底存在何種辯證關係?劉震雲一直不停地在想著。到了《一句頂一萬句》,他終於認定:知心者,一句頂一萬句; 講不上話的,一萬句頂不上一句。這事且是超越種族黨派性別階級財富宗教,可以跨時空超宇宙的。劉震雲這下子成了「唯心論」者。寫了二十多年,終於從河面寫到海底,從生活、生存寫到生命,大致釐清了唯物與唯心的纏夾關係。長夜漫漫路迢迢,這一路走來可真是不容易。無怪乎劉震雲要說:「這是我寫作以來,寫得最好的一部書。是我自個兒願意送人的一本書。」
之 三
「一句頂一萬句」最早出自林彪口中,捧毛澤東思想用的。這一句他前前後後恐怕也喊過一萬次了吧。但可惜不是知心的那一句,跟毛澤東還是講不上話。於是兩人都孤單, 都得繼續在茫茫大海裡航行,都盼著找到可依靠的舵手的那一句。「一個人的孤獨不叫孤獨,一個人尋找另一個人,一句話尋找另一句話才叫孤獨。」劉震雲這樣說。於是,毛澤東孤獨,林彪也孤獨。毛澤東知道親密戰友不知心,那一句也不是他要的那一句,所以林彪跑了,他也不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知心者,一句頂一萬句; 講不上話的,一萬句也頂不上一句。
之 四
《一句頂一萬句》,說複雜很複雜,跨越二三個世代,整個西北高原東奔西跑了個遍,想不複雜都不行。說簡單,也很簡單,上下好幾代,代代都想找到那個可以跟自己對上話,讓自己不要那麼孤獨的那個人,卻偏偏就是對不上。男的對不上,女的也對不上。一切都是那麼擰巴(彆扭),擰巴得讓人不得不把悲劇當喜劇看,以便再有存活下去的氣力。只是,講不上話,也未必是話講的不好,更多時候,是不會聽不想聽聽不懂。發射器沒問題,是接受器出了狀況。我們這個民族,從來都是重口不重耳,會講比會聽值錢。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那是高明。就算閉嘴不說,沒話了,也還叫沉默是金。聽話就沒這麼值錢了,「聽到了」跟「聽懂了」一個價,只聽不說,那叫一肚子壞水,滿腹陰謀。說到底,沒個會聽的,講一萬句也是白講。於是自古至今,大家都在漫天打鳥,都在大聲吶喊覓知音,於是連魯迅翁都要慨嘆賭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殊不知這誓條的先後弄擰了,該是「斯世願以同懷聽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才對哪。
之 五
都說這書有明清味道,誠然如是。但恐不是野稗日記言語簡潔,敘事直接這些表象原因。更多的成分,當來自「家常」兩個字。這也是劉震雲小說特具的風格。不管寫城市寫鄉村寫北京寫延津,寫前代寫今世寫一九四二或二○○二,他總是在「家常」裡取景寫境。寫的不外乎老張老李小林小劉賣豆腐的剃頭的吆喝包子跑貨卡的教書當顧問工地廚子電視主持人理容院老闆娘……的外在與內在世界。通過這個世界,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觀看的方法與連結的方式。按照革命的說法,劉震雲始終站穩階級立場,不曾一日或忘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這個無產,既是物質也是精神的)。按照文學的理解,則是「家常」風格,讓劉震雲與明清說部接上了軌,尤其是「三言二拍」這一尋常百姓悲歡離合路數。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的是嘛?以為找到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人了,誰知不是,傷心之餘,就跳水啦。賣油郎憑什麼獨占花魁?也不過就是「知心」二字。再看看「倒運漢巧遇洞庭紅」、「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這世道多擰巴,擰巴得悲劇喜劇都難分啦。再往上提到極致吧,《牡丹亭》題詞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講得夠玄妙了,說穿了,卻也不過就是「一句頂一萬句」在那作用著而已。
之 六
「咱再說些別的?」「說些別的就說些別的。」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劉震雲是也!
. 本文作者傅月庵先生,曾任出版社編輯、總編輯。現任二手書店執行總監。著有《生涯一蠹魚》、《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天上大風》。寫作以書評,書話文章見長,散見兩岸三地報紙期刊。因其文筆多致,又不失其幽默風趣,深受讀者矚目。
得獎紀錄:2010-01-10 華文獎項 >> 湖北“2009年度最有影響10本書” >> 《一句頂一萬句》獲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攜17種經過出版社推薦、專家初評、網上投票選出的精品圖書來到北京,邀請在京主流媒體,在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進行終評,以投票方式選出了“2009年度最有影響10本書”。
2010-01-05 華文獎項 >> 新浪中國2009年度好書 >> 新浪文化讀書頻道發布了2009年度“新浪中國好書”,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等當選新浪中國好書榜十大好書。
名人推薦:推薦序:劉震雲猜想/傅月庵
之 一
劉震雲的家鄉,離海幾萬里,幾代人沒見過...
章節試閱
楊百順他爹是個賣豆腐的。別人叫他賣豆腐的老楊。老楊除了賣豆腐,入夏還賣涼粉。賣豆腐的老楊和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是好朋友。兩人本不該成為朋友,因老馬常常欺負老楊。欺負老楊並不是打過老楊或罵過老楊,或在錢財上占過老楊的便宜,而是從心底看不起老楊。看不起一個人可以不與他來往,但老馬說起笑話,又離不開老楊。老楊對人說起朋友,第一個說起的是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老馬背後說起朋友,一次也沒提到過楊家莊賣豆腐也賣涼粉的老楊。但外人並不知其中的底細, 大家都以為他倆是好朋友。
楊百順十一歲那年,鎮上鐵匠老李給他娘祝壽。老李的鐵匠鋪叫「帶旺鐵匠鋪」,打製些飯勺、菜刀、斧頭、鋤頭、鐮刀、耙齒、鏟頭、門搭等。鐵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卻是慢性子;一根耙釘,也得打上兩個時辰。但慢工出細活,這根耙釘,就打得有稜有角。飯勺、菜刀、斧頭、鋤頭、鐮刀、鏟頭、門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帶旺」二字。方圓幾十里,再不出鐵匠。不是比不過老李的手藝,是耽誤不起工夫。但慢性子容易心細,心細的人容易記仇。老李是生意人,鋪子裡天天人來人往,保不齊哪句話就得罪了他。但老李不記外人的仇,單記他娘的仇。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壓的。老李八歲那年,偷吃過一塊棗糕,他娘揚起一把鐵勺,砸在他腦袋上,一個血窟窿,汩汩往外冒血。別人好了傷疤忘了疼,老李從八歲起,就記上了娘的仇。記仇不是記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過血窟窿後,仍有說有笑,隨人去縣城聽戲去了。也不是記聽戲的仇,而是老李長大之後,一個是慢性子,一個是急性子,對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樣。老李他娘是個爛眼圈, 老李四十歲那年,他爹死了;四十五歲那年,他娘瞎了。他娘瞎了以後,老李成了「帶旺鐵匠鋪」的掌櫃。老李成為掌櫃後,倒沒對他娘怎麼樣,吃上穿上,跟沒瞎時一樣,就是他娘說話,老李不理她。一個打鐵的人家,平日吃飯也是淡飯粗茶,他娘瞎著眼喊:
「嘴裡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讓我嚼嚼。」
老李:
「等著吧。」
一等就沒了下文。他娘:
「心裡悶得慌,快去牽驢,讓我去縣城聽個熱鬧。」
老李:
「等著吧。」
一等又沒了下文。不是故意跟他娘治氣,而是為了熬熬她這急性子。日子在他娘手裡,已經急了半輩子,該慢下來了。也怕開了這種頭,亂越添越多。但他娘七十歲這年,老李卻要給他娘做壽。他娘:
「快死的人了,壽就別做了,平時對我好點兒就行了。」
又用拐棍搗著地: 「是給我做壽嗎?不定憋著啥壞呢。」
老李:
「娘,您多想了。」
但老李給他娘做壽,確實不是為了他娘。上個月,從安徽來了個鐵匠,姓段,在鎮上落下腳,也開了個鐵匠鋪;老段是個胖子,鐵匠鋪便叫「段胖子鐵匠鋪」。如老段性子急,老李不怕;誰知段胖子也是個慢性子,一根耙釘,也打上兩個時辰,老李就著了慌,想借給他娘做壽,擺個場面讓老段看看。借人的陣勢,讓老段明白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但眾人並不明白祝壽的底細,過去都知道老李對娘不孝順,現在突然孝順了,認為他明白過來理兒了,祝壽那天中午,皆隨禮去吃酒席。老楊和老馬皆與鐵匠老李是朋友,這天也來隨禮。老楊早起賣豆腐走得遠,吃酒席遲到了幾步;馬家莊離鎮上近,老馬準時到了。老李覺得賣豆腐的老楊和趕大車的老馬是好朋友,便把老楊的座位,空在了老馬身邊。老李以為自己考慮得很周全,沒想到老馬急了:
「別,快把他換到別的地方去。」
老李:
「你們倆在一起愛說笑話,顯得熱鬧。」
老馬問:
「今天喝酒不?」
老李:
「一個桌上三瓶,不上散酒。」老馬:「還是呀,不喝酒和他說個笑話行,可他一喝多,就拉著我掏心窩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窩心了。」
又說:
「不是一回兩回了。」
老李這才知道,他們這朋友並不過心。或者說,老楊跟老馬過心,老馬跟老楊不過心。遂將老楊的座位,調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邊。楊百順前一天被爹打發過來幫老李家挑水,這話被楊百順聽到了。吃酒第二天,賣豆腐的老楊在家裡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禮白送了;不痛快不是說酒席不豐盛,而是在酒桌上,跟牲口牙子老杜說不來。老杜又是個禿子,頭上有味,肩上落了一層白皮。老楊認為自己去得晚,偶然挨著了老杜。楊百順便把昨天聽到的一席話,告訴了老楊。賣豆腐的老楊聽後,先是兜頭搧了楊百順一巴掌:
「老馬絕不是這意思。好話讓你說成了壞話!」
在楊百順的哭聲中,又抱著頭蹲在豆腐房門口,半天沒有說話。之後半個月沒理老馬。在家裡, 再不提「老馬」二字。但半個月後,又與老馬恢復了來往,還與老馬說笑話,遇事還找老馬商量。
賣東西講究個吆喝。但老楊賣豆腐時,卻不喜吆喝。吆喝分粗吆喝和細吆喝。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說豆腐,「賣豆腐嘍」「楊家莊的豆腐來了」細吆喝就是連說帶唱,把自己的豆腐說得天花亂墜:「你說這豆腐,它是不是豆腐?它是豆腐,可不能當豆腐…… 」那當啥呢?直把豆腐說成白玉和瑪瑙。老楊嘴笨,溜不成曲兒,又不甘心粗吆喝;也粗吆喝過,但成了生氣:「剛出鍋的豆腐,沒這個那個啊—」可老楊會打鼓,鼓槌敲著鼓面,磕著鼓邊,能敲打出諸多花樣;於是另闢蹊徑,賣豆腐時,乾脆不吆喝了,轉成打鼓。打鼓賣豆腐,一下倒顯得新鮮。村中一聞鼓聲,便知道楊家莊賣豆腐的老楊來了。除了在村裡賣豆腐,鎮上逢集,也到鎮上擺攤。既賣豆腐,又賣涼粉。用刮篾將涼粉刮成絲,擺到碗裡,擱上蔥絲、荊芥和芝麻醬;賣一碗,刮一碗。老楊攤子左邊,是賣驢肉火燒的孔家莊的老孔;老楊攤子右邊,是賣胡辣湯也捎帶賣煙絲的竇家莊的老竇。老楊賣豆腐和涼粉在村裡打鼓,在集上也打鼓。老楊的攤子上,從早到晚,鼓聲不斷。一開始大家覺得新鮮,一個月後,左右的老孔和老竇終於聽煩了。老孔:
「一會兒『咚咚咚』,一會兒『哢哢哢』,老楊,我腦漿都讓你敲成涼粉了,做一個小買賣,又不是掛帥出征,用得著這麼大動靜嗎?」
老竇性急,不愛說話,黑著臉上去,一腳將老楊的鼓踹破了。
四十年後,老楊中風了,癱瘓在床,家裡的掌櫃換成了大兒子楊百業。別人一中風腦子便不好使,嘴也不聽使喚,「嗚哩哇啦」說不成句,老楊卻身癱腦不癱,嘴也不癱。不癱的時候嘴笨,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或把兩件事說成一件事;癱了之後頭腦倒清楚了,嘴也順溜了,事碰事理得紋絲不亂。身子癱後,整日躺在床上,動一動就有求於人,這時就比不得從前,眼上、嘴上就得吃些虧;進屋一個人,眼裡就趕緊逢迎和討好;接著人問他啥,他就說啥;不癱時常說假話,癱了之後句句都掏心窩子。喝水多了,夜裡起床就多,老楊從下午起就不喝水。四十年過去,老楊過去的朋友要麼死了,要麼各有其事,老楊癱了之後,無人來看他。這年八月十五,當年在集上賣蔥的老段, 提著兩封點心來看老楊。多日不見故人,老楊拉著老段的手哭了。見家人進來,又忙用袖子去拭淚。老段:
「當年在集上做買賣的老人兒,從東頭到西頭,你還數得過來不?」
老楊雖然腦子還好使,但四十年過去,當年一起做事的朋友,一多半已經忘記了。從東到西,扳著指頭查到第五個人,就查不下去了。但他記得賣驢肉火燒的老孔和賣胡辣湯兼賣煙絲的老竇,便隔過許多人說老孔和老竇:
「老孔說話聲兒細;老竇是個急性子,當年一腳把我的鼓給踹破了。我也沒輸給他,回頭一腳, 把他的攤子也踢了,胡辣湯流了一地。」
老段:
「董家莊劁牲口的老董,你還記得吧?除了劁牲口,還給人補鍋。」
老楊皺著眉想了想,想不起這個既劁牲口又給人補鍋的老董。老段:
「那魏家莊的老魏呢?集上最西頭,賣生薑的那個,愛偷笑,一會兒自己樂了,一會兒自己樂了,也不知他想起個啥。」
老楊也想不起這個一邊賣薑一邊偷笑的老魏。老段:
「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你總記得吧?」
老楊鬆了一口氣:
「他我當然記得,死了兩年多了。」
老段笑了:
「當年你心裡只有老馬,凡人不理。豈不知你拿人家當朋友,人家背後老糟改你。」老楊趕緊岔話題:
「多少年的事了,你倒記得。」
老段:
「我不是說這事,是說這理。不拿你當朋友的,你趕著巴結了一輩子;拿你當朋友的,你倒不往心裡去。當時集上的人都煩你敲鼓,就我一個人喜歡聽。為聽這鼓,多買過你多少碗涼粉。有時想跟你多說一句話,你倒對我愛搭不理。」
老楊忙說:
「沒有哇。」
老段拍拍手:
「看看,現在還不拿我當朋友。我今天來,就是想問你一句話。」
老楊:
「啥話?」
老段:
「經心活了一輩子,活出個朋友嗎?」
又說:
「過去沒想明白,如今躺在床上,想明白了吧?」
老楊這才明白,四十年後,老段看自己癱瘓在床,他腿腳還靈便,報仇來了。老楊啐了老段一口:
「老段,當初我沒看錯你,你不是個東西。」
老段笑著走了。老段走後,老楊還在床上罵老段,老楊的大兒子楊百業進來了。楊百業是楊百順的大哥,這時也五十多歲。楊百業小的時候腦子笨,常挨老楊的打;四十多年過去,老楊癱瘓在床, 楊百業成了家裡的掌櫃,老楊舉手動腳,就要看楊百業的臉色行事。楊百業接著老段的話茬兒問:
「老馬是個趕大車的,你是個賣豆腐的,你們井水不犯河水,當年人家不拿你當人,你為啥非巴結他做朋友?有啥說法不?」
身癱的老楊對老段敢生氣,對楊百業不敢生氣。楊百業問他什麼,他得說什麼。老楊停下罵老段,歎了一口氣:
「有,不然我也不會怵他。」
楊百業:
「事兒上占過他便宜,或是有短處在他手裡,一下被他拿住了?」
老楊:
「事兒上占便宜拿不住人,有短處也拿不住人,下回不與他來往就是了。記得頭一回和他見面, 就被他說住了。」
楊百業:
「啥事?」
老楊:
「頭一回遇到他,是在牲口集上,老馬去買馬,我去賣驢,大家在一起閒扯淡。論起事來,同樣一件事,我只能看一里,他能看十里,我只能看一個月,他一下能看十年;最後驢沒賣成,話上被老
馬拿住了。」
又搖頭:
「事不拿人話拿人呀。」
又說:
「以後遇到事,就想找他商量。」
楊百業:
「聽明白了,還是想占人便宜,遇事自個兒拿不定主意,想借人一雙眼。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他看不上你,為啥還跟你來往呢?」
老楊:
「可方圓百里,哪兒還有一下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呢?老馬也是一輩子沒朋友。」
又感歎:
「老馬一輩子不該趕馬車。」
楊百業:
「那他該幹啥呢?」
老楊:
「看相的瞎老賈,給他看過相,說他該當殺人放火的陳勝吳廣。但他又沒這膽,天一黑不敢出門。其實他一輩子馬車也沒趕好,趕馬車不敢走夜路,耽誤多少事兒呀!」
說著說著急了:
「一個膽小如鼠的人,還看不上我,我他媽還看不上他呢!一輩子不拿我當朋友,我還不拿他當朋友呢!」
楊百業點點頭,知道他倆一輩子該成為朋友。說罷老馬,到了吃中飯時候。這天是八月十五,中飯吃的是烙餅,肉菜亂燉。烙餅是老楊一輩子最愛吃的,但六十歲以後,牙爛掉了一大半,嚼不動了;但配上亂燉,肉和菜在火上燉的時間長,肉是爛的,菜也是爛的,菜湯是滾燙的,將烙餅泡到菜裡,能泡得入口就化。老楊年輕的時候,一過節就吃烙餅;但他癱瘓在床之後,家裡吃不吃烙餅,不由他說了算。本來在問老馬之前,楊百業就決定中飯吃烙餅和肉菜亂燉,但當年賣豆腐也賣涼粉的老楊卻認為自己剛才說了實話,楊百業才讓烙餅,這飯是對他的獎賞。一頓飯吃下來,老楊吃得滿頭大汗。肉菜亂燉的熱氣中,又仰臉向楊百業討好地笑了笑,意思是:
「下回問我啥,我還說實話。」
楊百順十六歲之前,覺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頭的老裴。但自打認識老裴,兩人沒說過幾句話。楊百順十六歲的時候,老裴已經三十多了。老裴家住裴家莊,楊百順家住楊家莊,之間相距三十里, 中間還隔著一條黃河,一年也碰不上幾面。楊百順沒去過裴家莊,老裴來楊家莊剃過頭。但楊百順七十歲以後,還常常想起老裴。
老裴剃頭的手藝並不是祖傳。他爺是個織席的,捎帶賣鞋。他爹是個販毛驢的,一年四季,背著褡褳、拿根鞭子到口外內蒙古販毛驢。從河南延津到內蒙古,去時得走一個月;從內蒙古趕著毛驢回來,緊走慢走,得一個半月。一年下來,也就做四五趟生意。老裴成人之後,一開始跟他爹學販驢。兩年之後,老裴他爹得傷寒死了,老裴就開始一個人上路,和別的驢販子搭伴,一趟趟去內蒙古販毛驢。老裴年齡雖小,但長著個大人心,一年下來,不比他爹在時賺錢少。十八歲那年,娶妻生子,也不在話下。販毛驢常年在外,一年有八九個月不在家,免不了在外邊有相好。別的驢販子在外也有相好,或在山西,或在陝北,或在內蒙古,看走到哪裡碰上了。但相好也就是相好,認不得真,別人給相好留的是假名假姓,老家在哪裡,也不說實話。老裴當時還是年輕,在內蒙古靠上個相好叫斯琴格勒,頭一回在一起,斯琴格勒問他姓名,家住哪裡,老裴一時忘情,就說了實話。斯琴格勒是個有丈夫的人,丈夫出外放牧,她在家裡靠相好。一是圖個痛快,二是圖相好留下仨瓜倆棗的散碎銀兩,她好存個體己。但她靠的不是一個人,另有一個相好是河北人,也去內蒙古販驢,但人家留的就是假名假姓,縣份也是假的。這年秋天,斯琴格勒和河北相好的事發了。斯琴格勒的丈夫出門放牧三個月, 回來卻發現她懷孕了。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整天吃牛羊肉,熱性大,不在乎夜裡那點兒事;但懷孕了她丈夫就急了。因這孩子生下來,等於替別人養著。所以靠相好的人,都知道圖痛快歸圖痛快, 但痛快也分個時辰;時辰不對,痛快的最後一刻要忍住,不能讓懷孕。和河北人這次,斯琴格勒也是一時忘了情,雖然時辰不對,也讓河北人徹底痛快了。河北人痛快了,斯琴格勒的丈夫生了氣,覺得這是相好欺負自己,用皮鞭抽斯琴格勒,斯琴格勒不但供出了河北的相好,也供出了河南的老裴。蒙族人扔下自己的老婆,掂著一把宰牛刀上了路。先去河北,沒找著真人,又來到河南延津縣裴家莊, 找著了老裴,上去就要拚命。後經人說和,賠了這蒙族人三十塊大洋,又貼了來往路費,才把他打發走。蒙族人走了,事情卻沒有完。老裴的老婆叫老蔡,三天上了三回吊。雖然每回都把她救了回來, 但三天之後的老蔡,和三天前成了兩個人。過去老蔡怕老裴,現在老裴怕老蔡。老蔡說:
「你說這事兒咋辦吧?」
老裴:
「從今往後,一切聽你的。」
老蔡:
「從今往後,別理你姊。」
由靠相好轉到他姊頭上,老裴有些蒙。老裴從小娘死得早,從六歲起,由他姊帶大。老裴與他姊感情深,老蔡卻與他姊鬧過彆扭。老裴想明白這理兒,低著頭說:
「反正她已經出嫁了,從今往後,不理她就是了。」
老蔡又問:
「從今往後,你還去內蒙古不?」
老裴:
「去不去,還聽你的。」
老蔡:
「從今往後,別再提『販驢』二字。」
老裴只好放下褡褳和鞭子,不再販驢。老裴這才知道,那個內蒙古人不遠千里來河南找他,並不是為了拚命,也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讓他一輩子不得安生;這個內蒙古人人粗心不粗,下手有些毒。但斯琴格勒懷孕,並不是老裴的責任,老裴還得替河北人背著黑鍋,冤還冤在這裡。毛驢販不成了,老裴便開始跟馮家莊的老馮學剃頭。剃頭倒不難學,學剃頭三年出師,老裴兩年半就離開老馮, 自己擔著剃頭挑子,十里八鄉給人剃頭。這一剃就是七八年。只是自此不愛說話。師傅老馮給人剃頭時,愛跟人聊天;十里八鄉的事,數老馮知道得多。老裴給人剃頭,一個頭剃下來,一句話沒有。大家都說師傅徒弟不一樣。老裴話少不說,頭剃著剃著,還愛長吁一口氣。一個頭剃下來,要吁四五口長氣。一次老裴到孟家莊東家老孟家剃頭。老孟家有五十頃地,二十多個夥計。二十多個夥計的頭剃完,老孟的頭剃完,太陽就要落山了。老孟有一個朋友叫老褚,是豫西洛寧縣一個鹽商,這天從山東販鹽回來,路過延津縣,順便到孟家莊來看老孟;老褚的頭髮正好長了,也讓老裴來剃。老裴剃幾刀子,長吁一口氣;剃幾刀子,又吁出幾口氣。頭剃到一半,老褚急了,光著半邊頭跳起來,指著老
裴:
「操你媽,多剃一個頭,咋知道我不給你錢?唉聲歎氣的,撲身上多少晦氣。」
老裴提著刀子站在那裡,臉紅耳赤,說不出話,最後還是東家老孟替他解了圍,對老褚說:
「兄弟,他那不是歎氣,是長出氣;不是剃頭的事,是他個毛病。」
老褚瞪了老裴一眼,這才坐下,讓老裴接著剃頭。老裴在外剃頭不說話,剃一天頭回到家,也不說話。家裡每天有十件事,十件事全由老婆老蔡做主。老裴按老蔡的主意辦,稍有差池,老蔡還張口就罵。老裴一開始還嘴,但一還嘴,老蔡就扯到了內蒙古,內蒙古那個野種,老裴就不還嘴了。當面罵人不算欺負人,罵過第二天,老蔡又把老裴挨罵的情形,當作笑話,說給別人,就算欺負人了。但這話傳到老裴耳朵裡,老裴又裝作沒聽見。十里八鄉都知道,老裴在家裡怕老婆。
這年夏天,老裴到蘇家莊去剃頭。蘇家莊是個大莊,有四五百戶人家,老裴在蘇家莊生意最大, 包了三四十戶人家的頭;三四十戶人家,剃頭的男人,有百十口子。老裴連剃兩天,到第三天中午, 方才剃完。老裴挑著剃頭挑子往回走,在黃河邊上,遇上了曾家莊殺豬的老曾。老曾要去周家莊殺豬。都是出門在外的人,老裴和老曾常碰面,在一起說得著。兩人便停下腳步,坐到河邊柳樹下吸煙。吸著煙,說些近日的閒話,老裴看著老曾頭髮長了,便說:
「挑子裡還有熱水,就在這兒給你剃了吧。」
老曾摸摸自己的頭髮:
「剃是該剃了,可周家莊的老周,還等著我殺豬呢。」想想又說:
「剃就剃。我剃個頭,那個畜生也多活一會兒。」
老裴就在黃河邊上支起剃頭挑子,給老曾圍上剃頭布,用熱水給老曾洗頭。待洗泛了,比畫一下,就下了刀子。這時老曾說:
「老裴呀,咱倆過心不過心?」
老裴一愣:
「那還用說。」
老曾:
「這裡就咱倆,那我問你一句話,你想答答,不想答就別答。」
老裴:
「你說。」
老曾:
「十里八鄉都知道你怕老婆,我覺得你不值呀。」
老裴的臉一赤一白:
「娘們兒家,有啥正性,免生閒氣罷了。」
老曾:
「我知道你前幾年有短處在她手裡。我大膽說一句,長痛不如短痛。有短處在人手裡,一輩子別想翻身。」
老裴長吁一口氣:
「這個理兒我懂。能短痛早短痛了,可就是短不了呀。」
老曾:
「為啥?」
老裴:
「沒短處在人手裡,事兒倒好辦;她嘗到了把你短處的甜頭,你想短痛,她倒不答應了。」
又吁出一口氣:
「不短也成,還有孩子呢;難就難在,從長說,她就可以不講理了。」
老曾:
「如果是我,她不講理,我就打她;等她受不了,就該講理了。」
老裴:
「如果單是她,事情還好辦,可她身後,還藏著一個講理的。」
老曾:
「誰呀?」
老裴:
「她娘家哥。」
老蔡他哥老曾知道,鎮上一個開生藥鋪的,叫蔡寶林,左臉生一大痦子,嘴特能說,得理不讓人,是一個死蛤蟆能纏出尿的人。老裴:
「俺倆一鬧,她就回娘家找她哥,她哥就找我來論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條理,我跟他妹過了十來年,有多少事多少理呢?我嘴不行,說不過他。」
又長出一口氣:
「都說論理好,真論起理來,事情倒更難辦了。」
又說:
「其實論理不論理我都不怕,就怕自己哪天忍不住,一時性起,拿起刀子殺了誰。能因為一句話殺人嗎,老曾?」
殺豬的老曾驚出一身冷汗:
「老裴,剃頭,我話說多了。」
楊百順他爹是個賣豆腐的。別人叫他賣豆腐的老楊。老楊除了賣豆腐,入夏還賣涼粉。賣豆腐的老楊和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是好朋友。兩人本不該成為朋友,因老馬常常欺負老楊。欺負老楊並不是打過老楊或罵過老楊,或在錢財上占過老楊的便宜,而是從心底看不起老楊。看不起一個人可以不與他來往,但老馬說起笑話,又離不開老楊。老楊對人說起朋友,第一個說起的是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老馬背後說起朋友,一次也沒提到過楊家莊賣豆腐也賣涼粉的老楊。但外人並不知其中的底細, 大家都以為他倆是好朋友。
楊百順十一歲那年,鎮上鐵匠老李給他娘祝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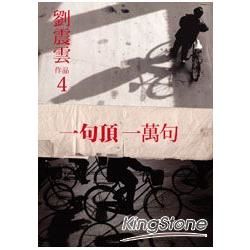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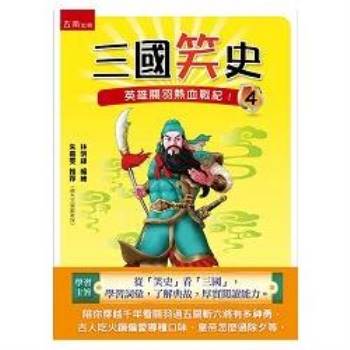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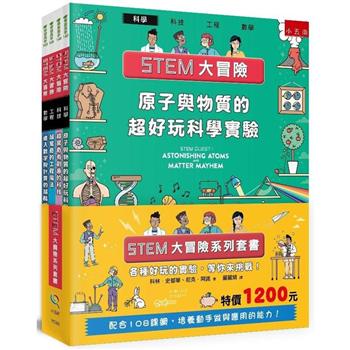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