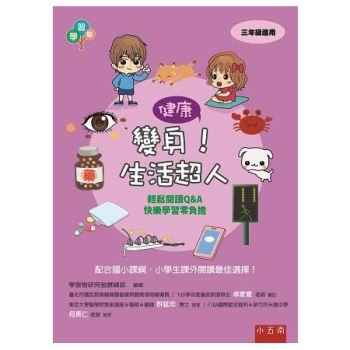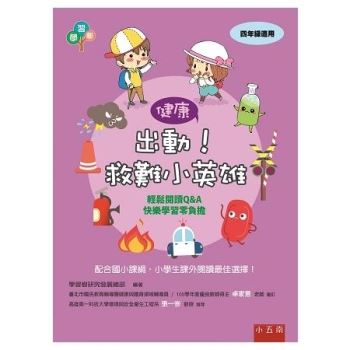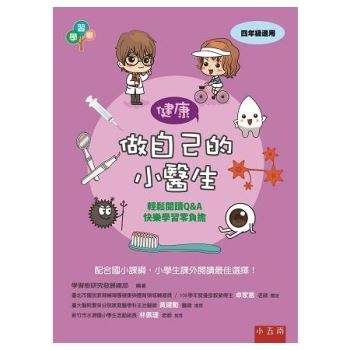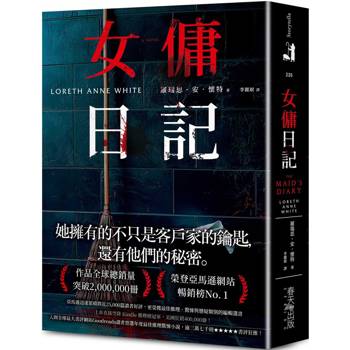林海音先生
四十年的文章,透明如玻璃;
五十年的婚姻,穩固如金石。
民國七十八年,何凡、林海音夫婦金婚,詩人余光中作此賀聯。寥寥二十二字,幾乎概括了這對文藝夫婦的一生:何凡在《聯合報•副刊》撰「玻璃墊上」專欄,每日一篇,持續數十年,所以上聯曰「四十年的文章,透明如玻璃」;何凡、林海音結褵五十年,是文壇上的典型佳偶,所以下聯曰「五十年的婚姻,穩固如金石」。
林海音(一九一八─二○○一)逝世,令人懷念,因為她的作品具有廣大的同情,因為她擔任聯副主編,創辦《純文學》月刊,對文藝界沾溉良多,更因為她性格上的奇特魅力,在文壇上獨領風騷。
林海音的小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發表在《文學雜誌》一卷四期的〈要喝冰水嗎〉。不識字的農夫闊嘴仔阿伯陪考,鈴聲響起,兒子出場與同學熱烈討論聯考試題,做父親的呆立一旁,絲毫插不上嘴,在尷尬不安的窘困中,終於冒出一句:「要喝冰水嗎?」時隔半個世紀,小說中主角的神情心態猶栩栩若生。難怪高陽評她「細緻而不傷於纖巧,幽微而不傷於晦澀,委婉而不傷於庸弱」。
林海音自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主編《聯合報•副刊》,至五十二年四月離職。近十年之間,倡導純文學,提拔文壇新人,不遺餘力。許多作家刊在《聯副》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她慧眼賞識下而出世,如黃春明第一次投稿的〈城仔落車〉(51•3•20),七等生的第一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51•4•3)、唯弦的〈赫魯雪夫〉(48•2•16)、鍾理和的〈蒼蠅〉(48•4•14)、陳之藩的〈迷失的時代與海明威〉(50•7•4),葉珊的〈樹薯國〉(50•6•25)……
林海音自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創辦並主編《純文學》月刊,共發行六十二期,次年又創辦純文學出版社(八十四年十二月結束),不但為台灣文學灌注了「純文學」的精神與活力,更由於她交遊廣闊、慷慨熱情、樂於提攜後進,使重慶南路的林宅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蔚為台北的文化中心。當時我年甫二十歲,還在師大國文系就學,就因為是《純文學•文思集》的作者,在她的引薦之下,親聞許多文壇前輩的流風餘緒。
林海音,大家都尊稱為「林先生」,她雍容大度,可敬可親,眉宇之間透現一股凜然嚴威,又流露無限親切溫馨。斯人雖逝,「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耳畔仍響起林海音先生鏗鏘的聲音:
「求其所同,尊重其所異!」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百萬英鎊買幸福
我們發現,光靠金錢要將一個普通的英國人變成一個幸福的英國人,非一百萬英鎊真莫辦。
這是英國華威克大學奧斯華教授的研究結論。本月九日外電報導,研究人員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每年調查九千個家庭,尋找出從「婚姻」、「健康」到「銀行存款」等各種影響英國人幸福感的諸多因素。研究人員有四點發現很耐人尋味:
一、意外獲得一千英鎊(約新台幣五萬元)橫財,只能讓人暫時有種幸福感,如果要維持這種幸福於不墜,非財源廣進不可。
二、財富不是獲得幸福唯一或最好的途徑。儘管最近幾十年來婚姻制度日漸沒落,婚姻卻比光憑金錢更能讓人幸福。
三、真正讓人幸福的還是健康。研究人員的結論是,身強力壯比腰纏萬貫強過幾萬倍。真正影響幸福的還是穩定的婚姻和健康,失業或離婚對一個人的幸福為害最烈。
四、美滿的婚姻一年大約值七萬英鎊,健康的身體一年更值二十萬英鎊。
其實,與幸福密切相關的,除了金錢、婚姻家庭與身體健康之外,還有各種因素,且處境不同的人對幸福的感受頗不一致:
生病的人自然覺得健康最幸福,貧窮的人當然認為有錢最幸福,囚犯能夠逃獄最幸福,考生認為金榜題名最幸福,戀愛中的人認為愛情最幸福,寫作的人認為文思泉湧最幸福!
還有,幸福也會捉弄富貴的人。香港有許多菲傭,月入港幣六千元,快樂得不得了;她們的雇主月入百萬港幣,很不幸福。教育部的工友無憂無慮,部長煩惱多多。所以,蘇俄的作家高爾基說得好:「只有在對美好事物的自覺追求中才會有真正的幸福。不要埋怨自己的力量菲薄吧,什麼也不要埋怨。您的牢騷所能給您的唯一東西只是精神貧乏者的憐憫和施捨。」
中國的諺語:「一勤二儉三節約,全家老少幸福多!」
幸福是一種感覺,繫乎自己的心境,蘇俄文豪托爾斯泰的名言:「為自己的幸福活著的人,低劣;為別人的意願活著的人,渺小;為別人的幸福活著的人,高尚。」我覺得只有善於自處與自得其樂的人,才可能成為幸福的人:
「懂得珍惜、掌握與享受自己手頭所能擁有的幸福,善莫大焉。」
──九十一年一月十九日
以人為可愛
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謾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
這是清代文人鄭板橋〈淮安舟中寄舍弟墨〉書信中的名言。以鄭板橋那樣嘻笑怒罵的文人,居然說出如此可親的話,真是異數。其實,懂得賞識人好處的美談,不乏其例,楊敬之〈贈項斯〉詩云:
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中唐詩人項斯以作品謁見前輩楊敬之,楊對項非常欣賞,題詩以贈。首二句謂:屢次讀到你的詩都很好,見面之後的感受,卻是人比詩更可愛(標格指風韻、氣質)。後二句謂:不喜歡將別人的優點藏在內心,所以到處讚不絕口。 細加思量,則「以人為可愛」內涵有三層:
第一層是每一個人都有可愛之處,也難免有可厭之處。如果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多看別人的好處,則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愛,感覺和蘇東坡一樣,「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所以《新唐書•魏徵傳》記唐太宗語云:「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如果吹毛求疵,專門挑剔別人的缺點,則人人皆看不順眼。
第二層是愛人者人恆愛之,嫌人者人恆嫌之。看人不順眼,常遭同等回報。所以《孟子•公孫丑上》:「惡聲至,必反之。」也正是辛棄疾〈賀新郎〉詞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人情一把鋸,你來我往嘛!
第三層是「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除了惺惺相惜的人性之外,更耐人尋味的是:只要我們隨時留意、欣賞、讚美別人的優點,把對方的好處存在心裡,掛在嘴邊,「到處逢人說項斯」,「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之餘,更可以在無形中受其沾染、感化,擷取各家的優點,自然可以薈聚眾長,集可愛於一身。
「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處處感受朋友的好處、優點,覺得每個人都可愛,不但對方會相知相惜,事實上,自己也在有形無形中變得更加可愛。苟能覺得世上每一個人都可愛,你就可能成為世上最可愛的人!
──九十一年二月九日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在古老的中國,從華北的北京,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古都,乃至江南的蘇州、杭州,大運河就像是人體內的一支大動脈,貫串南北。長江三角洲的沖積平原上,浩瀚無垠的太湖,正是靈秀所鍾的最大湖泊。太湖東北角上的蘇州,與長江北岸的江都(揚州),為歷史上兩大名城,「江蘇省」即緣此得名。
民國八十五年,我應邀赴徐州參加江蘇省修辭學會,途經南京,有山東籍的江蘇省政府高幹作東,席間談起江蘇省的今昔,我脫口問他: 「您山東老鄉到我們江蘇作官,對江蘇省的了解夠不夠?」
「我在江蘇蹲了四十多年,對江蘇的情況非常清楚!」
「那請您說說看,江蘇省為何取名江蘇?」
這下難倒了對方,一餐飯吃了兩小時,諒必找人去查詢,始終不得要領。他向我請教答案後,又問典出何處,我告以「想當然耳」。
「杜撰的來歷怎麼算數?」
「杜撰有的不可靠,有的絕對算數。您想想看,安徽省一半在江北,一半在江南,就得名自江北江南兩大名城──安慶和徽州!」
後來我到蘇州,蘇州大學的文學院長出面接待,並且謙稱校長公出,未能親迎。偶然動念:
「如果校長在座,我一定要考他一個問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典出何處?」
對方愣住了:
「我們錢培德校長是搞電子計算機的,肯定被你考倒。這個問題連我們一時間都答不上,他怎麼曉得?」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出典,只有蘇州大學的校長不能不知道。幸虧你們校長不在,否則的話,我就要請他讓位。」
「我們錢校長的位子您真的敢坐?」
「當然敢,坐三分鐘,照張相就還他!」
答案揭曉,典出南宋詩人范成大編《吳郡志•卷五十•雜志》:「諺曰『天上天堂,天下蘇杭。』」對方佩服得不得了,讚美我博學多聞,特地聘我為蘇州大學客座教授,備加禮遇。
其實,這真是美麗的錯誤,我絕對沒有像他們想像中的博學多聞,而是因緣湊巧:民國八十六年,應邀為中華電視台「莒光園地」製作介紹大陸風光的節目──「錦繡中華」,擔任撰稿兼主持人。其中第二集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當然要查考典故來歷。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當時在座的幾位教授,都是現代文學的專家,不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來歷,也無可厚非。不久遇到蘇州大學中文系的古典文學專家嚴迪昌,他脫口指明來歷,《元人小令集•雙調折桂令•西湖春二首第二折》:
「春暖花香,歲稔時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九十一年三月九日
芸娘餛飩 台北信義路永康街口的「鼎泰豐」,以茶點馳名海內外,許多日本觀光客不辭老遠,來此大快朵頤。每次經過門前,印象深刻的是常有食客排長龍,還有進門口一堆師傅在現做點心。食客眾多是外行看熱鬧,現包現做是內行看門道。鼎泰豐的美點,湯包、蟹粉小籠皮薄餡美,湖州粽子、雞燉翅入口即化,的確非同凡響。
推敲受食客歡迎的原因,無非是選料精、做工細、調味鮮。甚至比起揚州「富春茶社」的美點,也未遑多讓。富春茶社的蟹黃包子,是大閘蟹做餡,三丁包子、揚州獅子頭,源遠流長;且中古時期揚州為世界第一大港,千年美食文化盡萃於斯。富春茶社的美點,號稱世界第一,良有以也。不過,美食處處有,台北鼎泰豐、揚州富春茶社之外,茶點中的絕活,隨時有意外的驚喜,台北延平南路「郁坊」的鎮江餚肉、風雞,就被美食家常宗豪教授和香港「老正興」沈老闆評為青出於藍的極品。印象最深刻的是「芸娘餛飩」。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到蘇州,住在南林飯店,到對面十全街的「南園餐廳」飲早茶,有一道「芸娘餛飩」。顧名思義,典故出自清代文人沈復(三白)的名著《浮生六記》。沈復與其妻陳芸娘鶼鰈情深,〈閨房記樂〉膾炙人口;但他們雖然夫妻恩愛,卻是波折橫生,令人既羨且惜。「芸娘餛飩」清淡、精緻而又特別鮮美,當場向廚師請教做法的訣竅,無非是餡美、皮薄,不但講究火候,且現做現下鍋,其中的蝦仁就是活蝦當場現拆的。最特殊的一點,是餛飩包好之後,先在油鍋裡烹過,才放置沸水湯鍋裡煮。再追根究柢,對方就說不出所以然了。忽然靈光乍現:
「是因為愛情往往要歷經水深火熱的煎熬?」
「你怎麼知道?」
「沈三白說的!」
沈復昨夜夢中告訴我「芸娘餛飩」的緣由,因為不但同宗,聲氣相投,而且我們沈家四代以前的祖先就住在蘇州,太平天國戰禍才避亂遷居江北,「閶門沈氏」,可為明證。
──九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林語堂生活的幽默 一般人談到林語堂的幽默,往往側重於機辯風趣、詼諧風趣。其實,幽默大師的難能可貴,是生活中的情趣與豁達,能從淒風苦雨之中領略出風雨的情趣韻味,從尋常事物中透視出啟示……
這是馬驥伸教授對林語堂的描述,探驪得珠,頗能捕捉幽默大師內在心靈的奧祕。三月二十六日,台北市文化局整修陽明山仰德大道的「林語堂故居」,重新開幕。並委由佛光大學經營管理,展示林語堂的生活環境、手稿、藏書、文物等,期使幽默大師的流風餘韻,滋潤民眾的心靈。
盱衡幽默大師的幽默真諦,我以為林語堂能成為幽默大師的關鍵因素有四:
第一,創作與理論印證:早在民國十三年,林語堂即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徵譯散文並提倡幽默〉、〈幽默雜話〉;民國二十一年,又在上海創辦《論語》半月刊,提倡幽默、性靈小品。既有理論的闡揚,再加上作品的印證,所以在文壇上風吹草偃,引領風騷。
第二,東方與西方交融:林語堂不但介紹西方的幽默理論,而且將中國的幽默介紹到海外。《生活的藝術》在紐約發行,暢銷書排行榜上獨占鰲頭,讓全世界的讀者,都見識到中國式的幽默,從此幽默也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
第三,傳統與現代傳承:林語堂「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不但「兼通中外」,而且「通變古今」。〈論幽默〉文中闡揚傳統的幽默,從儒家、道家的幽默,一直說到陶淵明、蘇東坡的幽默,現代的幽默大師,映現了古典幽默的精神活力,更加靈氣飛舞。
第四,生活與幽默結合:林語堂的幽默,不只是在言談中自然流露,在文章中涉筆成趣,更重要的,是「生活即幽默,幽默即生活」。美國圖書館學者安德生在〈林語堂英文著作及翻譯作品總目•前言〉中說得好:
東方和西方的智慧聚於他一身,會覺得如在一位講求情理的才智之士面前親受教益。他有自信、有禮,能容忍、寬大、友善,熱情而又明慧。他的筆調和風格像古時的人文主義者,描述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深刻機敏、優美雍容。
「林語堂故居」開幕典禮上,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期許「台北的文藝復興」,壯志可嘉。台北市長馬英九也引述林語堂的名言:「紳士的演講,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並且以哈佛大學學弟的身分笑語:「林語堂哈佛畢業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更耐人尋味的是,從「故居」的負責人趙孝萱博士到擔任導覽的研究生簡文志等,似乎都沾染了優雅從容的幽默情懷。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林語堂在第三十七屆國際筆會演講〈論東西方文化的幽默〉時說得好:「幽默是人類心靈的花朵!」「林語堂故居」重新開放,讓台北的天空增添幽默的細胞,讓我們的體脈中流動著幽默大師的流風餘韻,不其懿哉!
──九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效法蕭伯納幽默(增訂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8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效法蕭伯納幽默(增訂新版)
施秋月﹝沈謙夫人﹞:
讀你那篇〈當下即報〉的文章時,我的感覺是:那不是寫寫文章說說而已,你是真心信仰這句話。從你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坦蕩蕩的君子所展現的風範與氣度。
鄭明娳﹝玄奘大學中文系教授﹞:
幽默中見透闢之識力,寬厚中隱含春秋之意見。先生散文最可貴處是流露高韜之性情與寬厚的人格。
王 堯﹝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
我始終覺得在沈先生著作與論述的背後,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心靈世界,他所有的文字幾乎帶著自己的血脈之氣,又連接著中國的文化傳統。
王潤華﹝新加坡國立大學特聘教授﹞:
沈謙自己從古今文學、經學、文字學、修辭學到文學創作,樣樣都造詣深厚,他就是我們期盼中出現的一位大師級學人。
作者簡介:
沈謙,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幼獅月刊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中興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系主任、新竹玄奘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曾先後主持華視「錦繡中華」、「中華文化之美」節目。著有《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得饒己處且饒己》、《書本就像降落傘》、《修辭學》、《林語堂與蕭伯納》等書。
章節試閱
林海音先生四十年的文章,透明如玻璃;五十年的婚姻,穩固如金石。民國七十八年,何凡、林海音夫婦金婚,詩人余光中作此賀聯。寥寥二十二字,幾乎概括了這對文藝夫婦的一生:何凡在《聯合報•副刊》撰「玻璃墊上」專欄,每日一篇,持續數十年,所以上聯曰「四十年的文章,透明如玻璃」;何凡、林海音結褵五十年,是文壇上的典型佳偶,所以下聯曰「五十年的婚姻,穩固如金石」。林海音(一九一八─二○○一)逝世,令人懷念,因為她的作品具有廣大的同情,因為她擔任聯副主編,創辦《純文學》月刊,對文藝界沾溉良多,更因為她性格上的奇特...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謙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10 ISBN/ISSN:9789574446148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