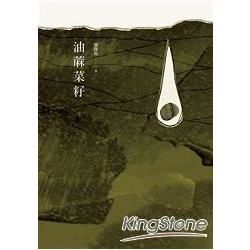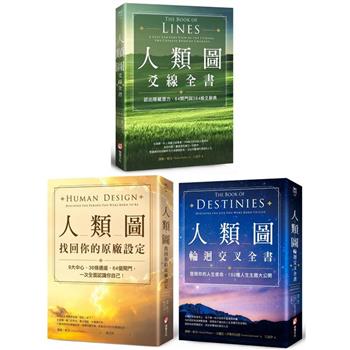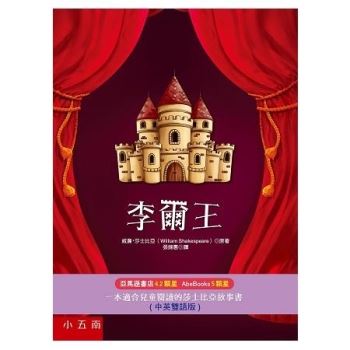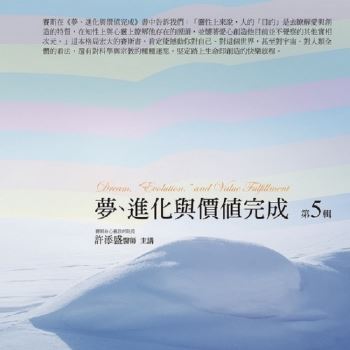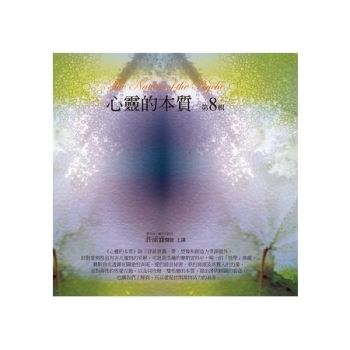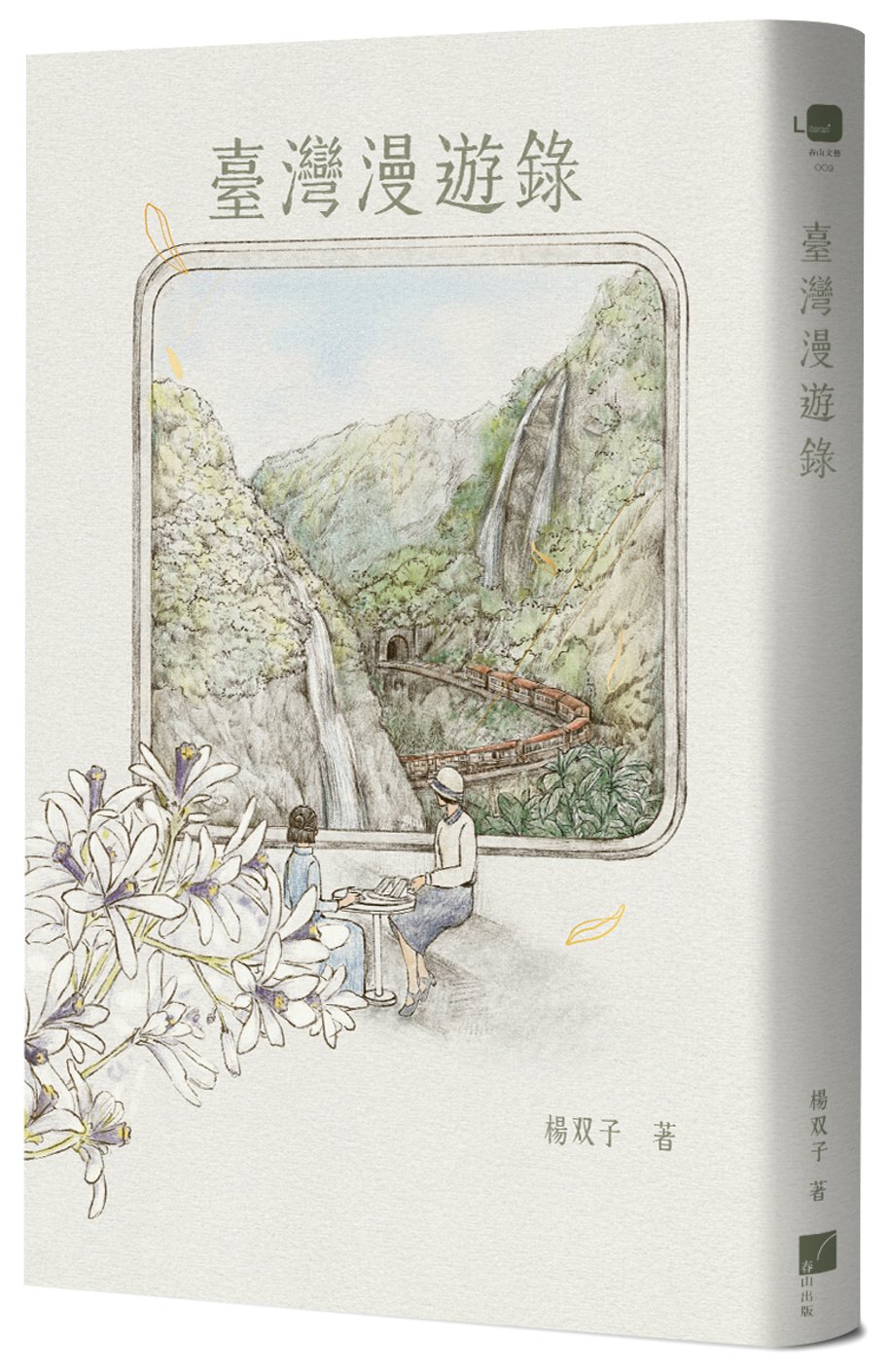重排新版序
油菜籽如今落在哪裡?
「查某囡仔是油菜籽命,落到那裡,就長到那裡」,這則台灣古老諺語,在農業時代,以不可撼動的堅固力量,定義著台灣女性服務者的艱苦命運,也定調了台灣女性終其一生無可逃避的服從與犧牲,是最真實三從四德的典範,更是禁錮台灣女性最無情的緊箍咒。
「油菜籽」的集體命運,也是出生在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我,身處其中、由茫然順服到不甘屈從,立意突破命運、找尋自己人生出口的漫長而苦澀的生命經驗。在偶然卻又必然的機緣下,將它寫成小說。它是一九八二年第五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的首獎作品,因緣際會遭逢女性主義正要在台灣萌芽的時候;也因緣際會在新舊社會交替的浪尖上被推湧而突出,很多女性讀了淚流滿面,男性則心情複雜。
小說得獎之後,很快又被拍成電影,除了聯合編劇的侯孝賢和我一起奪得金馬獎改編劇本獎之外,電影因小說的互相幫襯,也擠上了當時新浪潮電影的風光標竿上,到大阪、東京代表台灣電影參展;也在香港地區、特別是旺角,贏得廣大的共鳴,持續發散它的影響力;更難得的是,它會合了女性主義的洪流,勢不可擋的為開拓台灣女性的嶄新前途盡了一份棉薄之力。
三十年間,《油菜籽》這本小說,以台灣女性經典小說的身分,持續被許多所大學的中文系列為教材,也兩度被國立編譯館和台灣筆會譯介到世界文壇;美國康乃爾大學出版了當代華文女性小說選本(只有十名作者、十篇作品)行銷學界,《油菜籽》列名其中。今年,《油菜籽》更被學者推薦,翻譯成捷克文出版。這麼多年來,《油菜籽》被許多研究生做為論文主題,也曾被執教加拿大愛伯特大學的學者林蔚山拿來與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的作品相提並論,不因出版久遠而被遺忘,換句話說,三十年了,現在讀它的人,依然感動共鳴,所以是否可以說:它確實也禁得起時間考驗?它也確實反映了整個時代的吶喊與反省、推動了很大的改革?
很多讀過這本小說的年輕女性讀者都忍不住問我:「幾十幾百年來,女性一生都過著沒有自我、形同被迫害者般的生活,為什麼她們不會反抗?」「為什麼她們不能獨立生活?既然一樣是勞力,到哪裡都能換取生活所需,何苦一直留在不尊重妳的地方受苦?」「為什麼積重難返的兩性不平等關係,會輕易被一本小說撼動?」
其實革命是需要很多條件配合的,但是破冰更必須有一把利斧。讓女性覺醒的最大條件是─女性受過完整的教育,因為受過完整的教育,所以能夠有自己的經濟力,能夠擺脫被擺布的命運;也能逐漸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兩樣是充要條件。全球女性主義的覺醒,則是那陣東風,《油菜籽》則是小小的催化劑和劃開舊時代硬殼的利斧,萬事具備,東風也來了,終於為台灣兩性社會吹來一陣全盤重新大洗牌的旋風。
三十年了,我一直持續關心台灣兩性(特別是女性)的福祉與發展,如果問我一路走來的心情,我想可以用小說《油菜籽》書寫的心情來形容,那就是「悲欣交集」四字,有笑有淚,驀然回首,只有感謝─感謝這讓我們能當家做主的時代,感謝這允許我們全力奮鬥、也全心收成的社會!願所有四散飛揚、豐碩成長的油菜籽,成為照亮我們社會最溫暖、最光明的燈!
廖輝英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