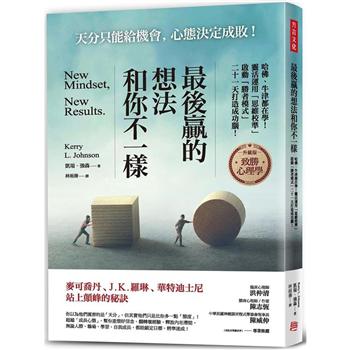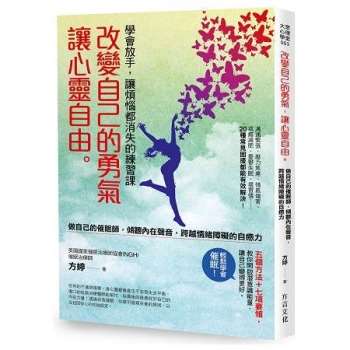序
XX人權公約規定⋯⋯
XX宣言宣告⋯⋯
世界衛生組織曾說⋯⋯
XX國家憲法明定⋯⋯
XX法律規定⋯⋯
從事公共衛生工作與研究,不會缺乏這些法律或政治文告作為倫理主張的基礎。許多的國家報告、政策文件、學術論文等,起首總是時常引用這些巨大而美好的倫理主張,接著展開後文的內容。彷彿只要承襲著這些主張,文件中所述的內容,就獲得、繼承了一種倫理正當性,值得而且「應該」受到讀者或大眾重視。對此,身為一名公共衛生學徒(a student of public health)的我,隨著在領域中學習浸淫日久,感到猶疑的程度也日漸增加。
當我們說我們要○○○時,我們到底做出了什麼倫理或政治承諾?
○○○可以帶入健康人權、群體健康、國家/民族健康、「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星球健康(planetary health)、健康一體(One Health),或者其他更多的美好群體生活想像。這些巨大的主張,都是極具規範性的倫理主張,換言之,這些主張都是在說,「我們」基於某些「倫理理由」,應該要去追求某些「應該追求的東西」。我並不是在說,我懷疑以上主張的根本倫理價值,或是質疑立法的政治正當性(雖然有些時候它們的確相當可疑),不消說,健康當然是個好東西,多多益善。但我還是忍不住好奇,撇開條文本身不管(法畢竟是人立的),所以,這裡說的「我們」是誰?基於哪些「倫理理由」?該去追求什麼「應該追求的東西」?這些東西是該由誰來負擔的集體責任、來聲索的權利、或實踐的倫理義務?健康在這些東西之中,總是最重要、最優先的價值嗎?這些問題使公衛學徒深深困惑。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嘗試回答這些根本問題。
公共衛生與廣泛健康科學傳統上是高度技術導向的研究領域,較少機會處理到公衛政策與實作所仰賴的那些規範預設與架構。這些問題,在多年的公共衛生政策實作之中,已經或多或少以一種「事實上存有」(de facto)的方式來回答了,也就是,政策確實做出了這些價值判斷。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判斷就是倫理上較可欲或較為正當的判斷,這正是本書的主要工作。這是一本「公共衛生倫理」(public health ethics)的專書,書中所提出的,是對公共衛生政策與實踐倫理正當性的叩問,本書也嘗試以公衛健康議題為核心,與政治、倫理、社會、人類學等不同領域對話,借助不同領域的知識,來解決人們每日生活中共同遭遇的公衛問題。
這樣的定位,也使得本書在風格上與一般自然生醫或社會科學導向的公共衛生領域著作不太相同,儘管是研究,但它並不是「科學」研究成果的彙報,儘管蒐集許多資料並以之為論述參照,但它也沒有提供什麼堅實的「證據」。我在本書中提供的答案,主要是一種綜合的分析架構、觀看的視野,可以合理地應用於思考各個不同的公共衛生或健康政策相關議題。有些時候,我會講出我自己認為某件事情在倫理上最好的某種「主張」(這種時候,我盡量會在文中直接說出,而不會迂迴隱晦等待讀者自己發掘)。這是一般公共衛生倫理研究的常見途徑。
然本書要再更往前退一步,不僅是應用倫理概念、原則與理論來處理公衛介入會遭遇到的倫理難題,本書也要去探問那些更為根本的前提預設,也就是應該共同行動的我們是誰的「邊界問題」(boundary problem),這也是本書名為「重返邊界」之由來。需要「重返」(revisit,或稱為再訪、再探),正因為我們通常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但邊界並不是一開始就在那裡的,好像某天就從天上掉下來,或是被天啟或命運所指定一般,邊界除了指地理上的疆界,也包括共同經營生活、甚而互相負有義務的人們的邊界,也包括橫跨現在與未來的時空邊界。邊界與我們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政治生活所需的團結,以及朝向未來的永續經營,都有密切關係,釐清這些關係,是本書的主要任務。
這樣一本公衛倫理專書,在某個程度而言—借用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序言的用詞——必定是「固執己見的」(opinionated)(2012: 15),我提出的架構和主張,必然是源自我的見解以及其他可能的倫理與政治立場。但我希望讀者清楚辨明,我的主張也只是眾多主張中的一個版本,一方面我當然希望能夠透過論述說服讀者這些主張的合理性(儘管讀者最終可能仍不同意,沒有被我的主張說服,卻可在最低度的、共同想望健康未來的社會合作前提下,認可這些主張有些值得參考之處),這樣很好,這是論述本身學術價值與創見的彰顯;另方面,我更期待的是,在之後收到讀者進一步的反駁、批評或延伸討論,吸引越來越多人關心公共衛生的倫理層面議題。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建立定於一尊的完善倫理主張,而是想邀請讀者們一起參與這個宏偉的思想工程。
撰寫一本書,理論上是可以沒有完成的時候,但篇幅的限制、出版的時程、(計畫的結案、)地球的自轉、種種的因素,使得我必須在此停筆(作為一種寫作的比喻,本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20年代,應該沒有人真的在用筆寫書了)。還有很多未能完成的分析、未能解答的問題,我在本書中各處,有指出其中一些我認為值得繼續發展的方向,當然,肯定還有更多,就留給未來繼續努力吧。
10/23/2023 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