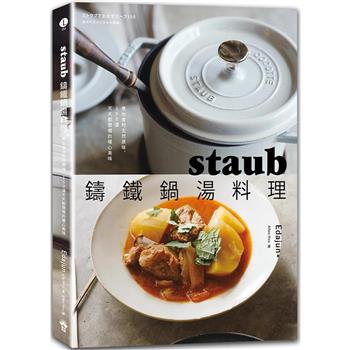本書為楊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種,為楊天石先生關於中國近代思潮與人物研究的論文集。民國史是楊天石先生數十年來研究的主業,本書集結了包括近代思潮、文藝思想研究、黃遵憲論叢、魯迅論叢、錢玄同論叢、胡適論叢在內的六部分,論述涵蓋儒學、民主主義、“國民國家”思想、翻譯史的思潮演進、平均主義、國粹主義、漢字簡化議題等在近代中國紛繁起伏的思潮,涉及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羅隆基、鄧演達、蘇曼殊、陳由己、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章炳麟、馮桂芬、鄧實、黃遵憲、魯迅、錢玄同、胡適等數十位近代中國思潮史中的重要人物及其觀點。
作者簡介:
楊天石
1936年出生於江蘇興化。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第一中學。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
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華書畫家》雜誌顧問、上海《世紀》雜誌顧問、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編委。中央文史研究館34卷本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副主編之一。曾任中國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為《中國文化詞典》副主編之一。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1卷、第6卷等。個人著作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揭開民國史真相》(7卷本)、《楊天石文集》、《尋求歷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朱熹及其哲學》、《朱熹》、《朱熹:孔子之後第一儒》、《王陽明》、《泰州學派》、《南社史三種》、《半新半舊齋詩選》、《橫生斜長集》等。主編有《〈百年潮〉精品系列》(12卷)、《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4卷)等。
楊天石參與寫作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獲國家圖書獎榮譽獎。個人著作《尋求歷史的謎底》獲國家教委所屬高校出版社及北京市優秀學術著作獎。《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1輯獲全國31家媒體及圖書評論家協會十大圖書獎以及香港十大好書獎,第2輯獲南方讀書節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獎,第3輯及第4輯獲《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獎。楊天石著作所獲的獎勵還有孫中山學術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著作獎等。《帝制的終結》獲《新京報》2011年度好書獎,是當年該報獎勵的唯一歷史圖書。
作者序
“考證確鑿”與思想的力量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套用“入所教育”的俗話一句,我已正式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新兵”。這時,楊天石老師早就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健將”了。從年齡到學問,楊先生都是我的師輩。相識相交近四十年,從楊老師處獲益多多,沒得說,一直以老師相待。但沒想到入所不久,就被楊老師賞識有加,以友相待。作為“新兵”的我,端的是受寵若驚。近四十年亦師亦友,學術、思想、觀點的交流更無拘束也更加暢快、更加深入。楊老師還具有深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關切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在本職工作之外,曾兼任以實事求是、秉筆直書著稱的《百年潮》創刊主編,著名理論家龔育之先生將他與胡繩、鄭惠並譽為《百年潮》創業“三君子”之一。他有幾次“直言上書”,事先都徵求我的意見,士人風骨,令人敬佩,而對我的信任,更令我深深感動。當然,還是沒想到,楊老師此次竟然邀我為《思潮與人物》冠序,一時間感悚並至,確感榮幸,同時又知道自己其實無此資格與水平。恭敬不如從命,不揣冒昧,竦然作序。
一
楊老師認為,追求歷史真相是歷史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無論這種真相多麽“不如人意”,也必須面對。這是他對自己治學態度、方法的要求。幾十年前著名的“中山艦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次事件,已成板上釘釘的“鐵案”。但楊老師卻細讀史料,於不疑處發現可疑之處,一點點尋找、發現、研讀、分析史料,在80年代發表的《中山艦事件之謎》,還原了“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被譽為具有“世界水準”的好文章。他對史料的追尋,著實到了“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地步。他在海內外到處搜尋史料,早早就發現了錢玄同未刊日記、《蔣介石日記類抄》,對史料幾近“竭澤而漁”。不預設立場,不為既有觀念束縛,注重史料的爬梳考證,尊重史實,楊老師堪稱典範,為學界公認。
“考證確鑿,堪稱傑作”,是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狹間直樹教授對楊老師的評論。日本學者向以資料搜求仔細全面、考據認真著稱,狹間先生此評確為的論,是楊老師治史方法、風格的總結概括。
二
“考證確鑿”的盛名,卻無形中掩蓋了楊老師學術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其實,楊老師的學術研究恰是從思想史研究起步、開始跨入學術大門的。楊老師是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畢業後到中學當老師。這時他寫的明代泰州學派傳人韓貞、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研究文章,就先後發表在權威的《光明日報》“哲學”專刊和《新建設》雜誌。他的研究,引起了史學大家侯外廬先生的注意。“文革”結束,楊老師從中學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為專業研究者。
歷史研究向有兩種傳統,一是“六經注我”,一是“我注六經”;用現代學術語言來說,一種強調研究者主觀觀念的主體性投射,一種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實證分析。前者高屋建瓴,自成體系,但易失之於空泛,根據不足而形成“無據之理”,牽強附會甚至淪為荒誕。後者踏實細密,言皆有本,但易失之於瑣屑,缺乏概括綜合而“不成體統”,淪為無法把握大局、看不到整體的細瑣繁屑。“六經注我”而不荒誕,“我注六經”而不瑣碎,至為不易。思想史研究多是“六經注我”,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所以屢有宏大體系建構者。然而,正是由於“六經注我”,不少體系建構者擺脫史實史料的束縛,洋洋灑灑、大言炎炎、巨著皇皇、體系宏大,但夷考其實,這些所謂體系皆是遊談無根、郢書燕說,剪裁塗抹史實以符合某種理論框架的荒謬荒誕之論。
楊老師的思想史研究秉承的是“論從史出”的傳統,他提出的論點是逐步地、一點一點抽絲剝繭地建構起來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毫不牽強。
社會主義,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思潮,並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命運。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並有專門研究機構。然而,楊老師卻從著名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史,從劉師培的幾篇短文的分析中,使人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歷史過程、中國知識界的心路歷程。
早在1903年蘇曼殊將《悲慘世界》部分翻譯,名為《慘社會》,1904年由陳獨秀修改、加工,改名為《慘世界》。他們並非嚴格的翻譯,而是有譯有作。翻譯《悲慘世界》第二卷的第一到第十三節,有增有刪,如增加一段敘述:“哪裏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哪裏有真正行善的人呢?”作為譯者,蘇、陳還憑空增加了明男德、范財主、范桶、孔美麗等幾個人物和情節,表達譯者自己的思想。《慘世界》有一農夫生有一女一子。女兒出嫁之後,兒子無人照顧。蘇曼殊寫道:“他的親戚和那些左右隔壁的鄰居,雖說是很有錢,卻是古言道:‘為富不仁。’那班只知有銀錢、不知有仁義的畜生,哪裏肯去照顧他呢?”“你看那班財主,一個個地只知道臭銅錢,哪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才有分無立錐的窮漢。”又說:“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做工的仗著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著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哪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蟊賊呢?”譯者藉自己創造出的明男德嚴厲批判金錢,主張財富公有:“哎!臭銅錢,世界上哪一件慘事,不是你趨使出來的!”“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哪鑄定應該是哪一人的私產呢?……”又稱:“我看這財帛原來是大家公有的東西。”第十二回,譯者甚至聲稱:“雅各伯黨定了幾條規矩”:第一條,取富戶的財產分給盡力自由之人以及窮苦的同胞。第二條,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和佔奪他們財產的權利。第三條,全國的人,凡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收回。第四條,凡是為左右而死的遺族,需要盡心保護。第五條,法國的土地,應當為法國人民的公產,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佔有,不准一人多佔土地。
楊老師評論說:“核心是土地公有,同時無償地剝奪富人的財產,均分給貧苦人民。”“它既繼承了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的‘均貧富’思想,但又表現出鮮明的近代革命色彩。”“《慘世界》的‘規矩’顯然可以視之為20世紀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綱領。在辛亥革命前夜眾多的革命宣傳品中,《慘世界》的獨特之處在這裏,它在近代中國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獨特地位也在這裏。”約二十年後,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當非偶然。
說起劉師培,人們首先想起“無政府主義者”和擁袁復辟的要角。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他的作用不能低估。1907年,流亡日本的劉師培接觸到當時的“新思潮”,也設計了一個實現“共產”的社會方案。在他的宏大藍圖中,那個社會不僅土地、生產資科公有,而且一切產品和財富也都公有,“完全平等”。這種平等不僅表現於沒有任何統治者或管理者,而且在消費、生活的各方面也全都一樣。“人人衣食居處均一律”,要求大家穿一樣的服裝,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房子。既然中國的傳統服裝是寬松的“深衣”,那你就不能穿洋服;既然食堂供應窩窩頭,那你就不能吃白麵饃饃。楊老師文中特別說明,劉師培是近代公共食堂的提倡者,他要求在每鄉建立“會食之地”。
劉師培設計的“共產”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均力”。他認為人人做工,人人勞動,固然是平等了,但是,同一做工,苦樂難易,大不相同。譬如造釘製針,活兒很輕松,而築路蓋房,幹起來就很吃力,兩者之間還是不平等。因此,他提出了“人類均力說”以平均苦樂難易。他將人分為三個年齡段:一,二十歲以前在老幼棲息所受教育。二, 二十一歲至三十六歲,從事農業勞動,兼做其他工作。即二十一歲築路,二十二歲開礦伐木,二十三歲至二十六歲築室,二十七歲至三十歲製造鐵器、陶器及雜物,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紡織及製衣。三, 三十六歲以後,免除農業勞動,從事各種工作。即三十七歲至四十歲烹飪,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運輸貨物,四十六歲至五十歲當工技師及醫師,五十歲以後入棲息所任養育幼童及教育事。劉師培要求每一個人都按照這一鐵定程序輪換。若想當運輸工人,先幹十六年農業活兒,再當四年廚師,在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才行。你想當老師,那就要等到五十開外,遍歷農、工各種行業之後。可以有人不想當醫生,但輪換表中有此一項,非當不可。至於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新聞家,輪換表中沒有,任何人都別想業此。劉師培把他的這種設計稱為 “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是“權利相等,義務相均”的最高美滿境界。至於實現他的宏圖的方法、手段,他在《論水災即係共產無政府之現象》、《論水災為實行共產之機會》這兩篇文章中稱,水災一來,田地也沒了,房產也沒了,金銀珠寶也沒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難,其結果必然是到處被逐,叩頭哀求而難得一飽。於是,飢民起來“革命”。
經過一番分析,楊老師對劉的理論得出如下結論:“不能認為劉師培的‘均力’說完全荒唐。從有分工以來,人類就渴望打破分工的束縛。歐文、傅立葉、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設想過,在未來社會裏,勞動者可以全面地發展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志趣經常地自由地調換工種,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但是,社會主義大師們所設想的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人的全面解放,而劉師培所設想的則是自然經濟基礎上人的全面束縛,其結果只能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文化事業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倒是‘史無前例’的十年間,將工人調到大學和研究機關去‘摻沙子’,將知識份子趕下幹校去‘學工’、‘學農’,很有那麽一點實行‘均力’說的意味。”“劉師培的‘水災共產主義’提出於本世紀(20世紀)初,今天的讀者也許會視作一種笑談。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訓卻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國,無視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以為在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只要變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想法,並不是個別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人們吃了不少苦頭之後才認識到的真理。”
不知不覺中,顯示出思想的力度。
從事思想史與歷史人物研究,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闡釋之時,如何能夠運用理論框架而又不被這種理論淹沒束縛,以保存歷史上的思潮與人物,和同作為研究者的“我”的雙重主體性為定位,確實需要一種意識和方法上的自覺。楊老師對“思潮與人物”的研究,既保有自己的主體性,同時又充份尊重史料,絕不妄解。他的研究,在一層層探討時代思潮、歷史人物的社會性時,解開了一道道傳統意識形態枷鎖,擴展了我們對思潮、人物與歷史進程互動層面的理解與觀察,加深了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歷史學者
“考證確鑿”與思想的力量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套用“入所教育”的俗話一句,我已正式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新兵”。這時,楊天石老師早就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健將”了。從年齡到學問,楊先生都是我的師輩。相識相交近四十年,從楊老師處獲益多多,沒得說,一直以老師相待。但沒想到入所不久,就被楊老師賞識有加,以友相待。作為“新兵”的我,端的是受寵若驚。近四十年亦師亦友,學術、思想、觀點的交流更無拘束也更加暢快、更加深入。楊老師還具有深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
目錄
序:“考證確鑿”與思想的力量 雷頤
第一部分——近代思潮 001
儒學在近代中國 002
戊戌維新以來的“國民國家”思想 012
蘇、陳譯本《慘世界》與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潮 028
章太炎為何要砸拿破崙與華盛頓的頭 040
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張繼 042
《天義報》、《衡報》對“社會主義講習會”活動的報導 044
論《天義報》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 049
劉師培的平均奇想 073
劉師培的“水災共產主義” 074
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 077
陳獨秀組織對泰戈爾的“圍攻”——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094
第二部分——文藝思想研究 099
馮桂芬對桐城派古文的批判與衝擊 100
鄧實與湖海有用文會 105
第三部分——黃遵憲論叢 113
海外偏留文字緣 114
讀黃遵憲致王韜手札 116
黃遵憲厚“今”重“我”的文學思想 129
黃遵憲傳 137
第四部分——魯迅論叢 225
釋“擠加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入” 226
《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與中國近代史上的護礦鬥爭 229
讀《魯迅〈中國地質略論〉作意辯證》 232
魯迅早期的幾篇作品和《天義報》上署名“獨應”的文章 237
“咸與維新”的來歷 240
周氏三兄弟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之二 242
讀魯迅與胡適軼札 246
第五部分——錢玄同論叢 251
振興中國文化的曲折尋求——論辛亥前後至“五四”時期的錢玄同 252
論錢玄同思想——以錢玄同未刊日記為主所作的研究 273
錢玄同與胡適 294
漢字“橫行”與錢玄同 327
錢玄同自揭老底 329
潘漢年與錢玄同——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331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前言 337
第六部分——胡適論叢 345
溥儀出宮、胡適抗議及其論辯 346
胡適曾“充份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讀胡適《歐遊日記》 350
《醒世姻緣傳》與胡適的“離婚”觀 ——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355
胡適抗議“反革命”罪名 ——因北京大學復校引起的爭論 359
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 362
跋胡適、陳寅恪墨蹟 386
胡適與蔣介石的最初會見——讀胡適日記 389
胡適1933年的保定之行——讀胡適日記 392
周作人與胡適的唱和詩 394
胡適撰寫的一篇白話碑文 398
柳亞子與胡適——關於中國詩歌變革方向的辯論及其他 401
胡適與楊杏佛 416
胡適與陳光甫 443
蔣介石與晚年胡適 464
附錄
我和民國史研究 517
進一步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訪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 530
序:“考證確鑿”與思想的力量 雷頤
第一部分——近代思潮 001
儒學在近代中國 002
戊戌維新以來的“國民國家”思想 012
蘇、陳譯本《慘世界》與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潮 028
章太炎為何要砸拿破崙與華盛頓的頭 040
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張繼 042
《天義報》、《衡報》對“社會主義講習會”活動的報導 044
論《天義報》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 049
劉師培的平均奇想 073
劉師培的“水災共產主義” 074
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 077
陳獨秀組織對泰戈爾的“圍攻”——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094
第二部分——文藝思想研究 099
馮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