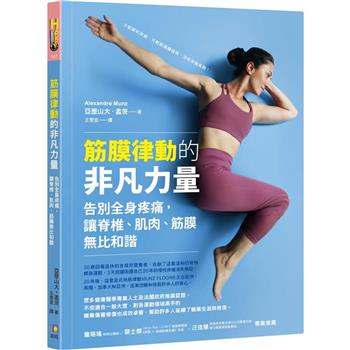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呼蘭河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6 |
小說 |
$ 306 |
中文書 |
$ 30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呼蘭河傳
1.名家經典。本書是蕭紅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亞洲週刊》組織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作品中,《呼蘭河傳》排名第九。
2.本書是中國現代小說散文化的代表,同時也被後人認為是繼魯迅之後對國民心態反省和批判的力作。
3.本書亦可供讀者了解抗戰時期作家在香港的文學活動。
4.可配合許鞍華執導的關於蕭紅的電影的宣傳。
《呼蘭河傳》是民國才女蕭紅在香港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説,也是她的巔峰之作。小說以作者的家鄉和童年生活為原型,描繪出了作者記憶中的家鄉呼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東北小鎮的單調與美麗、人民的善良與愚昧。全書七章:一、二章寫小城風情,三、四章談家中親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繪獨立旁枝人物。七章可各自獨立又渾然一體。
作者簡介:
蕭紅原名張廼瑩,1911年端午節出生於黑龍江,幼年喪母。她在中學時期接觸五四運動以來的進步思想和中外文學,尤受魯迅、茅盾和美國作家辛克萊作品的影響。蕭紅的作品,經常表現出兩種主要關懷:鄉土與女性,其語言風格溫順平和,略帶哀婉氣質。
商品資料
- 作者: 蕭紅
- 出版社: 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4-09-30 ISBN/ISSN:97896207450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