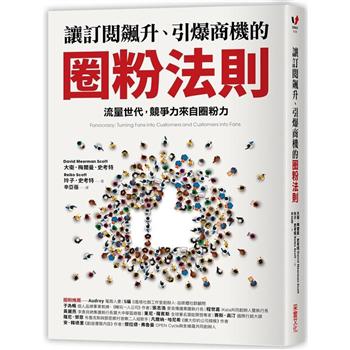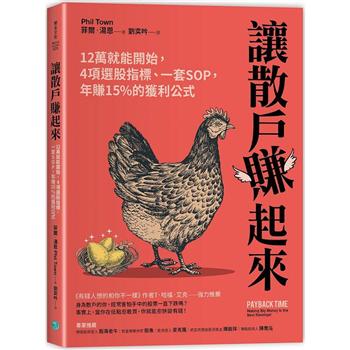存在主義的安慰
那只粉色的小行李箱羞怯地躲在她的床邊,目測不超過十八吋,幾位兒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圍繞著她,吱吱喳喳問道:「妳怎麼有個這麼可愛的行李箱啊?這個行李箱小到連離家出走所需的家當都塞不下吧?」
她沉默,一頭褐色長髮披散在小麥色的肩上,脂粉不施的臉蛋透出十六歲少女才有的細嫩光滑。如此突兀的存在。幾乎以為她是誤闖加護病房的逃家少女。她應該在陽光下。
妳凝視著她,眼中隱約有另一張臉交疊在她臉上。是妳在精神科的primary care。相同身高、體重、膚色。在她抬起頭還來得及與妳相視之前,妳趕緊低下頭。這是一個錯誤,一個玩笑。妳想。上帝總是有著饒富興味的幽默感。
妳深深的將外界的空氣吸進肺部,鼓起勇氣上前對她說:「我是X醫師的實習醫學生,我姓李,我接著這幾天都會來看妳喔!」
她略帶疲態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妳想起另一個少女,妳第一次見面對她說的是:「妳願意陪我走一段嗎?」她那時笑靨綻放如一朵曇花。短暫甜美得令人心痛。
眼前這位少女不是她,也不會是她。這只是一個替身,是妳乾涸的情感沙漠中偶然閃現的海市蜃樓。
也好,人總是需要短暫的慰藉,縱使虛實不分。那又如何呢?
而且妳已經怕了,這一切靈魂的穿刺,抽出了甚麼?又剩餘甚麼?
一切淺淺輒止即可。妳決定。核爆最後只會殘存廢墟。
躺在病床上滑著手機的她對於妳內心的曲折一概不知,她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主體性,成為被妳情感投射的客體。
第一次的對話稀稀落落,妳努力找回自己在精神科與病人會談的能力,不知道是因為這幾個月在內科病房的「訓練」,妳發現自己的舌頭不屬於自己,那些以往自然吐露的話語到了舌尖瞬間融化,妳成了失語症的病人,只能僵硬的問她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平常滑手機都在看甚麼?在這裡是不是很無聊?平常是跟誰住?
越多話語自妳口中流出,妳越是羞愧地想要逃離。妳自己都無法想像有醫學生與妳進行拙劣的對話,一字一句在心湖裡噴濺出惹人厭的巨響。上帝,怎麼樣才能讓我結束這場讓人無地自容的對談?妳習得無助的思忖著,如果每天都必須如此那會是莫大的鬧劇!所幸對話到了一個無法推進的窘局,妳立刻敷衍了幾句:妳好好休息啊!我明天會再來看妳!離開時,妳幾乎是踩著小跑步如夾著尾巴的小狗一拐一拐的掃出現場。
隔天下午三點,妳在她的病房門外踟躕著敲門的時機,在妳終於蓄積了面對現實的勇氣開門進去後,妳看到她的病床為簾幕掩起。妳內心的小聲音扯著妳一步一步倒退至門口,過程中妳縮到不能再縮的勇氣依舊徒勞的試著改變妳的動向。妳輕輕的關上門,如釋重負。晚點再來看她好了,妳對自己一再確認,妳不是膽小鬼,只是體貼病人,不想不合時宜的打擾她。
晚上六點,妳真的得不合時宜的去打擾她吃飯,不然當天的progress note交不出來。再一次,妳拖著沉重的腳步出現在門前,妳整整衣領,反覆確認聽診器是聽得到聲音的,做好「萬全」的準備,妳敲了三下,拉開門,直直的走到那個為簾幕隱藏起來的病床,在簾幕外對著她說:「真真,我來看妳了。」
她應了一聲,揭開簾幕,妳發現她伏案讀書,擺的是社會科。妳笑了,問她是不是在準備期末考,她立刻哀號一聲,說她缺了幾十堂課,進度落後很多,社會科是她喜歡的科目,她還可以自己讀,然而數學物理她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妳說妳以前也最討厭數學物理,但是為了考試不得已一定要讀。妳們開始抱怨數理,討論起熱愛的歷史與地理。第一次,妳在她疲倦的雙眼看到光。那是年輕的心靈尚未熄滅的篝火。
「妳以後想做甚麼呢?」妳問
「我以後想要走企業管理相關,但我爸媽覺得我沒辦法。其實這個寒假我有報一個企管營,在台北,但我爸媽不准我去。他們覺得以我的狀況是不能去。」
她側著臉,陰影投射在她半邊臉。妳沒有體驗過一年住院住到自己數不出次數,妳不知道一葉的肺被切除呼吸是何等費力,有太多事妳不知道。妳想起另一個少女,她那一晚吞了八十顆Flunitrazepam1,隔天還是爬起來上教會,儘管知道上帝拯救不了她。妳只知道自己曾經被許多躲在暗處的惡意戳刺到不願從床上爬起去上學,多少個早晨妳伏著洗手台努力不使翻攪痙攣的胃擠出胃酸。
但妳還是決定讓自己站在陽光下,妳知道陽光不會審判妳,它對每個人都是仁慈公平的。
「其實人活著就注定承受很多病痛,有些我們可以預防,有些我們無法,面對那些我們無法預防的劫難,我們唯一無法被奪走的是心中的夢想。妳雖然有這樣的病,但這也擋不了妳去追尋內心想要的,勇氣會讓妳生出翅膀,也許也會為妳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她抬頭迎向妳的目光,眼神不是妳能讀盡。
美,往往是生於苦難,苦難卻不一定會孕育出美。
雖然如此,妳還是想要相信這一切苦難是有意義的,妳想要相信漫漫長路的盡頭是有甚麼等著她們。雖然她們不見得能活著走到。
「最重要的事,不是肉眼看得見的。
這一切都只會是暫時的,妳必須這麼相信」
妳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她的肩微微動了一下。也許是一種微弱的回應。
妳也必須這麼相信。這樣妳才能繼續好好活下去。
兩年後,妳在一次外科值班查詢急診簽床名單看見她的名字,這次她是發燒、咳嗽有濃痰來急診,因為免疫不全的underlying2,她被簽往兒科加護病房。
妳複製她的病歷號,在體系病歷上搜到她過往兩年的門診紀錄。在值班為數不多清閒的縫隙之中默默拼湊出她這兩年來的輪廓:數不清的回診,有小兒心肺、小兒免疫,以及小兒精神,幾次急診紀錄(每一次都是前一次的複製,發燒咳嗽有濃痰)。妳知道她有在吃預防黴菌感染的用藥以及抗憂鬱藥物。她曾經因為抗憂鬱藥物以及對所有事物興趣缺缺而胖了幾公斤。她的key person3是媽媽,卻與媽媽漸行漸遠,而從前住在一起的爸爸與阿嬤也很少見到她。
一個漂浮的孤島,妳想。
我從國中到現在最熟悉的地方就是醫院。
我很害怕,很不喜歡來看醫生。每次的回診都提醒著我的殘缺。
在十六歲那一年右下肺葉被切除後,我總是想著哪時候我另一個肺葉也要犧牲。
有時在想會不會哪一次進來了就出不去,被關在陽光到不了的小房間裡,最後一點一滴與無光融為一體。
我有時很希望我沒有被生下來,我愛我爸媽但又無法原諒他們。
或說我無法原諒的是自己,帶病的自己。
妳想像著她在精神科診間裡,面對著醫師,以退化成嬰孩的姿態大哭大鬧,蜷縮在椅子上。這些話注定是深深葬在她心底那不知何日才會消融的永凍層。
她如果說出了,她就會死去,然後重生。
然而,她沒有死去。
她繼續活著,以失重的飄浮狀態。
妳在還來得及預測她將被帶往何處之前就被樓下ICU4叫下去幫忙壓胸。
在妳雙手壓著那具因為肋骨被壓斷而凹陷的胸廓時,妳很清楚自己只是在執行醫療常規,妳手下這個沒有脈搏的阿嬤不會因為妳跟學長們多壓三十分鐘就活起來。
但因為家屬還沒有準備好讓她走,妳們四位輪流上陣一邊揮汗一邊壓胸,等到急診的壓胸器上來繼續壓。
結束後妳瘸腳般慢慢走回值班範圍。一走回來,護理師湧上來跟妳報:
李醫師,治療室那一床血壓在掉了,現在是65/35,妳還要把Levophed 5上調嗎?
妳硬拖著一身疲憊走進治療室,那個行銷骨削的癌末阿公躺在床上,開始出現Cheyne stokes6呼吸pattern,他兒子一看到妳從躺椅上倏地彈起來,湊上來等待妳。
妳緩緩轉向他說:差不多是時候了。
他壓抑著內心所有情緒自制的點點頭,拿起手機開始叫家人與葬儀社的人準備好。妳悄悄的走到病人面前,剪掉他身上pigtail7的綁線,他杏眼圓睜的注視著前方。妳從他眼中看不到自己的倒影,只是無盡的黑暗。
妳在家屬蜂擁而至之前離開了治療室,躲進值班室,當時是凌晨兩點半,妳準備和衣而睡。兩年前她最後一次凝視妳的眼神幽幽的浮上妳面前,逼得妳無法不直視。
那一刻的妳張口想說甚麼,濕濡濡的話語卻瞬間乾涸。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咬子彈的女人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咬子彈的女人
給下一輪年輕醫師的備忘錄
人是如此怕痛的物種,但痛就是活著的證據。這本書,獻給還在感受痛的你。
女醫以溫柔的文筆,書寫在醫院的所見證的生老病死、聚散悲歡,試圖以另一種方式,同自己、同病痛和解。
作者簡介:
欠斤小姐
1996年生的孩子,現任不分科住院醫師第二年,性格是各種矛盾的組合—敏感卻大膽,活潑卻內向,看穿人心的影依然篤信光的存在,看似自我卻往往不小心成為別人的療癒者,除了睡飽飽與永遠美麗之外的心願是靈魂永遠保有純粹,保有內心真正的強大。
在醫學教育裡面,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問。提倡者認為透過非數據化、非專業化的敘事,才能貼近病人的主觀經驗,拾起這門行業某些古老而幾乎被遺棄的本質。因此年輕醫師的寫作格外重要。
本書透過文字,我們在進入專業化的領域之前,試圖重新理解病人到底經歷到了什麼、感受了什麼,那是超越檢驗數據與醫學影像的更深邃的世界。
章節試閱
存在主義的安慰
那只粉色的小行李箱羞怯地躲在她的床邊,目測不超過十八吋,幾位兒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圍繞著她,吱吱喳喳問道:「妳怎麼有個這麼可愛的行李箱啊?這個行李箱小到連離家出走所需的家當都塞不下吧?」
她沉默,一頭褐色長髮披散在小麥色的肩上,脂粉不施的臉蛋透出十六歲少女才有的細嫩光滑。如此突兀的存在。幾乎以為她是誤闖加護病房的逃家少女。她應該在陽光下。
妳凝視著她,眼中隱約有另一張臉交疊在她臉上。是妳在精神科的primary care。相同身高、體重、膚色。在她抬起頭還來得及與妳相視之前,妳趕緊低下頭。這...
那只粉色的小行李箱羞怯地躲在她的床邊,目測不超過十八吋,幾位兒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圍繞著她,吱吱喳喳問道:「妳怎麼有個這麼可愛的行李箱啊?這個行李箱小到連離家出走所需的家當都塞不下吧?」
她沉默,一頭褐色長髮披散在小麥色的肩上,脂粉不施的臉蛋透出十六歲少女才有的細嫩光滑。如此突兀的存在。幾乎以為她是誤闖加護病房的逃家少女。她應該在陽光下。
妳凝視著她,眼中隱約有另一張臉交疊在她臉上。是妳在精神科的primary care。相同身高、體重、膚色。在她抬起頭還來得及與妳相視之前,妳趕緊低下頭。這...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給下一輪年輕醫師的備忘錄 阿布
拿到學妹《咬子彈的女人》書稿時,是2021年的七月,我一邊讓年輕醫師用文字帶著我走過各科,一面回想,我也曾經在清晨查房時、在值班的夜裡,匆匆走過醫院的長廊,穿梭在不同科別的護理站與護理站之間,穿梭在疾病與疾病之間。那已經是正好十年前,2011年的事了。
目前為止,醫界一直不缺後來者。年輕人前仆後繼的進入這門古老的職業,有時候我幾乎已經忘記我當初第一次踏入醫院時的心情了,只能從年輕醫師的惶惶神情中找到一點回憶的線索。而現在我留在我成長的醫學中心,承接起當年教導我的資深醫...
拿到學妹《咬子彈的女人》書稿時,是2021年的七月,我一邊讓年輕醫師用文字帶著我走過各科,一面回想,我也曾經在清晨查房時、在值班的夜裡,匆匆走過醫院的長廊,穿梭在不同科別的護理站與護理站之間,穿梭在疾病與疾病之間。那已經是正好十年前,2011年的事了。
目前為止,醫界一直不缺後來者。年輕人前仆後繼的進入這門古老的職業,有時候我幾乎已經忘記我當初第一次踏入醫院時的心情了,只能從年輕醫師的惶惶神情中找到一點回憶的線索。而現在我留在我成長的醫學中心,承接起當年教導我的資深醫...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To Pain
妳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那個沒有止痛針的年代,將士們在戰場上只能咬著與其肉身一樣殘缺的子彈,忍痛亦步亦趨(也許只是與死神一步之距)。
止痛藥的發明,是普羅米修斯1盜給希波克拉特斯2的火薪,自此畫下無痛時代的開端。語至此處,妳那雙陰柔純真的深眸波瀾不驚。
無痛,是這世代最美的白色謊言,亦如永恆。如果蘇珊桑塔格3還在世,她將看到這個世紀疾病的隱喻4已經被消弭,被瀰天漫地的白覆蓋。
身陷無痛世代,妳不斷的重複著這謊言,對著那些受苦的臥床者,亦對著自己。
第一部分,妳躲在病人背後,剖著他們的情...
妳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那個沒有止痛針的年代,將士們在戰場上只能咬著與其肉身一樣殘缺的子彈,忍痛亦步亦趨(也許只是與死神一步之距)。
止痛藥的發明,是普羅米修斯1盜給希波克拉特斯2的火薪,自此畫下無痛時代的開端。語至此處,妳那雙陰柔純真的深眸波瀾不驚。
無痛,是這世代最美的白色謊言,亦如永恆。如果蘇珊桑塔格3還在世,她將看到這個世紀疾病的隱喻4已經被消弭,被瀰天漫地的白覆蓋。
身陷無痛世代,妳不斷的重複著這謊言,對著那些受苦的臥床者,亦對著自己。
第一部分,妳躲在病人背後,剖著他們的情...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 給下一輪年輕醫師的備忘錄 阿布 6
自序 To Pain 8
輯一: 豔陽下的戰壕冷影 11
蜂的微笑(胸腔內科) 12
亡目(胃腸內科) 16
光與影(一般內科) 21
藏(心臟內科) 24
衣櫃打開之後(感染內科) 27
日光走廊(腎臟內科) 31
繩索之下(心臟加護病房) 38
實與虛的距離 (肝膽外科) 43
蛻(胃腸外科) 47
形的謬論(心臟外科) 50
遺族(神經外科) 54
凝視的逃避(婦產科) 57
失樂園(小兒中重症病房) 61
占有(小兒神經) 64
旁觀者(小兒加護病房) 67
存在主義的安慰 (小兒免疫) 70
陪病人(眼...
自序 To Pain 8
輯一: 豔陽下的戰壕冷影 11
蜂的微笑(胸腔內科) 12
亡目(胃腸內科) 16
光與影(一般內科) 21
藏(心臟內科) 24
衣櫃打開之後(感染內科) 27
日光走廊(腎臟內科) 31
繩索之下(心臟加護病房) 38
實與虛的距離 (肝膽外科) 43
蛻(胃腸外科) 47
形的謬論(心臟外科) 50
遺族(神經外科) 54
凝視的逃避(婦產科) 57
失樂園(小兒中重症病房) 61
占有(小兒神經) 64
旁觀者(小兒加護病房) 67
存在主義的安慰 (小兒免疫) 70
陪病人(眼...
顯示全部內容
咬子彈的女人 相關搜尋
體內針灸:第二冊(國際英文版)Styletubation: A Video Intubating Stylet Technique fo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大師教你太極養生功:男女老少皆可練,越練身體越年輕
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3萬冊暢銷經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
體內針灸:第一冊(國際英文版)
自律神經失調有救了:為何很多醫師都治不好?25年臨床經驗!權威名醫給你有效的治療對策
五十肩,一定治得好!:徐子恆用千例臨床經驗找出真正關鍵,教你如何重拾健康肩膀!
70%的人都有自律神經失調?!(經典暢銷版):自律神經不自律,就是生活失控的開始!
脂肪魔術師:增脂、減脂、補脂,雕刻完美曲線
腎臟超圖解:慢性發炎、免疫失調、腎病變,權威名醫教你看懂腎臟求救訊號,立即提升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