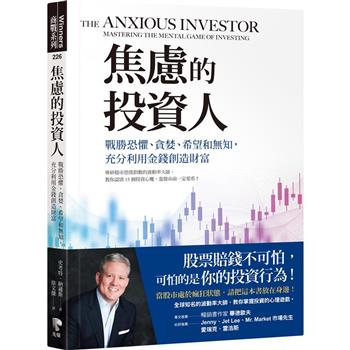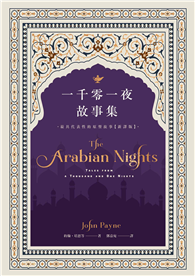窗邊起了陣騷動。傑佛瑞.逖區菲爾說:「啊,首相的車子到了。」他像個老僕,對主人崇拜得五體投地。接著走向門,陶醉在自己的話語裡,無心參與他的話引起的騷動。賓客面面相覷,互相確認,一、兩個人似乎已經舉棋投降,縮到角落,男賓客間有一小陣不太和善的推擠。
尼克跟著眾人移往樓梯口,心想首相肯定凡事要求完美,若沒有眾人夾道熱烈歡迎一定會生氣。他被擠在第一段樓梯的扶手上,微笑俯視,活像一幅歷史名畫中引人目光卻沒沒無名的隨從。前門敞開,外頭溼冷的空氣更添刺激。女賓哆嗦,又喜又憂。這夜晚是她們得群力打敗的乖張分子。「毒舌分析家」衝進來,差點兒跌倒,引起一片笑聲和咋舌聲。傑洛已經下了車,謙恭地跟特支部的人排成一列。瑞秋站在屋內,禮服的濛濛光澤和晶瑩銀彩讓她如有光環。耳邊傳來熟悉的聲音,一瞬間鴉雀無聲,接著她人出現。
她踩著優雅的快步走來,帶著一絲絲壓抑已久的羞澀和轉化成權力的愚拙。她引頸翹望,探進這陌生的房子,觸目所及無不定心凝神。高大的玄關鏡歡迎她到來,迎接者的面容有些縱使莊嚴卻超越了驕傲,有如狂喜,一時間既不顧一切又驚恐而羞澀。有眾人的歡迎她面露喜色,並雀躍而務實地平復情緒,就像現代的皇室。看不出來她是否注意到前門的顏色。
上樓之後氣氛恢復平靜,但不是普通的平靜,而是序曲結束,布幕升起,屏息以待的平靜。賓客重整心情。夫人走進房間時,大家自然而然列隊歡迎。她丈夫尾隨在後,低調地溜去找飲料和一名老友。首相過去握拜瑞.格魯的手時,他往後一跳,垂著頭低聲下氣;後來更傳言他甚至劈頭就說哈囉。她跟瓦利打招呼的方式很幽默,好像兩人才剛在別處碰過面似的。瓦利贏得青睞,但這麼快就得再跟她對話令他無法招架,不過緊緊握著她手的那一刻他看來就像要吻她一般。傑洛吃味地帶她繼續前進,低低報上賓客的名字。她走近時,尼克滿懷好奇地瞄著她。她儀態端莊,珠光寶氣,美麗超越了外在儀表。髮型無懈可擊,尼克不禁想像它溼答答垂下的模樣。她穿著黑色長裙,白金相間的寬肩外套,裝飾剪裁天衣無縫,有如夢幻國度的服飾,開低的前襟露出高貴的珍珠項鍊。尼克凝視著項鍊、挺立的豐滿胸部和為人母的圓胖頸部。「她真美。」楚笛.逖區菲爾看得出神,不知不覺地說。
傑洛很快介紹尼克,幾乎是在長長一句抑揚頓挫的社交語句中匆匆帶過,但卻有個出乎他意料的細節:說了小謊。「尼克.蓋斯特,我孩子很要好的朋友,年輕教員。」他感覺自己身價同時抬高又降低,因為教員並非最得首相青睞的人。他點頭微笑,感覺到她的藍色眼珠短暫而不放心地瞅著他,接著她逮到機會主動對約翰.提姆斯大喊:「約翰,哈囉!」提姆斯一眨眼站到他身旁說:「首相……」他雖沒跟首相握手,卻用他熱情討好的語調擁抱她。隊伍最後是主人一雙毫不相像、瞪大眼睛的兒女。陶比還是眉飛色舞,凱薩琳照例該要擺出臭臉或語出驚人,但卻反常地跟首相握手,開朗地說哈囉,像孩子盯著魔術師般盯著首相瞧。「噢,這位是我的男朋友。」她介紹賈斯伯,但忘了說他名字。首相道了聲哈囉,語調索然,暗示她該來杯酒了。眼神如鹿、笑容沉穩的特里斯道立刻呈上酒。
尼克快快提神後小跑下樓,剛好碰上瓦利從傑洛和瑞秋房裡走出來。「天啊,小心點兒,親愛的。」他說。
「我只是借廁所。」瓦利說。
「嗯。需要的話用我房間的。」尼克說,自己都醉醺醺暈陶陶,管不了那麼多。
「看樓梯。」瓦利說。
尼克喜歡古柯鹼如此揭開香檳、波爾多紅酒、索甸甜酒和更多香檳的面紗。它將點數加以總和,轉成另一個快感帳戶的信用點數,一切變得澄澈,如藥到病除一般:一開始簡直像神智清明。他搭著瓦利的肩,問他是否盡興。「我們好少碰到。」他說。兩人一起走下樓,第三或第四步時,尼克瞥見有人在瓦利剛剛走出的豪華白色臥房裡移動。他身為這房子的守護者及秩序維護者的直覺甦醒過來。賈斯伯走出門,一副手上握有房間鑰匙,只是帶買主參觀房子公事公辦的模樣。他對尼克點點頭、使了個眼色。「我到樓上小琳的房間。」他說。
「這樣。」尼克說。他和瓦利走下樓,一、兩步就若有所思、腳步遲疑,彷彿兩人會沉醉於共同的幻想中,而後停下腳步。「連在這裡你都要亂來。」
「多多益善,老弟,多多益善。」
「是啊!」尼克說,把輕蔑和反脣相譏吞了回去。他在瓦利紅得出奇的臉上尋找罪惡感,霎時洗牌似地瞥見兩人在浴室;瓦利對墮落的執迷、一切縱容隨著剛剛那劑白粉而逝。「所以那不再是我們之間的祕密了。」他說。瓦利看他的眼神嘲弄但不凶惡。尼克也許處在清明、機敏的階段,但瓦利更上一層樓,亢奮的情緒釋放而出並戛然而止,怔怔望著幾乎不認得的房間或朋友。尼克讓他走,古柯鹼導致心跳刺耳,讓他一瞬間慌了手腳。他防備地咪咪笑,但笑容似乎在搜尋並找到一個更陶然的目標,迎接藥效發揮。難以辨別什麼才是要緊的,此時此刻想這個當然毫無意義。外頭的大帳幕傳來音樂,到處充滿放縱狂歡的氣息。
他在客廳一角看見強第.史塔弗在跟凱薩琳調情,這名牙暴年邁的退休大使俯身圍住她,有如一隻快活的魔獸。「不,我想妳會喜歡杜不洛尼的,戴克里先飯店美妙極了。」他說道,還不忘拋個媚眼。
「噢。」凱薩琳說。
「他們每次都給我們結婚套房,妳知道,床都是最大的。裡頭任憑你愛怎麼玩。」
「想必您新婚之夜沒玩吧!」
「哈囉,強第先生。」
「啊,妳年輕俊美的愛慕者過來了。不成功便成仁!」強第爵士看見有女人臀部經過,又搖搖晃晃追上去,哪知剛好是首相。他猛然回身搖了搖頭:「太美了,你知道,首相……」
「看來妳被個喝得爛醉的老男人搭訕。」尼克說。
「被人看上還不賴。」凱薩琳說,倒進沙發。「知道賈斯伯在哪嗎?」
「沒看到。」尼克說。
攝影師四處跑,鏡子裡閃光燈亮晃晃。他輕手輕腳在賓客間徘徊,面帶笑容逼近,穿戴領結和晚禮服,像個你沒啥印象的討厭鬼,接著就砰一聲,照片到手!過一會兒他又改變主意踅回來,因為照片中人不是模糊不清就是剛好轉身,接著又一次把照片弄到手。此刻數名攝影師聚在一起對著他,或是假裝沒看到他,自以為瀟灑自若,神不知鬼不覺。尼克也倒進沙發,坐在凱薩琳身旁,一條腿盤起,咧嘴笑著自己的優雅神態。他覺得自己一整夜都能扮演自己。他感覺好極了,熱愛這樣的夜晚,以性作為壓軸雖好,但若落空似乎也無妨。沒有性再好不過。
「嗯,你身上好香。」凱薩琳說。
「噢,就是那瓶『我發誓』。」尼克說,對著她晃一晃袖釦。「妳去跟首相會見十二秒了嗎?」
「剛要去就被傑洛攔下來。」
「晚餐時我稍微聽到她說話。她有偉大人物那種既平易近人又自我中心的氣質。」
「真貪心。」凱薩琳說。
「大家都為之著迷,不約而同鬆了口氣,不斷討論植物性奶油和動物性奶油的事,沒想到她話鋒一轉,就開始談共同農業政策。」
「你沒表達意見。」
「還沒,她不太能自由行動,不覺得嗎?雖然是老大,卻得由人帶。」尼克說。
「在這裡她可不是老大。」凱薩琳說,大方示意特里斯道過來。「想喝什麼?」
「要什麼呢?來什麼好呢?」尼克說,用狡黠的笑容迎向特里斯道彬彬有禮的微笑,眼神飄往侍者的身體。
「香檳嗎?還是烈酒?」
「現在先香檳,待會兒再烈酒。」尼克懶洋洋地說。享樂的光景在他面前加深,藥物和酒精交相作用同心協力,危機感無來由增強安全感,多年之後他有自信可以對特里斯道為所欲為。特里斯道只點了個頭,但當他彎身斟酒時,匆匆且重重地往尼克的膝蓋一靠。尼克看著他走入人群,說短也長的那一時半刻,一切歷歷透澈,這裡,浩克斯伍,金光閃耀,鏡子,一間又一間房;心裡有個念頭一閃而過,只抓住尾巴:它獨自走向你,正是你夢寐以求。追逐不過就是一種永無止盡的等待。傑洛說的沒錯:統統都該有獎。特里斯道走回來,俯身把托盤送向他們時,尼克擎起一杯酒,既坦蕩又神祕地乾杯。「敬我們。」他說。
「敬我們。別跟那名侍者眉來眼去了。」凱薩琳說。
不久她又說:「費登今天晚上看來挺活躍的,還真不像他。」兩人舉目而望,看見陶比臥在首相坐的那張沙發上,正說著無法想像的笑話。首相身旁寬敞凹陷的椅墊是接見處,訴求的人傾吐個一、兩分鐘就被客客氣氣請走。不過,陶比藉由他餐後的精彩演說.可能可以待得比別人久。
尼克說:「瓦利給了他一點化學幫助,就算沒有我也不驚訝。」
「天啊。」凱薩琳不屑地說,但想一想又笑了出來。「你知道他這個人,準會呈上一杯喝的給她。」
「她可以喝的多的是,但對她好像都沒什麼效果。」
「看她在男人堆裡周旋真有趣。男人帶著老婆走過去,但看得出來太太角色尷尬。看看那一對,沒錯,握握手,說:『是,首相,是,是。』幾乎找不到時機介紹太太……表情擺明希望老婆滾開,好讓他跟夫人來個火熱約會——現在老婆非坐下不可,老公火大……但是,耶!她贏了,他蹲了下來……跪在地毯上。」
「說不定她會逼他吻她,呃……」
「噢,怎麼可能?」
「她的戒指,親愛的!」
「大概吧,很大的戒指。」
「她那身行頭頗有女皇架勢,不是嗎?」
「女皇?親愛的,她看起來像個西部鄉村歌手。」
凱薩琳尖叫一聲,或喜或怒程度不一的賓客紛紛轉過頭來。她長得就一副多愁善感的樣子,顫抖著手把酒杯舉在面前。「這些高腳杯還真大!」她說。
「是啊,簡直是大腳杯,不是嗎?」尼克說。
社區花園轟然響起煙火聲,震天價響,如雷貫耳。窗戶格格響,爆破聲在屋裡迴盪。大家興奮喊叫,聞聲畏縮,但首相文風不動,用堅實的音階鞏固她的聲音,彷彿挺身對抗鬧哄哄的國會,周圍的朝臣嚇得像雉雞一樣亂跳。
「其實我訝異的是男人的女皇情結,異性戀的女皇情結。」尼克說。
「這我可想而知。你知道,傑洛自己就……」凱薩琳說。
「親愛的,傑洛就像一身工作服的工人,跟這裡某些人比起來,傑洛就是上街抗議的礦工。看看那個老頭,他是什麼部長來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個某某『怖』長,恐怖的怖。看他臉紅成那樣。我在電視上看過他。」
他們說的是站在首相正後方的其中一個男人,他活像個馬戲團團長,對首相既保護又炫耀,不時用覬覦的眼神瞟著她的頭髮。他頭上的灰色鬈髮油亮往後梳成大波浪,手舉過頭,但極少碰到人。他是少數身穿白色晚禮服的隨從,擺出一副隨時隨地嚴正以待的姿態。外套翻領傾洩而下,乳白色絲綢滾邊;一整排閃亮的藍色西裝鈕釦上攀至低垂的正紫色天鵝絨領結。襯衫衣領讓他的頭定在一個孤傲的角度,緊身的絲綢腰帶讓他身體直挺,加深他臉上因消化不良泛起的紅光。
凱薩琳說:「我想稍微有點兒自尊的同性戀都不會穿成那樣。」
「噢,我不會那麼極端。」尼克說,不確定他和凱薩琳誰比較尖酸。「那只是虛榮。」
「親愛的,他是虛榮怖長!」凱薩琳又大叫一聲說。
尼克到一樓廁所快快吸了一管。偷偷摸摸跑去頂樓似乎不太必要。他用拇指輪流按住一邊鼻孔吸,看見傑洛跟雷根總統的握手照冷冷一笑。感覺上那老小子似乎連傑洛是誰都不知道,只見他一臉慈祥不慍不火。外頭的音樂砰砰響,剛剛是大編制爵士樂,現在換成了早期搖滾樂,就是瑞秋和傑洛二十五年前可想而知會隨之起舞的搖滾樂。煙火引爆呼嘯。上鎖的門外傳來熱鬧滾滾的宴樂聲,暗示著潛藏的機會:裡面有兩個男人他感興趣。門把格格響,他收拾、檢查、沖水,對著鏡子拉拉領結,信步走了出去,根本沒看見等在一旁的警員。
女伯爵佔去凱薩琳身旁的位置,他只好四下張望。擁擠的客廳就是他的遊樂場。他不自覺直往首相坐的沙發漫步而去。陶比像演員般走到邊廂,依舊笑咪咪,看不出來究竟從首相口中聽到什麼話。帕特瑞基夫人逗留不去,緊握著首相的手不放。她就像尼克看見景仰的作家一樣幾乎說不出話,最多只說得出「我喜歡你的書」。但此時此刻的情況是,儘管帕特瑞基夫人是個老婦人,智慧之痕和為人母親的驕傲仍然伴隨著如孩子般的敬畏和順從。尼克聽不清她在說什麼……什麼小問題?他很肯定帕特瑞基夫人也聽不見首相的話。但無所謂,兩人緊抓著彼此的手,致敬也好,治療也罷,對茱蒂是新奇刺激的體驗,對首相則是再熟悉不過的日常動作。兩人都醉茫茫,當她們把手前伸後拉並提高聲音時,幾乎像要爭辯起來。首相一副寧可爭辯的樣子,那可是她的專長。茱蒂撤身,躬身向後,全不看狀況;她擎起空的威士忌酒杯,猛力往虛榮「怖」長腿上一放。
對尼克來說輕而易舉。他走過去坐在沙發邊邊,半跪著,像演員在戲裡求婚一樣。他欣喜地凝視首相的臉龐、她的整顆頭、鷹鉤鼻、如冠頭飾,在他眼裡是漩渦派與巴洛克激盪出的細緻、甚至不可思議的融合體。她反射性地回以笑容,如光耀耀的藍色挑戰。那是溫柔燦爛的焰焰火光,一閃、再閃、三閃而逝,如光耀動的危機意識,火光在眼底波動有如一抹黑影,他的心跳加速,但毫不費力就咧嘴笑問:「首相,願意跳支舞嗎?」
「噢,非常樂意。」她用胸音說,女低音的允諾。身旁隨從暗自竊笑,聽見這始料未及的放肆要求不以為然。尼克與她穿過驚詫騷動的人群時,聽見整件事開始引發眾議,開創歷史,宴會重心眨眼轉移,這樣的效果無人能起,無人能擋。尼克居高臨下朝某個角度綻放笑容,不顧眾人眼光,專心一意聽著首相說話,還有自己大膽的精彩回答。其他人尾隨他們走下石階,穿過提燈打亮的步道,觀看、扮演著陪襯的角色。「教員邀舞很難得。」首相說。尼克發現傑洛錯了:她如魚得水,自得其樂,自有一套華美的觀看方式;她根本不甩壁紙的方格圖案或藍色的大門;她什麼都不留意,卻什麼都記得。
他們踏上拼花地板,隨著「走出我的生活」的節奏,大家稀疏而混亂地移動。傑洛與雙脣緊閉的珍妮.格魯跳波普;拜瑞顫巍巍擁著潘妮在舞池迴繞。瑞秋沉著地跟強第.史塔弗跳捷舞,一臉拋開禮儀的樣子。後來傑洛看見首相,他的偶像。之前首相說不跳舞,但現在幾杯威士忌下肚就紆尊降貴,跟尼克嫵媚地跳起舞來。尼克之前得自艾微森小姐調教的舞技全回來了,有如十二乘法表、輕快的步伐、握住上臂的輕輕力道一樣可得,只不過更加鮮活深刻,彷彿可以挽著在他懷中喘不過氣的首相跳個不停。但無論如何,傑洛中途出面阻止了。
他們三人上去尼克的浴室。瓦利又嚼又吸,幾乎顫抖起來,像生病一樣。他雙目圓睜面容憂鬱,全力衝刺而迷失了方向。他說自己沒事,再好不過了,集中精神攤開《閣樓論壇》四角,接著把白粉從女孩黑色陰毛小丘上刮落。尼克坐在浴缸邊、浴缸裡、斜著身體,雙腿掛在浴缸外,看著特里斯道尿了好久。
「別浪費。」瓦利說。這是他的小玩笑之一。
特里斯道輕笑了一聲說:「他愛開這種玩笑。」
「是啊!」尼克說。
「我知道在哪見過你了。」特里斯道說,照樣尿尿並按下沖水。洗手時,他對著鏡子說:「陶比先生的生日宴會,在那間豪華大房子。很久以前。」
「沒錯。」尼克說。他奮力站起來,脫下外套。特里斯道也脫下燕尾服,兩人彷彿說好了一樣。這種默契讓尼克微笑。
「你到廚房來找我,我以為你醉死了。」
「是嗎?」尼克含糊地說。
「後來我覺得很糟,因為我答應你待會兒見面,卻爽約了。」
「我們知道原因。」瓦利說。
「別擔心,我確定我也忘了。」尼克說。
特里斯道把一隻手放尼克肩上。尼克會過意,拿出皮夾給他二十鎊。特里斯道歪著頭,又長又厚的舌頭伸進尼克嘴裡,按部就班地吻了他十秒,接著伸出舌頭,轉過身。瓦利忙著集粉,沒注意到;特里斯道走去他背後打量。「我會惹上大麻煩。」他說。
「不會,安全得很,屋裡有警察防守。」
「我是指我老闆。就一下下,好嗎?」
「看看你喜不喜歡。」瓦利說,頭也不回就把手往侍者胯下摸。
「你需要多一點錢嗎?」尼克問。
「我剛剛才拿了他媽的五十塊給他。」瓦利扯嗓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特里斯道抽身,又照鏡子。他問:「你沒帶太太一起來?」
「他媽的,她又不是我太太,你這賤胚。」瓦利眉飛色舞地說。
特里斯道咧嘴對尼克笑,「我看見你跟夫人跳舞,跳來跳去。感覺她喜歡你。」
瓦利仰頭笑了一聲,「下次看見她,我要問問他對尼克的評價。」
「你們是好朋友?」特里斯道說,又對尼克咧嘴笑。
「他媽的好朋友。」瓦利說,輕輕拍著、瞅著他的成品。「非常好的朋友,好了……」他轉身凝視,「難道你不愛她嗎?不覺得她很美?」
特里斯道把臉一扯,「她還可以,對我來說。總之,人很多,錢很多,小費很多,幾百塊,兩百鎊。」
「天啊,賤貨。」瓦利說。
尼克走去洗手檯喝了兩杯水。「我需要來、一、下。」他低聲吟道。他們全都準備好了,迫不及待,分量充足讓他們心下踏實到簡直酥酥麻麻。這種感覺超越快感,自有一種動力,純粹的衝動,但卻讓他們誤以為自己有所選擇並做了明智抉擇。
特里斯道彎身吸一口,瓦利摸他老二,尼克摸他屁股。「好東西?你哪裡弄到的?」他說,往後站開,暫時抽身,狠狠一吸。
「朗尼給我的。他叫朗尼。啊,這樣好些——」瓦利說,捏著鼻孔。「我愛朗尼,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唯一的朋友。」
「除了首相之外。」尼克說。
特里斯道放肆冷笑,有人已經幫他做了許多決定。他說:「我以為他才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尼克。不是嗎?」
「尼克?他只是個妓男。他拿我的錢。」瓦利說。
尼克吸到一半回過頭說:「他的意思是說,他是我老闆。」不可或缺地擺出學究臉孔。
「不是說他負責幹人。」瓦利說。
「其實那是我的工作之一。」尼克莽撞地說。
「什麼?幹人?」特里斯道說,笑得像個傻瓜。
「反正,他是百萬富翁,所以……」尼克說。
「超過百萬。」瓦利說,似有若無地皺眉。「秀一下絕招吧!」
「什麼絕招?」尼克問。
「看就知道了。」瓦利說。
「希望嗑了藥不會讓我的老二軟趴趴。」特里斯道說。
「如果你的老二軟趴趴,我就他媽的把錢要回來。」瓦利說。
特里斯道把內外褲褪到膝蓋,坐上小小藤椅的扶手,黝黑的大屌懸著。他把手伸進襯衫往上推到肋骨,扭他的乳頭。「要幫我嗎?」他問。
瓦利啐了一口,走去站在他身後,把頭靠向前打量,一邊用食指和拇指揉捏、愛撫侍者的乳頭。特里斯道又嘆又笑,咬著他焦乾的嘴脣。他定眼俯視,彷彿看見自己的老二勃起,漲大,有氣無力地抽搐、聳至大腿,包皮稍微撐開時再羞紅含笑地自在搖擺,每次都令人驚嘆不已。「就是這樣。」瓦利說。
「就這樣?」尼克回道。
「你喜歡?」特里斯道說。那張臉在尼克眼裡霍然貪婪、陌生起來。他的陽具當然是今天晚上這奇怪的小場景潛藏的主旨,一個緩緩拖曳被人忽略最後又以一種愚蠢、強大的事實提起的主旨。尼克說:「這麼說你看過了?」
「噢,他每次都要。」特里斯道說。
瓦利屈膝跪下,笨手笨腳全心全意地投向他期待已久的事。他褲子已解開,但小小陽具因為藥效挾風帶電發作而低頭不舉,皺巴巴的,簡直躲躲藏藏。他恍了神,尊嚴全拋——這就是付錢的目的。他又舔又吸,鼻子不忘吸氣,閃耀的黏液摻雜了血液和未溶解的白粉,從他的鼻子流到侍者的大腿。侍者自己顯然從未試過,這危險的把戲是他從瓦利身上學來的。他開始講個不停,像跟朋友在一起。他對瓦利點頭說:「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陶比先生的宴會。他給我古柯鹼,我幹他屄固。」
「屄固?噢,屁股,我懂了。」尼克笑道,冷漠奇怪地混合了欣喜,雖然痛苦,對這傷人的事仍懷有某種敬意。他看著特里斯道把手伸進愛人的黑色鬈髮裡。做這個動作他往往輕鬆愉快、耐心、熟悉,彷彿瓦利沒在幫他口交,彷彿他是個被寵壞的漂亮孩子,在大人跟前團團轉,渴望也確信會獲得讚美。特里斯道摩娑著他的頭髮,咧嘴微笑並讚美他。「他給最多錢。」
「一定的!」尼克說,從口袋拿出一個保險套。
「來吧!」特里斯道說。
樓下,首相正要離去。傑洛跟她共舞了將近十分鐘。他不顧細雨,懷著溫熱的親密感和輕飄飄的成就感目送首相上車。煙火仍在釋放,有如槍砲,他們抬頭觀望。瑞秋站在門口,潘妮在她身後;傑洛搶先便衣警察一步,傾身向前關上車門,不由自主地開心鞠躬。雨絲在街燈下細細閃耀,戴姆勒賓士揚長而去,發出冒失嘆息似的聲音。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美的線條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5 |
二手中文書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美的線條
本書為英國二○○四年曼氏布克獎得主,也是英國布克獎成立36年來首度闖越性與權力禁區的精彩作品,藝文圈一致好評!
一九八三年夏天,正值青春年華的尼克.蓋斯特搬進費登家位於諾丁丘的豪宅閣樓。一家之主傑洛,費登是野心勃勃的新任保守黨議員,女主人瑞秋出身顯赫,夫婦膝下有陶比和凱薩琳一雙兒女。尼克就讀牛津時就對陶比傾心,但住進費登家後,跟風波不斷、叛逆任性、見解犀利的凱薩琳結為密友,並惶惶負起照顧凱薩琳的責任。
八零年代中期英國社會蓬勃發展,對政治和財富純真又無知的尼克一腳踏入費登家的世界,周旋於豪華盛宴、勾心鬥角、既滑稽也駭人的眾生百態之中。尼克在這一切充滿可能的時代裡,得以追求對美的執迷;對他而言,美的收穫就如同權力和財富對其友人一樣動人心魄。與任職於地方政府的一名黑人相戀讓他初藏愛情滋味,後來跟一名俊美的百萬富翁的戀情才讓他的生活產生巨變,也讓殘酷年代的虛妄幻想隨之浮現。
小說時間設於讓佘契爾夫人重握大權的兩次大選之際。書中呈現了歷經巨變和傷痛的四年。尼克與佘契爾夫人共舞的一幕最為膾炙人口。小說最後,潛藏暗湧的(同性戀)愛滋問題在貫穿前後的選戰之際赫然浮上台面,並意外成為(異性戀)政壇婚外情醜聞的擋箭牌;尼克也因為陰錯陽差捲入爆料案並成為醜聞主角,為寄人籬下的生活劃下句點。本書文字飽滿,情感豐沛,是數一數二的英語作家的重要著作。
章節試閱
窗邊起了陣騷動。傑佛瑞.逖區菲爾說:「啊,首相的車子到了。」他像個老僕,對主人崇拜得五體投地。接著走向門,陶醉在自己的話語裡,無心參與他的話引起的騷動。賓客面面相覷,互相確認,一、兩個人似乎已經舉棋投降,縮到角落,男賓客間有一小陣不太和善的推擠。尼克跟著眾人移往樓梯口,心想首相肯定凡事要求完美,若沒有眾人夾道熱烈歡迎一定會生氣。他被擠在第一段樓梯的扶手上,微笑俯視,活像一幅歷史名畫中引人目光卻沒沒無名的隨從。前門敞開,外頭溼冷的空氣更添刺激。女賓哆嗦,又喜又憂。這夜晚是她們得群力打敗的乖張分子。...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艾倫.霍林赫斯特 譯者: 謝佩妏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7-06-14 ISBN/ISSN:978986124874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46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