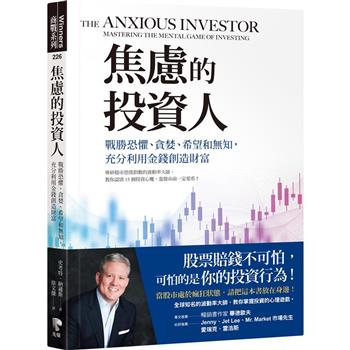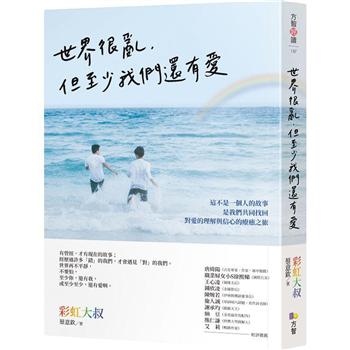愛因斯坦對浩瀚的宇宙吐舌頭,而馮內果則對荒謬的全人類扮鬼臉。
他花了七八十年,不厭其煩地跟我們說:
人類最最荒謬不過的行為,莫過於發動各種名義的衝突、對抗、戰爭,互相殘殺,來遂行他們花樣繁多的把戲。
他的所有嘲弄,都來自於對弱勢人們的「悲憫」。
反擊不公義,是他的良知;嘲弄則是他的智慧。
被公認為當代美國最好的作家之一,以《第五號屠宰場》知名於世界文壇的反戰文學大師──馮內果,在這本全新、從未發表、出版過的最後遺著中,再次以他最拿手的輕佻文字、幽默卻反諷的語氣和精采的素描與畫作,用他的真誠與悲憫態度,有力地陳述人類最嚴肅的課題。
終其一生,馮內果作為一位偉大、慈祥、人道主義、同情心的父親、作家、畫家、軍人、和平追求者,由其兒子馬克‧馮內果編輯此書,完成馮內果在世間所扮演的角色,留給讀者最好的美麗回憶。
馮內果在最後一篇演講稿說:「謝謝各位專心聽我說話,我要閃人了。」
兩週後,他不慎跌倒,撞到了頭,就此玩完了。
不過,故事還沒有結束……
本書不但呈現出馮內果這位作家暨畫家的才華,也充分反映出我們當前這個時代最需要聽到的聲音。
本書收入馮內果的十二篇從未發表、出版的最新遺作,其中包括短篇小說與散文,主題環繞著他生前最重視的兩項主題:戰爭與和平。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遍及他一生中的各個階段,但先前從未發表、出版過。在這些文章裡,可以看出馮內果堅決反對暴力的態度,也可看出他對人類不斷受到暴力吸引的現象深感沮喪。
本書收入的文章都帶有馮內果招牌的幽默,內容包羅廣泛,包括一篇栩栩如生的散文,記述德勒斯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摧毀的情形,今天看來仍然切中時弊;還有一篇令人笑中帶淚的短篇故事,講述三名士兵幻想著戰爭結束後回家要吃的第一道完美大餐;以及一篇寓意沉重的故事,談及我們難以保護孩子免於暴力的誘惑。
在馮內果透露著厭憎與內疚的真誠筆觸下,書中有三則戰俘故事都以描寫美國人的惡形惡狀為主題:〈學聰明點〉寫的是戰俘營裡的叛徒故事;〈戰利品〉敘述盟軍戰俘獲釋之後劫掠平民家戶的行為;〈就你和我,山姆〉則是其中最具野心的作品,是一則爾虞我詐的謀殺故事。透過這些文章,讀者可以深入洞悉馮內果身為軍人、作家、畫家、父親,以及和平追求者的各個面向。
這部文集還收入了馮內果告知家人自己曾遭德軍俘虜的一封信、他人生中的最後一篇演講稿、兒子馬克‧馮內果寫的引言,以及他令人嘆為觀止的素描與畫作。他的圖畫和著作一樣多采多姿又充滿驚奇,有時辛酸,有時又令人噴飯。
如同馬克.馮內果說的:「如果你對其中某些文章的內容不感興趣,也請看看其中的結構和韻律以及用字遣詞。你如果無法從他的文章裡獲得閱讀和寫作方面的洞見,那麼也許你不該浪費時間看他的書。」
所以,請各位繼續享受馮內果對世界發聲吧!
章節試閱
西元一○六七年,在英格蘭的高地史杜,十八具屍體在村莊的絞刑架上來回轉動著。吊死他們的是恐
怖羅伯,即征服者威廉的朋友。這幾具死屍雙眼凸出,沿著順時鐘方向緩緩轉動,北、東、南、西,
接著又回到朝北的方向。和善、貧窮、體貼的人都感到絕望。
絞刑架對街處,住著樵夫艾爾默和他的妻子艾薇,還有他們的十歲兒子厄索伯特。
艾爾默的小屋後面是一片森林。
艾爾默關上小屋的門,閉上眼睛,舐了舐嘴唇,只嚐到悔恨的味道。他和厄索伯特一起在餐桌旁坐了
下來。
由於恐怖羅伯的隨從突然造訪,他們的稀粥都放冷了。
艾薇的背緊貼著牆,彷彿上帝剛從她面前經過。她兩眼發光,呼吸急促。
厄索伯特目光呆滯地盯著眼前的冷粥,腦袋裡盤桓著家族悲劇。
「啊,恐怖羅伯騎在馬上,看起來是不是很高貴呢?」艾薇說:「鐵甲漆得五顏六色,還有羽毛,馬
身上的披巾又是那麼漂亮。」她掀動自己身上的破舊衣服,像女皇一樣昂著頭,聽著諾曼人的馬蹄聲
漸漸遠去。
「是很高貴沒錯,」艾爾默說。他身材矮小,頭卻很大。一雙藍色的眼睛因為剛剛收到的壞消息而透
露出焦躁不安。他瘦小的骨架上可見到一條條結實的肌肉,是斯文人不得不勞動而留下的痕跡。「他
只能用高貴兩字形容,」他說。
「你愛怎麼說諾曼人,隨你,」艾薇說:「反正他們真的把英格蘭的格調提高了不少。」
「我們也付出代價了,」艾爾默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他把手指伸進厄索伯特那頭濃密的淡
黃色頭髮,把他的頭往後一仰,看看他眼中有沒有生氣。不過,眼睛裡映照出來的卻是他自己困惑不
安的心靈。
「鄰居一定都看到了恐怖羅伯在我們前門高聲咆哮,,」艾薇得意地說:「等他們聽到他派了隨從把
你任命為稅吏,該有多麼驚訝哪。」
艾爾默搖搖頭,鬆弛的嘴唇隨之顫動。他原本因為自己的智慧與溫和而受人喜愛,現在卻必須代表恐
怖羅伯的貪婪,如果不接受,就別想活命。
「我真想用他那匹馬身上的披巾做一件衣服,」艾薇說:「藍色的,上面還布滿了一個個小十字架。
」這是她一生中首次感到快樂。「我會做成隨興的風格,」她說:「後面全部皺在一起,拖在地上,
可是其實是精心設計的結果。等我有了幾件好衣服,說不定我也可以學點法語,和那些諾曼女士聊聊
天。她們那麼優雅。」
艾爾默嘆了口氣,雙手緊握兒子的手。厄索伯特的手很粗糙,手掌都是繭,毛孔和指甲底下也都塞滿
了泥土。艾爾默撫摸著他指尖的一道割痕。「這是怎麼來的?」他問。
「做陷阱受傷的,」厄索伯特說。他整個人活了起來,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我在坑洞上鋪了荊棘,
」他熱切地說:「這樣獨角獸只要跌進去,荊棘就會掉在牠身上。」
「這樣應該可以逮到牠了,」艾爾默的語氣很溫柔。「英格蘭可沒幾戶人家有機會吃一頓獨角獸大餐
呢。」
「我希望你能到森林裡來看看陷阱,」厄索伯特說:「我想確定陷阱做得沒有問題。」
「我相信你的陷阱一定很棒,我也很想看,」艾爾默說。在這對父子平淡乏味的生活中,捕捉獨角獸
的夢想就像一片灰布上的一條金線。
他們兩人都知道英格蘭根本沒有獨角獸,但他們刻意活在這種虛假的信念裡──彷彿獨角獸真的存在
,彷彿有一天厄索伯特真的會抓到一隻,彷彿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在不久之後就會有吃不完的肉,還
能把珍貴的角變賣,換得一大筆錢,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說你要來看,已經說了一年了,」厄索伯特說。
「我太忙了,」艾爾默說。他不想去看那個陷阱,不想面對現實。那個陷阱只不過是地上的一個小洞
,上面鋪了幾根樹枝,只因為男孩的想像力而成為推動希望的一股巨大力量。艾爾默只想繼續在腦海
中想像著那個陷阱有多麼宏偉,多麼大有可為,因為除此之外,生活中再也沒有其他希望了。
艾爾默親吻兒子的雙手,嗅了嗅肌膚與泥土混雜的氣味。「我很快就會找時間去看看,」他說。
「做了衣服之後,剩下的披巾還夠幫你和厄索伯特做幾件內褲,」艾薇說,仍然沉浸在那股興奮情緒
中。「到時候你們兩個可神氣了,穿著上面滿是金色十字架的藍色內褲。」
「艾薇,」艾爾默耐著性子說:「希望你想清楚──羅伯真的很恐怖。他不可能把馬兒身上的披巾給
你,他從來不曾給過任何人任何東西。」
「只要我願意,我當然可以做做白日夢,」艾薇說:「這應該是女人的特權吧。」
「做什麼白日夢?」艾爾默說。
「如果你表現得好,他說不定會在披巾舊了之後,把它送給我,」艾薇說:「而且,如果你收的稅金
多得超過他們的想像,說不定他們偶爾會邀請我們到城堡去作客。」她在小屋裡走來走去,賣弄風情
,一手拎著想像中的裙襬。「找安,先生,女士,」她嘟嘴捲舌,模仿法語的發音。接著又說:「相
信各位大人和女士身體都健康。」
「這就是你的夢想嗎?」艾爾默問道,震驚不已。
「然後他們還會賜給你一個響亮的名號,像是血腥艾爾默或瘋狂艾爾默之類的,」艾薇說:「而且你
和我和厄索伯特也會每週騎馬上教堂,打扮得光鮮亮麗。如果有哪個老農奴對我們說話不夠恭敬,我
們就痛打他──」
「艾薇!」艾爾默高聲打斷了她的話:「我們就是農奴啊。」
艾薇踏著腳,緩緩地搖頭。「恐怖羅伯不是才剛給了我們上進的機會嗎?」
「變得像他一樣可惡?」艾爾默說:「這樣叫做上進嗎?」
艾薇在餐桌旁坐了下來,雙腿擱在桌上。「一個人如果生在統治階級裡,身不由己,」她說:「那他
就必須好好管理百姓,要不然百姓就再也不會把政府當一回事了。」她優雅地抓了抓癢。「老百姓就
是要有人管。」
「真不幸,」艾爾默說。
「老百姓需要有人保護,」艾薇說:「裝甲和城堡也不便宜。」
艾爾默揉了揉眼睛。「艾薇,你能不能告訴我,還有什麼比我們的政府更差勁?」他說:「我還真想
看看,然後再決定到底哪個東西比較可怕。」
艾薇沒有聽他說話。她因為聽到愈來愈響亮的馬蹄聲而興奮不已。恐怖羅伯和他的隨從在返回城堡的
路上又經過了他們家,小屋也在權勢與光榮中微微顫動著。
艾薇衝到門前,打開了門。
艾爾默與厄索伯特低下了頭。
諾曼人發出驚喜的歡呼聲。
「呀!」
「看!」
「勇士們,快追!」
諾曼人的馬匹立起來,向前一躍,奔進了森林裡。
「有什麼好消息?」艾爾默問:「他們踏扁了什麼東西嗎?」
「他們看到了一頭鹿!」艾薇說:「他們都追上去了,恐怖羅伯在前面領頭。她手撫著胸口。「他真
是身手矯健啊,對不對?」
「是啊,」艾爾默說:「願上帝賜給他強壯的右臂。」他望向厄索伯特,以為他會露出心照不宣的嘲
諷笑容。
不過,厄索伯特卻是面無血色,圓睜著眼。「陷阱──他們跑到陷阱那裡去了!」他說。
「他們如果敢碰你的陷阱,」艾爾默說:「我就──」他脖子上青筋暴起,雙手曲握成爪。恐怖羅伯
如果看到那個陷阱,可想而知一定會把男孩的心血毀掉。「只是好玩而已,只是好玩而已,」他咬牙
切齒地喃喃自語。
艾爾默想要幻想自己殺掉恐怖羅伯,但這樣的幻想卻和人生一樣令人沮喪,因為這樣等於是在沒有弱
點的地方找尋弱點。他幻想中的結局也和真實世界裡一樣,羅伯和他的手下騎在如同大教堂一樣高大
的馬匹上,身穿鐵甲,在頭盔的面甲後方哈哈大笑,好整以暇地挑選著叉子、鐵鍊、鐵鎚、剁肉刀等
各種武器,決定怎麼對付這個滿腔怒火、衣衫破舊的樵夫。
艾爾默的手癱軟了下來。「他們要是敢破壞陷阱,」他有氣無力地說:「我們就再搭造另一個陷阱,
造得比前一個還好。」
艾爾默對自己的軟弱感到羞愧不已,並且因此覺得一陣頭暈目眩。他的手臂擱在桌上,把頭靠在手臂
上。一會兒之後,他才抬起頭來,卻像骷髏頭一樣咧著嘴笑,一面左顧右盼。他已經度過了崩潰的臨
界點。
「爸爸!你還好嗎?」厄索伯特說,語氣中充滿了驚恐。
艾爾默顫抖著站起身來。「很好,」他說:「我很好。」
「你看起來和之前不太一樣,」厄索伯特說。
「我是不一樣了,沒錯,」艾爾默說:「我再也不怕了。」他抓住桌沿,大吼一聲:「我不怕了!」
「小聲點,」艾薇說:「他們會聽到的。」
「我才不要小聲點!」艾爾默激動地說。
「你最好小聲一點,」艾薇說:「你知道恐怖羅伯會怎麼處置大聲嚷嚷的人。」
「沒錯,」艾爾默說:「他會把帽子釘在他們頭上。不過,如果我得付出這樣的代價,那也沒關係。
」他雙眼朝上一翻。「我一想到恐怖羅伯破壞孩子的陷阱,人生的真諦就突然閃過了我的眼前!」
「爸,你聽我說──我不怕他破壞我的陷阱。我只怕──」
「閃過了我眼前!」艾爾默大吼。
「喔,拜託,」艾薇不耐煩地說,一面關上了門。「好吧,好吧,好吧,」她嘆了一口氣。「就來聽
聽你閃過眼前的人生真諦吧。」
厄索伯特扯著父親的袖子。「如果你問我的話,」他說:「那個陷阱其實──」
「破壞者與建造者的對抗!」艾爾默說:「那就是人生的真諦!」
厄索伯特一面搖頭,一面自言自語:「他的馬如果踏到那條繩子,就會牽動樹苗,然後──」他抿著
嘴唇。
「你說完了嗎,艾爾默?」艾薇說:「就這樣而已嗎?」她滿心只想再回去觀看那群諾曼人。艾爾默
不禁怒火中燒。他碰觸門把。
「沒有,艾薇,」艾爾默咬著牙說:「我還沒講完。」他一掌把她的手從門把上打掉。
「你居然打我,」艾薇驚詫不已。
「你每天都把門開著!」艾爾默吼道:「我真希望我們沒有門!你整天什麼都不做,就只會坐在門前
,看著犯人被處死,看著諾曼人經過。」他的手在她面前顫抖著。「難怪你腦袋裡只有一堆光榮和暴
力的怪念頭!」
艾薇嚇得縮成一團。「我只是看看而已,」她說:「我一個人會寂寞,看那些東西可以讓時間過得快
一點。」
「你看得太久了!」艾爾默說:「我還有其他消息要告訴你。」
「什麼?」艾薇膽怯地問。
艾爾默挺了挺他瘦小的肩膀。「艾薇,」他說:「我不當恐怖羅伯的稅吏。」
艾薇倒抽了一口氣。
「我不幫助劫掠者,」艾爾默說:「我兒子和我都是建造者。」
「你不當稅吏,他會把你吊死的,」艾薇說:「他說他一定會這麼做。」
「我知道,」艾爾默說:「我知道。」他還沒感受到恐懼。疼痛也還沒出現。他只覺得自己總算做了
一件理想的事,只覺得自己嚐到了一口冰涼純淨的泉水。
艾爾默把門打開。風變大了,死屍身上的鐵鍊也因而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風從森林裡吹來,傳來了
諾曼人狩獵的呼喊聲。
不知為什麼,他們的叫喊聲中充滿了惶恐和疑慮。艾爾默猜想這是距離造成的結果。
「羅伯?喂,聽得到嗎?羅伯?呀!喂,聽得到嗎?」
「喂,聽得到嗎?呀!羅伯。出個聲音好嗎,求求你。呀!呀!有沒有聽到?」
「喂,喂,聽得到嗎?羅伯?恐怖羅伯?呀!喂,喂,聽得到嗎?」
艾薇從身後抱住了艾爾默,臉頰貼在他的背上。「艾爾默,親愛的,」她說:「我不要你被吊死。我
愛你,親愛的。」
艾爾默拍了拍她的手。「我也愛你,艾薇,」他說:「我會想念你的。」
「你真的要這麼做嗎?」艾薇說。
「時候到了,我應該為自己的信念而死,」艾爾默說:「就算這不是我的信念,我也必須這麼做。」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在兒子面前說了我會這麼做,」艾爾默說。厄索伯特走到他面前,艾爾默伸手抱住了男
孩。
他們三人擁抱在一起,在落日下前後晃動,隨著他們骨髓裡感受到的韻律搖晃著。
艾薇在艾爾默背後抽泣著。「你這樣只會教厄索伯特也一起走上死路,」她說:「他現在對諾曼人都
無禮得很。他們沒把他關進地牢就謝天謝地了。」
「我只希望厄索伯特這輩子也能像我一樣,有個這麼好的兒子,」艾爾默說。
「所有的事本來都很順利的,」艾薇說。她哭了出來。「你得到了這麼好的一個職務,可以藉著這個
機會往上爬,」她抽抽噎噎地說:「我本來還想,等到恐怖羅伯那匹馬身上的披巾舊了之後,說不定
你可以問問他──」
「艾薇!」艾爾默說:「別讓我更難過了。安慰我吧。」
「如果我早知你要做什麼,說不定事情會容易一點,」艾薇說。
兩名諾曼人從森林裡走出來,滿臉沮喪與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們彼此對望,攤開雙臂,聳了聳肩。
其中一人用腰刀撥開灌木叢,低頭看了看,一副無計可施的可憐樣。「喂,喂?」他說:「羅伯?」
「他不見了!」另一人說。
「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
「他的馬、他的鎧甲、他的羽毛──一轉眼就不見了!」
「唉!」
「真糟糕。」
他們看到了艾爾默一家人。「呀!」其中一人對艾爾默喊道:「你有沒有看到羅伯?」
「恐怖羅伯?」艾爾默問。
「對。」
「抱歉,」艾爾默說:「連他的影子都沒看到。」
「什麼?」
「我連他的人影都沒看到,」艾爾默說。
兩名諾曼人又對看了一眼,滿臉淒涼的神色。
「糟糕!」
「媽的!」
他們又慢慢返回森林裡。
「喂,喂,聽到沒有?」
「呀!羅伯!有沒有聽到?」
「爸!你聽!」厄索伯特興奮地叫道。
「噓,」艾爾默輕柔地說:「我在跟你媽說話。」
「就像那個愚蠢的獨角獸陷阱,」艾薇說:「我也不了解那個陷阱到底要幹麼。我一直很有耐心,從
來沒說過一句話。可是現在我要把心裡的想法說出來了。」
「說吧,」艾爾默說。
「那個陷阱一點用也沒有,」艾薇說。
艾爾默的眼眶盈滿了淚水。幾根樹枝、地上的小洞,還有男孩的想像力,這些就代表了他的一生──
即將畫下句點的一生。
「這裡根本沒有獨角獸,」艾薇說,對自己的見多識廣頗為得意。
「我知道,」艾爾默說:「厄索伯特和我都知道。」
「你慷慨赴義對現況也不會有什麼幫助,」艾薇說。
「我知道。厄索伯特和我也知道這一點,」艾爾默說。
「或許笨的人是我吧,」艾薇說。
艾爾默突然感到一陣恐懼和孤寂,還有即將隨之而來的痛苦,這是他堅持理想必須付出的代價。他想
品嚐冰涼純淨的泉水,就得付出這樣的代價。這種代價比羞辱還要痛苦百倍。
艾爾默嚥了一口口水。脖子上將會被絞繩勒住的地方傳來一陣疼痛。「艾薇,親愛的,」他說:「我
希望真是這樣。」
那天晚上,艾爾默祈禱艾薇能夠嫁個新丈夫,厄索伯特能夠有顆堅強的心,也祈禱自己能夠不受痛苦
而死,而且死後能夠上天堂。
「阿門,」艾爾默說。
「說不定你可以假裝當一下稅吏,」艾薇說。
「那我去哪裡生出假裝的稅金?」艾爾默問。
「說不定你當稅吏只要當一下下就好了,」艾薇說。
「即使只是一下下,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厭惡我,」艾爾默說:「然後我就可以走上黃泉路了。」
「總是有什麼辦法的,」艾薇說。她的鼻頭紅了起來。
「艾薇──」艾爾默說。
「嗯?」
「艾薇──我了解你為什麼想要布滿金色十字架的藍色洋裝,」艾爾默說:「我也希望能讓你過那樣
的生活。」
「還有你和厄索伯特的內褲,」艾薇說:「我不是只為了自己而已。」
「艾薇,」艾爾默說:「我要做的事,比馬身上的那些披巾都還重要。」
「這就是我的疑問,」艾薇說:「我實在想像不到有什麼會比那些披巾更了不起。」
「我也一樣,」艾爾默說:「可是那樣的事物確實存在,那樣的事物必須存在。」他露出一抹哀傷的
微笑。「不論那些事物是什麼,我明天在天國裡歡欣鼓舞,就是為了它們。」
「我希望厄索伯特趕快回來,」艾薇說:「我們全家應該團聚在一起。」
「他必須檢查他的陷阱,」艾爾默說:「日子還是得過下去。」
「真高興那些諾曼人回去了,」艾薇說:「他們滿口法語,我聽得都快發瘋了。我想他們應該找到恐
怖羅伯了吧。」
「那我就注定要賠上一條命了,」艾爾默嘆了一口氣。「我去找厄索伯特,」他說:「在人生的最後
一夜,還有什麼事比從森林裡把兒子帶回家更有意義?」
艾爾默走進夜色裡,天上掛著一輪彎月,周遭的景物都染上一抹淡淡的藍色。他循著厄索伯特走過的
小徑走到森林邊緣,望著面前那片由林木形成的黑暗高牆。
「厄索伯特!」他喊道。
沒有人回答。
艾爾默撥開枝葉,走進森林裡。樹枝劃過他的臉,刺藤絆著他的腿。
「厄索伯特!」
只有絞刑架回應著他的呼喊。鐵鍊嘎嘎作響,骷髏摩擦著地面。絞刑架上的八個欄位只吊了七具死屍
,還有空間可以再吊死一個人。
艾爾默愈來愈焦急,不斷往森林深處走去。他來到一片林間空地,停下腳步,喘著氣,汗水刺痛眼睛
。
「厄索伯特!」
「爸,是你嗎?」前方的灌木叢裡傳來厄索伯特的聲音。「快來幫我。」
艾爾默盲目地闖入灌木叢裡,兩手不斷撥開枝葉。
厄索伯特在一片漆黑中抓住了父親的手。「小心!」他說:「再走一步,你就會跌進陷阱裡了。」
「喔,」艾爾默說:「好險。」為了討兒子歡心,他故意顫抖著聲音。「唔──,真可怕!」
厄索伯特把他的手往下拉,壓到地上的一個東西。
艾爾默吃了一驚,發現手掌摸到的竟是一頭大公鹿。他蹲了下來。「一頭鹿!」他說。
他的聲音迴盪在四周,彷彿發自大地的深處。「一頭鹿、一頭鹿、一頭鹿。」
「我花了一個小時,才把牠拖出陷阱,」厄索伯特說。
「陷阱、陷阱、陷阱,」回音在他們身邊蕩漾著。
「真的嗎?」艾爾默說:「好樣的,兒子!我沒想到你的陷阱做得這麼棒!」
「這麼棒、這麼棒、這麼棒。」
「你不知道的可多了呢,」厄索伯特說。
「可多了呢、可多了呢、可多了呢。」
「那回音是從哪來的?」艾爾默問。
「從哪來的、從哪來的、從哪來的?」
「從你前面來的,」厄索伯特說:「就是你面前的陷阱。」
艾爾默不禁往後一跳,只聽到厄索伯特的聲音從面前的大洞裡迴盪而出,彷彿來自地底,來自地獄的
大門。
「陷阱、陷阱、陷阱。」
「你挖了這麼大一個洞?」艾爾默難以置信。
「上帝挖的,」厄索伯特說:「這是一個洞穴上方的裂口。」
艾爾默癱軟在地。他把頭枕在公鹿冰冷僵硬的後腿上。灌木叢濃密的枝葉間只有一道細縫,正好可以
看見夜空裡一顆明亮的星星。艾爾默眼裡盈滿了感恩的淚水,淚光閃爍,只見星星化成了一道彩虹。
「我這一生別無所求了,」艾爾默說:「今天晚上,上帝已經把一切都賜給了我,而且還比我要求的
多得多、更多、更多。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兒子捕到了一頭獨角獸。」他伸手摸著厄索伯特的腳,輕
撫著他的腳背。「連微不足道的樵夫父子的祈禱,上帝都願意聆聽,那世界上還有什麼理想不能實現
呢?」
艾爾默差點沉入了夢鄉。他只覺得自己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
厄索伯特喚醒了他。「我們是不是該把這頭公鹿抬回去給媽?」厄索伯特說:「來一頓午夜大餐?」
「不能把整頭鹿抬回去,」艾爾默說:「這樣太冒險了。我們切下幾塊比較好吃的部位,剩下的先藏
在這裡。」
「你有刀子嗎?」厄索伯特問。
「沒有,」艾爾默說:「那是違禁品,你應該知道吧?」
「我去找個東西來割肉,」厄索伯特說。
艾爾默仍然躺在地上,聽著他兒子從裂口爬下地底洞穴,聽著他愈爬愈深,聽他奮力搬動著洞穴裡的
木材。
厄索伯特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一個長長的東西,映照著星星的光芒。「這個應該就可以了,」他說
。
他把那東西交到艾爾默手上。那是恐怖羅伯沉重鋒利的大腰刀。
午夜。
這一家人吃了滿肚子的鹿肉。
艾爾默用恐怖羅伯的短刀剔著牙縫。
厄索伯特在門口把風,拿羽毛擦了擦嘴唇。
艾薇心滿意足地在身前攤開了馬匹的披巾。「我要是知道你捕得到東西,」她說:「就不會瞧不起那
個陷阱了。」
「陷阱就是這樣,」艾爾默說。他仰靠在椅背上。恐怖羅伯既然死了,他就不必擔心自己明天會被送
上絞刑架。他覺得自己應該為此感到興奮,但和他腦袋裡其他各式各樣的念頭相較之下,撿回一條命
顯然只是件小事罷了。
「我只有一件事要說,」艾薇說。
「說吧,」艾爾默顯得志得意滿。
「我希望你們兩個不要再把我當成笨蛋了。你們一直說這是獨角獸的肉,難道你們以為隨便說什麼我
都會信嗎?」
「這是獨角獸的肉啊,」艾爾默說:「我還要告訴你一件可以相信的事情。」他套上恐怖羅伯的鐵甲
手套,然後用手指輕叩著桌面。「艾薇,小人物也有出頭的一天。」
艾薇以愛慕的眼神望著他。「你和厄索伯特真好,」她說:「還特別帶了衣服回來給我。」
遠處傳來了馬蹄聲。
「把東西藏起來!」厄索伯特說。
轉眼間,恐怖羅伯的遺物和鹿肉就都不見蹤影了。
全副武裝的諾曼武士從樵夫艾爾默毫不起眼的小屋前奔馳而過。他們對著夜裡無形的惡魔高聲大吼,
聲音中摻雜了恐懼和傲氣。
「呀!呀!鼓起勇氣,勇士們!」
馬蹄聲漸馳漸遠。
西元一○六七年,在英格蘭的高地史杜,十八具屍體在村莊的絞刑架上來回轉動著。吊死他們的是恐怖羅伯,即征服者威廉的朋友。這幾具死屍雙眼凸出,沿著順時鐘方向緩緩轉動,北、東、南、西,接著又回到朝北的方向。和善、貧窮、體貼的人都感到絕望。絞刑架對街處,住著樵夫艾爾默和他的妻子艾薇,還有他們的十歲兒子厄索伯特。艾爾默的小屋後面是一片森林。艾爾默關上小屋的門,閉上眼睛,舐了舐嘴唇,只嚐到悔恨的味道。他和厄索伯特一起在餐桌旁坐了下來。由於恐怖羅伯的隨從突然造訪,他們的稀粥都放冷了。艾薇的背緊貼著牆,彷彿上帝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