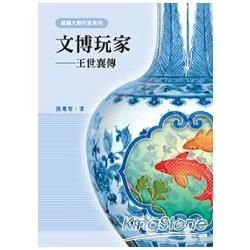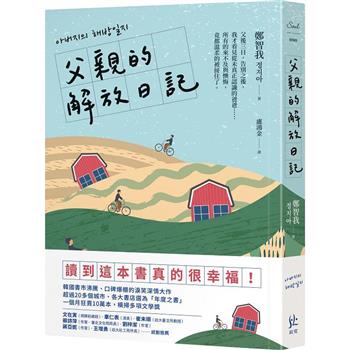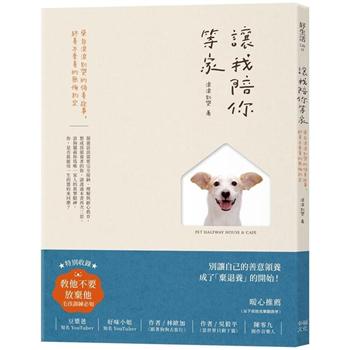序言
斯人已去,絕響誰繼∕張健智
奇人王世襄走了,永遠。今天是他的追思會,我未能趕往北京參加,只能在電腦螢幕上向他鞠禮致哀,如果按佛禮的話,還應點燃三支馨香從右至左向他磕頭,以讓他安靜地走入佛國仙境中去。一如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曾經說過的話,可讓王老與他老伴袁荃猷到極樂西天去了。
我想像著他們夫婦倆,現正在一團軟軟的白雲上作詩彈琴、聽蛐蛐蟈蟈唱歌、還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畫案上《說葫蘆》、《談匏器》,也正在欣賞那尊唐代的鎏金佛像、那皇宮裡才有的好鴿子「小點兒大胖子」的尾巴上,鴿哨正鳴著一連串最美妙的音樂和他們在一大朵藍天白雲上。而大奇人王世襄,正坐在《大樹圖》中最高的位置上,像一尊平生他最喜歡的佛像一樣莊嚴。(見袁荃猷刻紙《大樹圖》)
今年,大師們走了不少,季羨林、任繼愈、楊憲益,他們都到藍天白雲上去了,他們走的時候,有的人喜歡放音樂,如楊憲益先生在走去的路上,就放了他生前喜歡的洋音樂,詩人彭燕郊走去時,也放了首《送別》的曲子。我想,唯有王世老不必放洋的或古的音樂。因為,他日夜憧憬、呼籲那老北京曾經有的、滿天一陣陣飛翔的他最喜愛的銀鈴般的鴿哨聲,就會護著他。「鴿是和平禽,哨是和平音」(見《贈荷蘭傅立莎王子鴿哨附小詩》),老早有鴿與哨,一起伴著他飛入了雲天。
王世襄是個奇人,真走掉了嗎?我總有點不信。但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時二十二分,我的手機響起,一看是北京董秀玉先生來電,他告知噩耗:「王老於昨天清晨謝世!」這突來的信息,雖是任過堂堂三聯書店總經理所告知的,但於心理上一時讓我感到不能接受,總覺得以王世老之體魄,能挺過這一劫的。但隨後,卻讀到中央文史館正式訃聞: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王世襄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九時二十五分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歲。王世襄先生遺體已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火化。
這一刻,才感到王世老真走了││他,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人世間難料的變故,使我未能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了,啊,一時間心如刀絞,痛惜不絕矣!
董先生發來快訊的那晚,腦海中映射晃動的,依然是老人一年多前我與他訪談時的神清氣爽,談鋒甚健的話語;依然是樸素的中式大褂,敦厚壯實的中等身材,像老農般但又風規雅正的文人氣質。
與王世老神交,乃是緣於他是我的鄉前輩,他曾有詩說:「兒時依母南潯住,到老鄉音脫口流,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仍半屬湖州。」但為這多年前寫的詩,他還專門寫了一段自嘲的話:「晉魏時,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後果貴。可襄一生坎坷,有負宅相多矣。」二○○八年七月,王老又來信,特為此詩又作了更正,他說那「仍」字應改為「終」;還說「一字之改,意義可大矣!」的確,他對於慈母的老家,終念茲在茲。於是,我在拙作《王世襄傳》第二章〈江南金家〉第十三頁上,尊他意改詩為:「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終半屬湖州。」
其實,王世襄先祖,居江西吉水縣清江鄉,故人稱「西清王氏」。 後不知何故,也許出於商業上的需要,從江西遷徙福建定居。自五世祖時,由商賈入仕,高祖王慶雲(西元一七九八至一八六二年)終於在嘉慶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一九年)中得舉人,那時僅二十一歲,十年後又中得進士;後任兩廣總督,清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官至工部尚書。後祖父、伯祖、父親均為官一方。從此,王氏家族,以商習儒後入仕,遂成官宦之家。但王世襄外租——金家,卻是富甲一方的江南名鎮南潯的「四象八牛」之一。(當地形容家資在百萬兩銀至千萬兩的大族,稱其象和牛)其母金章,卻出身於江南富庶之地的湖州南潯,而王世襄兒時,卻隨母在外婆家居住;雖他居京九十多年,但他依然可講一口軟濃的江南吳語。王老平時喜歡回憶兒時生活,一次他俏皮地對我說:「我們王家祖上做官,後衰落了沒錢。可母親家有錢,外公(金泰)在南潯鎮,發了財的是他的父親(金桐),做蠶絲生意。外公雖未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這在當時是少有的。」確實是的,一九○二年,金氏兄妹(即王世襄母親金章)漂洋過海,歷時五載,後來他們兄妹幾人學成回國,或畫或刻,卓有成就。時屬清末,一個小鎮上十六歲的小女子,能去英國留學,實屬罕見。爾後,王世襄的母親金章(號陶陶)受中西畫薰陶,成了著名的魚藻畫家;大舅金北樓,曾是二十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袖人物,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表兄金開藩、金勤伯也是有名的畫家。真可謂一門藝術世家。王老說「我幼年立幾案,觀諸舅父作畫刻竹,情景猶歷歷在目也」這足可見其外祖家,對他一生成就的影響。
王世襄是大家,這不用我說,是天下第一大玩家,這也不用我說。「蛐蛐蟈蟈雖細物,令人長憶舊京華」曾是「燕市少年」。他少年及長,架大鷹、養狗獵獾、養蛐蛐、養鴿、種花草、養魚鳥;一九三四年,時二十一歲,入燕大,四年後的一九三八年又考進研究生,他選擇的專業是自小就受母親薰陶的書畫。畢業論文是《中國畫論研究》。抗戰後,到四川李莊,入梁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於此,走入了古文物研究之路。一如邵燕祥先生所概括
王老厚積薄發,堪稱淵博,而他所做學問,不知是否前無古人,看來是後無來者的。因為時逢前現代與現代轉型之際,因出身書香門第,深受傳統文化薰陶,又經燕京大學沐歐風美雨。大自傳世鼎彝,下至蟋蟀家俱,研究起來自然別有眼光,非他人所能替代。王老淹通博物,固勿論矣,至其書法及詩詞的造詣,似尚未有足夠的重視,實應注意及之。
綜觀王世老一生,卓然大家,他是明式家俱收藏大家,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等,這些大家知道,都無須我述。
在這裡我想說的,是王世襄博學多才外;他卻還是一位難得的美食大家,被人稱為「烹調聖手」。汪曾祺說過這樣的話。「學人中真正精於烹調的,據我所知,當推北京王世襄。」黃苗子、郁風是同住芳嘉園的老鄰居老朋友,郁風曾說,「王世襄不但每天買菜是行家,哪家舖子能買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藝也是超一流。」這是人家說的,但我也有親聞目睹的事兒可一說。
記得二○○八年四月間,我赴京與他做訪談(同去幫我錄音、作版書的,有女兒張欣,那時她正在做博士論文),那日,早上去他家,我們相談到了中午十二時了,王世老還很健談,臨走他定要請我們吃飯。只見他老,坐著輪椅下電梯,到馬路就自已推著輪椅走。他指定是到王老家附近日壇公園東面,那家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當我們大家落座後,女服務員請他點菜時,令我驚詫的是,他卻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兜裡,拿出一張紙,原來是他早親手擬好之食單。那刻,他又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交代菜的做法。經理一見,如此的美食家,忙將大師傅喚來。只聽王老向廚師問道:「有鮮蘆筍嗎?不是罐頭的,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來一隻烤鴨,可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郫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聽著王老和廚師這一番對答,已令大家暗自歎服,同時也讓我知道,便是並不隨著餐廳的菜單來吃,而自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只求味純,並不求貴。一如汪曾祺、陸文夫、台灣的逯耀東等美食家,無不如此。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時的情景;艱難時刻也體現美食家形象,善待自己。他說曾在那裡採蓮蓬、吃蓮子,有一次,一氣買十四條公鱖魚,自創了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的美食菜餚。真可謂地上好吃的,當時,全在一個落難知識分子的食中了;創造了《幹校六記》、《牛棚日記》外的另一種錢鍾書、楊絳、陳白塵所不能道的景象。因為,有過了這般自然美味的吃味,這次我與他吃談時,王老時感菜餚的味道,總今不如昔矣。他說,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餚,但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卻又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那次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餐廳為吸引食客眼球,讓廚師現場將烤鴨片成薄片,但根據王老的傳統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連皮帶肉的,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裡,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的。烤鴨過後,端上的卻是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只見湯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已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菜式可加進你們的菜單裡去,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鮮美無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卻做出令人讚歎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耐人尋味。我總算親眼看到了王老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美食大家。
那日,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那最苦的幹校的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難忘的憤怨,反而只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不知是那種人生哲理的悟性,他卻從飲食之談,一掃往日多少坎坷愁緒、多少磨難。其實,如果我們細讀王老詩文,那一堆堆的《錦灰堆》裡,他早清楚地向我們坦露了秘密:他與夫人袁荃猷,歷經劫難後,遂決心走出一條自珍自愛之路││那就是,他要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幹成就,最後自會讓「世終漸識真吾」的。這便似有司馬遷著書立說之道。
這所謂的自珍之路,實源於一九四五年,抗戰後成立「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當年,由杭立武任主任委員、梁思成、馬衡任副主任委員。沈兼士任教育部駐京特派員兼清損會代表。王世襄任平津區助理代表。爾後,王世襄在國內為國家與民族,追回了許多被侵佔的國家文物,因全力以赴工作,共收回國家文物計六批,其中三批,都由故宮接收。計收回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兩百四十件。收購郭觶齋所藏瓷器。追還美軍德士嘉定少尉瓷。收回存素堂絲繡兩百件。接收溥儀存天津張園文物一批,大小有一千多件(其中有宋馬和之《赤壁賦圖卷》、元鄧文原《章草卷》、元趙孟頫設色《秋郊飲馬圖卷》等)。一九四七年三月,王世襄被派往日本,又全心力追回了被日軍從香港掠去的一百零七箱中國古籍善本,古籍運回上海後,鄭振鐸派謝辰生在滬接收。可以說,這些價值連城的國家典寶被追回,將是有大功於國家與人民的。但是,由於一貫的極左思潮,運動文化的不斷,王世襄這為國追文物之事,卻視為盜賊,竟無端繫獄,五七反右時,欲訴無門,卻又被打成右派。文革時「五七幹校」勞動期間,罹患肺疾,卻昂首抬頭,也只能作詩云:「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
於此,他與夫人袁荃猷遂訂「自珍、自愛、自強」之路。其實,這路,在我們幾十年風風雨雨、複雜紛繁的社會生活中,也並非易走。繫獄後,因純屬子虛烏有,放歸家門,但王世襄無故卻被開除公職,時夫人荃猷則鼓勵他:「我們一定要堅強!」一個人身處劣境時,能否堅強的道理,她更是一語中的:「堅強要有本錢,本錢就是自己必須清清白白,沒有違法行為,否則一旦被揭發,身敗名裂,怎還能堅強?!您有功無罪,竟被開除公職,處理不公在上級,因此我們完全具備堅強的條件。」是啊,荃猷一席話,令王世襄領悟到今後的人生之路,兩人必攜手共同走自珍之路。正是這一決定,讓他們兩人能樂觀地笑對坎坷、堅定信念、寵辱不驚。所以,王世襄晚年,在接受各大電視台採訪時,總愛說這樣的話:「一個人的人生之旅上,當遇到坎坷、冤曲時,有些人往往會走絕端,那就是有人想不通就走自殺,另外有的人,卻與對方硬拼,這兩條路都不對,不能走。所以我選擇「我走自已的另一種人生之路。」
我們說,楊憲益和夫人戴乃迭,他們不僅將上千萬字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作為主要譯者和執行主編,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近五十年。同樣的,王世老與夫人袁荃猷,也相濡如沫、不分日夜,共同拼摶,一起完成了近四十部大部頭著作。而且,這些成就大多是在八十歲進入高齡年邁時所完成,談何容易。當《明代家俱研究》無人能任畫結構線圖時,是袁荃猷自告奮勇、竭盡全力、從頭學起,為明式傢俱繪製了千餘幅線圖,使色不少。正是那一幅幅精密、細緻、美麗的線圖,才讓明代傢俱那簡練純樸、自然的造型結構,更為彰顯;而明代家俱那精心設計、雅而不俗、雕琢精細、攢鬥巧妙的花紋圖案,令世界驚歎。王世襄在八十一歲之際,因忙於校對《錦灰堆》書稿,一天起來忽然左眼失明,這之後荃猷擔心他用眼過甚,便更多代為校對文稿、抄錄詩句等工作都由夫人撐起。可以說,王世襄的成果,離不開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努力和艱苦,也是常人無法體會的;而支持她的動力,便是當年夫婦倆堅守的自珍精神。
「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已,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卑不亢,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苦,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這便是王世襄人生座右銘的不移信念。讀著王世襄的話,我想,古往今來成大家者,必如此對已矣。
當二○○三年,王世襄榮獲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獎時,夫人正逝世,王老痛不欲生,「蒙冤不白憤難舒,祇有茹辛苦著書,五十一年如一日,世人終漸識吾真。」今天我重讀之,令我痛徹心扉、潸然淚下。王世襄和袁荃猷五十八年的風雨同路,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歲月,多少大喜大悲,多少聚散離合,多少屈辱苦難,他們只是用相互理解,平實生活,共同的文化使命,使他們堅守自珍,沒有山盟海誓、沒有驚天動地,卻令世人永記。
今晚,當我撰此文時,又翻出他於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給我的信,是他端正的楷書所書:
建智:上周我去協和醫院,作兩次體檢,二次看結果,幸無大恙。從胸片看有局部肺炎,所以又照CT。證實後已服特效藥,因較輕,體溫正常。有點多痰,服藥後頗見效。唯醫生囑多休息。你撰襄傳,今後我仍會提供有關材料。前面的九章很好,寫得順暢。八十歲後,完全走「自珍之路」,所以往下寫就方便了。唯寫作很苦,謝謝你!匆此並祝文祺!
王世襄,二○○八,八月三十一日。
而二○○八年冬天來臨之際,筆者去北京看他時,他已在一所中醫院住院,後又聽說做著血透。那時,我多麼希望王老總會脫離病床,會重新站起來。後又聽王老三聯的老領導董秀玉先生曾在春節後,又於二○○九年初夏,曾去中醫院和協和醫院看他,只感到他老已很累了。看來,在人世間大地上,他的人生道路走得也夠真累了,因為,他生活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畢竟是一個多災多難、風雨飄泊的時代。可以想像出他老,以好動之性格,在病床這長長的日月裡,是多麼的寂寞啊!
但是,我想,王世襄在寂寥中,定在尋找著一種歸宿,那藝術與靈魂的雙重歸宿。他的所有著作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在中國與世界上,決不是一點微波細浪而已,他最大的遺產是人類工藝的生存與創新,以及他的博學、堅定和純真的個性。他構建的大雅大俗並能立足於世界文明之林的中國文化,是多麼的燦爛、優美與質樸。二○○三年十二月三日,荷蘭王子約翰.佛利蘇,專程到北京為八十九歲高齡的王世襄先生,頒發二○○三年「克勞斯的譽獎」,他獲得此獎項的原因在於,他的創造性研究,已經向世界證明:如果沒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國文化,還會處在被埋沒的狀態。我想,他在病塌上,在這寂寞的日子裡,心底定有許多尋思與無窮的回憶,我們但願他不是「壽則多辱」,走完那最後的一站人生之路。因為,對他來說,那大半輩子走的是一條坎坷的人生之路,當然,他對塵世的不幸和痛苦早有認識:「五十八年多禍患,苦中有樂更難忘。西山待我來歸日,共賞朝霞夕陽。」這便是他最後要交給世人的一顆最平靜之心。
王世老走了,永遠。但他的沉甸甸的幾十部大作仍長存人間,他的工藝創新成果、所帶動的一個產業鏈,他所有灑向人間的友誼也同將長存我們大地。寫完此文,已是三更,遙望北天,僅以此一紙悲痛悼文,以及王老喜愛的鴿子與美妙的哨音,一齊上路,入藍天白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