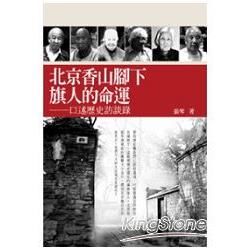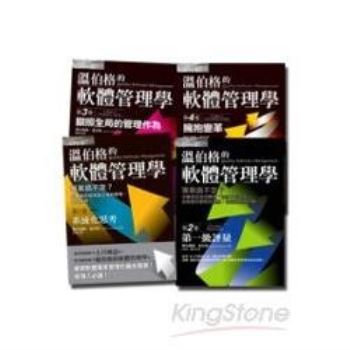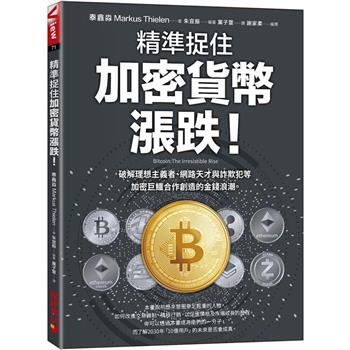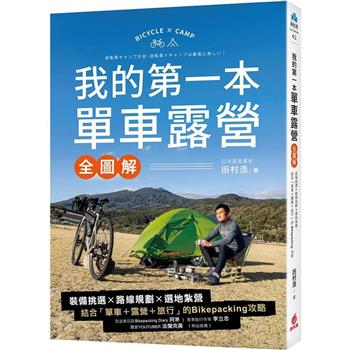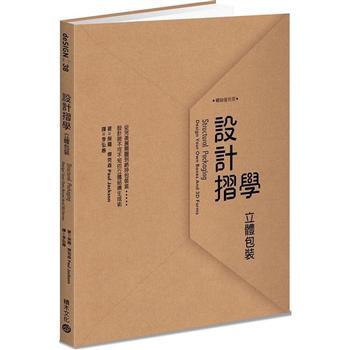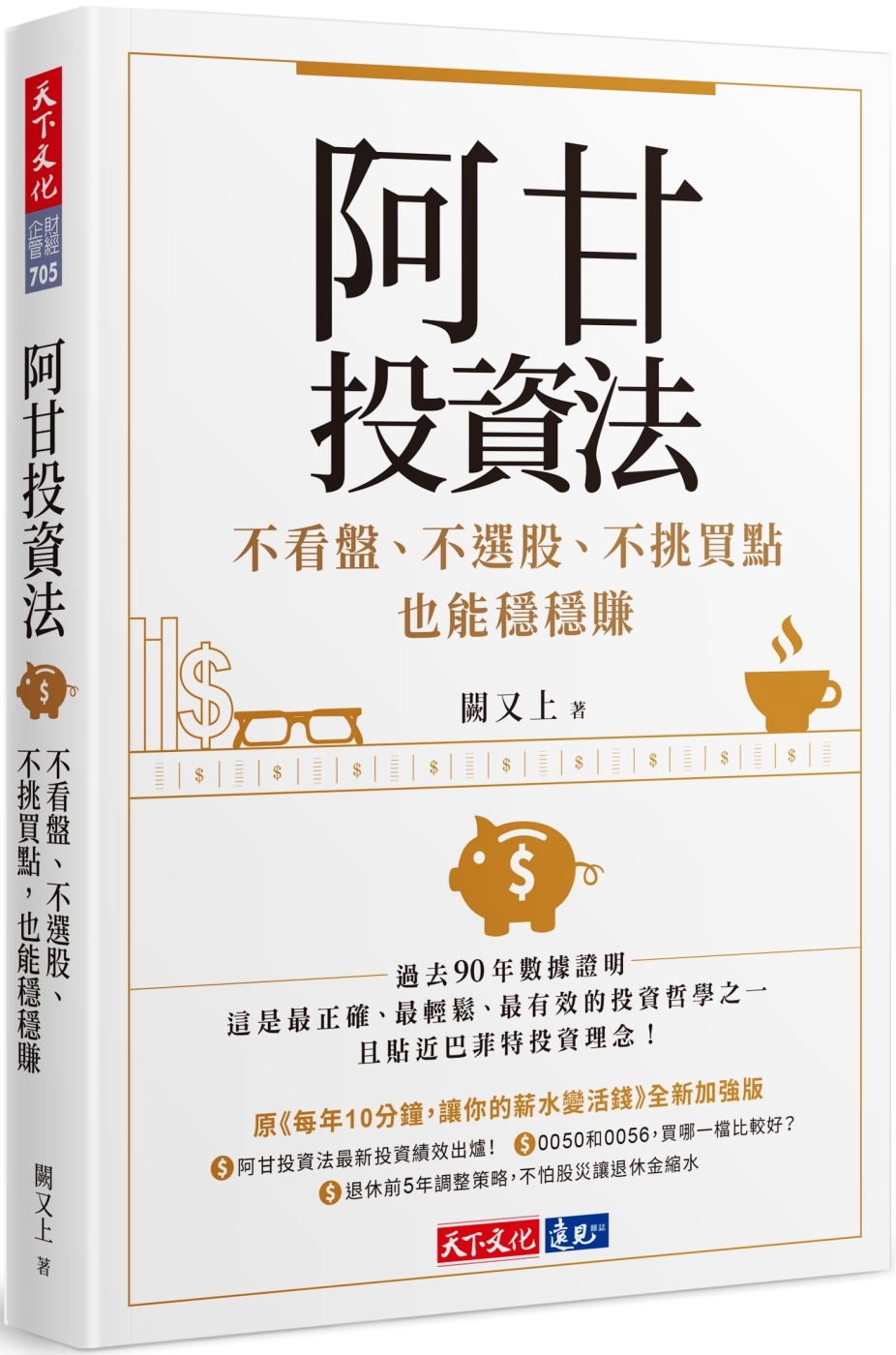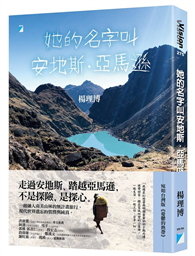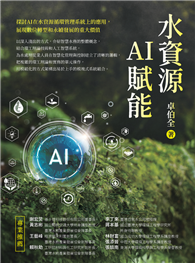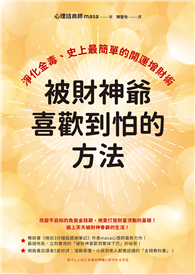滿族賢淑女―― 佟秀敏
時間:2006年5月3日
地點:北京香山北辛村
人物:佟秀敏
學歷:師範
年齡:95歲
2005年夏天,作者在香山租房時,是佟秀敏老奶奶的兒子引著進了他家的院落,老宅院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四堵老牆塞得滿滿的,住了五家人。當她的兒子指著幾個平方米,空落落什麼都沒有,需要兩百元房租的房間,作者一下愣了。即便這樣,還是與佟秀敏老奶奶結下了緣。
佟秀敏真正進入筆下採訪,那是2006年春天,作者再次香山小住的日子裏才結識到這位老奶奶的。她每天至少有兩次到三次,在吃過早飯或是午睡以後到小胡同裏看看形色人群。夏天的傍晚會來到家門口那條小胡同裏坐坐,深情地注視著從她身邊流逝而過的人和事,但我們卻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不過,行人路過此地就會看到這樣一位和藹的老奶奶安詳地坐在那裏,當你的視線無意間和她目光相遇,那是一一副充滿睿智,富有愛意微笑的面容。
母親離開人世那年,我還不記事。清朝沒落之前,我的祖先一直在軍營裏從戎,後來由於戰亂繼而又中斷了與父親和家族的音信。我先被慈幼局收養,後來在慈善家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幼院上學,幾乎過著寡情的生活。所以,我對祖先甚至於父輩的歷史沒有多少印象,儘管一個多世紀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歲月蹉跎已讓我們淡忘了許多往事。但早先那曾停留在記憶裏的一切,似乎與我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不過,每每這個時候,所問及到的人和事,我都非常平靜,除此之外,只要提到慈幼院的生活,以及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後的生活,總會勾起我心中塵封已久的回憶,這時,每每我都會非常激動。
我是宣統退位第二年,即中華民國二年出生的(1912年),沒有趕上前清朝政的日子,兩歲那年母親就去世了。200年前,我祖先的老姓是伍彌特氏,從東北長白山入關北京的,按照20年為一代,從祖上到現在已有十幾代人了吧。當時的滿族皇室,幾乎有一半的人都姓佟,有人稱它為「佟半朝」。意思就是說,在朝廷裏半數的人啊都姓佟,可如今這個姓啊,已寥寥無幾咯。
我的祖先從小就當兵,射箭練功夫,人整個一生都從馬背上跑過來的。父親佟建明是正黃旗,光緒26年在騎兵營當兵,正趕上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京師保衛戰,後來聽丈夫說,那戰啊打得真是兇猛,官兵將士們赤膊上陣,非常勇敢,無數旗人為國捐軀。
只知道母親娘家是南營鑲黃旗的,其餘的就什麼都不知道吶。滿族女子結婚不僅要順從丈夫,還有孝敬公婆。凡是老人健在,家中大事小事由不得媳婦出面,男人掌管著外面一切,他們從來是不進廚房的。那時滿漢不通婚,就連上黃旗也不允許娶下黃旗閨女。
香山腳下,旗人居住區域繁華昌盛,夜不閉戶,夜宵滿街皆是。那時,劉羅鍋,紀曉嵐都在清朝任職。葉氏拉那掌管政權,按先祖規律,女人是不能執政問朝廷的事。喔,這對我們旗人女子來說,還真不知道是榮還是辱?清朝政權至少是在那個垂簾聽政的女人手上敗陣下來的。清朝的消失,我們隨著沒有朝廷的俸祿,家境一落千丈。旗營裏那些老爺們生在皇城根下,個個關餉吃皇糧,過慣了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依賴生活,想想看當時的日子是怎麼順心啊!?後來,這滿朝官兵眷屬的生計也被掐斷了,不得已只好和你們漢人爭飯碗,什麼都去學著做,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人總要活下去吧?不得不去賺錢養家糊口。民國開始,一夜間多少八旗子弟沒了生活著落,生活來源只好靠挑水過活,那挑水的人比喝水的人還要多啊!到了冬天給大戶和有錢人家背煤。北京是平原,哪來那麼多煤窯?這你就不知道了。那會咱上學時,從先生那裏就得知,郊區煤窯林立,不然,北京城裏人那麼多,大冷的天咋辦?煤的需求量可不是一筆小的數字。
作者查史料證實了佟秀敏老人所說的:據1762年(乾隆27年)工部衙門的報告,北京西山和宛平、房山兩縣共有煤窯750座,可采的煤窯有273座。
關於窯民的描寫。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關於煤礦工人的描寫極為罕見,而在滿族詩歌中至少有兩篇可謂詳盡地反映煤礦工人的詩,而具出自大家之手。一是英和的《煤窯民》,一是奕繪《挖煤歎》。《煤窯民》描述了豎井設備與生產情況。在設備方面,詩人重點指出:關係礦工「性命所托惟風輪(鼓風機)」。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北京香山腳下旗人的命運──口述歷史訪談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書 |
$ 246 |
中國歷史 |
$ 252 |
人物群像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2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北京香山腳下旗人的命運──口述歷史訪談錄
辛亥革命燃燒起的排滿情緒,為了緩解民族仇恨和矛盾,他們不得不改名換姓,被迫流離失所外出謀生。本書通過落泊的清末後裔對祖先的回憶,從而揭示了京城八旗生活命運的興衰史。今日旗人生活境遇怎樣?書中主人翁對他們祖先的姓氏起源、風俗習慣、衣食起居、宗教信仰、婚喪嫁娶及旗營軼聞作了敘述。
作者簡介:
張琴
自由撰稿人。中國西北新聞函授學院結業,曾勝任《四川城鄉建設報》記者站,《海南經濟日報》資訊部,《歐洲時報》西班牙特約記者。獲世界華人作家西班牙賽區徵文首獎。法國《歐洲時報》徵文三等獎;西班牙《華新報》徵文比賽二等獎。2010年世界華文小小說徵文《漁家淚》獲獎。作品在《歐洲時報》、《華新報》、《中國報》、《歐華報》發表並連載。獲獎作品在《中央日報》首版發佈。2010年微型小說《為主人守墓的傑米》、2011《守望》發表在《香港文學》。出版〈地中海的夢〉、《異情綺夢》、《浪跡塵寰》、《田園牧歌》、《琴心散文集》、《秋,長鳴的悲歌》、《天籟琴瑟》。
2010年,作品收藏在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出版的《對窗六百八十格》、《歐洲不再是傳說》、《歐洲教育》等書中。 現為「西班牙作家藝術家協會」首席華人會員。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世界華文小小說總會會員。
章節試閱
滿族賢淑女―― 佟秀敏
時間:2006年5月3日
地點:北京香山北辛村
人物:佟秀敏
學歷:師範
年齡:95歲
2005年夏天,作者在香山租房時,是佟秀敏老奶奶的兒子引著進了他家的院落,老宅院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四堵老牆塞得滿滿的,住了五家人。當她的兒子指著幾個平方米,空落落什麼都沒有,需要兩百元房租的房間,作者一下愣了。即便這樣,還是與佟秀敏老奶奶結下了緣。
佟秀敏真正進入筆下採訪,那是2006年春天,作者再次香山小住的日子裏才結識到這位老奶奶的。她每天至少有兩次到三次,在吃過早飯或是午睡以後到小胡同裏看看形色人群。...
時間:2006年5月3日
地點:北京香山北辛村
人物:佟秀敏
學歷:師範
年齡:95歲
2005年夏天,作者在香山租房時,是佟秀敏老奶奶的兒子引著進了他家的院落,老宅院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四堵老牆塞得滿滿的,住了五家人。當她的兒子指著幾個平方米,空落落什麼都沒有,需要兩百元房租的房間,作者一下愣了。即便這樣,還是與佟秀敏老奶奶結下了緣。
佟秀敏真正進入筆下採訪,那是2006年春天,作者再次香山小住的日子裏才結識到這位老奶奶的。她每天至少有兩次到三次,在吃過早飯或是午睡以後到小胡同裏看看形色人群。...
»看全部
目錄
目錄
【推薦序】「讀張琴與她的書」/金適
【代序】探尋歷史的榮與痛/飛揚的流沙
【自序】旗人的根究竟在哪裡?/張琴
滿族賢淑女──佟秀敏
祖父留下的「虎符」牌──那世儒
官宦之家──寧海
戰爭改變了她的信仰──吳素芝
我姓愛新覺羅──愛新覺羅‧朝奎
將軍的女兒──鄂秀華
一輩子做官,十輩子壘磚──趙芝香
來自美麗的傳說──孟昭銥
我們祖先在長白山下──付尚義
香山腳下話旗營──白鶴群
淺析滿族文化──金城
八國聯軍為何沒有西班牙?──吾義
京城苗寨是怎樣形成的?──薩繼承
我們的祖先究竟是誰?─...
【推薦序】「讀張琴與她的書」/金適
【代序】探尋歷史的榮與痛/飛揚的流沙
【自序】旗人的根究竟在哪裡?/張琴
滿族賢淑女──佟秀敏
祖父留下的「虎符」牌──那世儒
官宦之家──寧海
戰爭改變了她的信仰──吳素芝
我姓愛新覺羅──愛新覺羅‧朝奎
將軍的女兒──鄂秀華
一輩子做官,十輩子壘磚──趙芝香
來自美麗的傳說──孟昭銥
我們祖先在長白山下──付尚義
香山腳下話旗營──白鶴群
淺析滿族文化──金城
八國聯軍為何沒有西班牙?──吾義
京城苗寨是怎樣形成的?──薩繼承
我們的祖先究竟是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琴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2-02-16 ISBN/ISSN:97898622188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