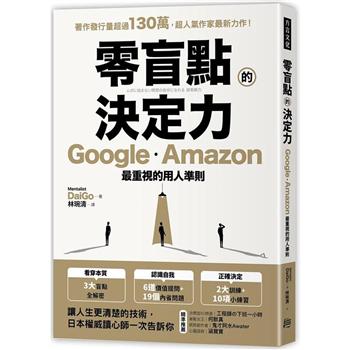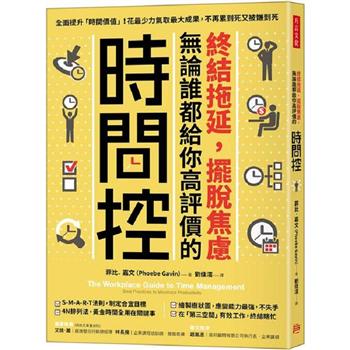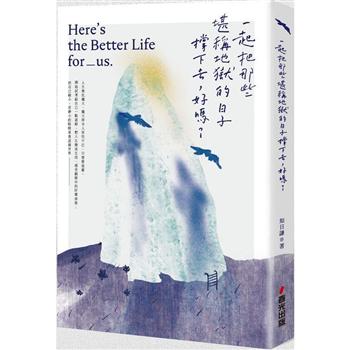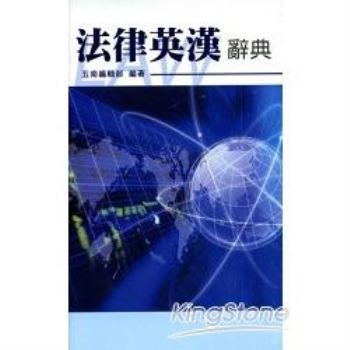第一次見到她,他就覺得,她真是笨得可以!
怎麼會有人單純天真到近乎「愚蠢」的地步?
要不是在一次任務中受了傷,意外被她「撿」回家,
他永遠也不會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真有所謂的好人。
她住的小屋又破又窄,就連床也十分迷你,
他一躺在上頭,連腳都伸不直,真不知道要怎麼睡人。
聽她喊他一聲大師兄,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有這麼一個不中用的師妹。
問她知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她開心的說:「行俠仗義!」
身在殺手門中,卻想要行俠仗義,她是不是拜錯師啦?
問她知不知道門規,只見她搖了搖頭,露出小狗般迷惑的眼神,
還問他門規是要背下來的嗎?不是看看就好?
麻煩!她絕對會是個大麻煩!
但他最討厭欠人情,既然她救了他,他會報答她。
不過,可以報答她的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她一下子惹上街頭惡霸,一下子又差點被賣掉,
上一刻才將她從惡匪手中救出,下一刻她又掉進了陷阱裡……
若不好好看住她,制止她那氾濫的愛心,
只怕哪天她在人家刀下了,還會笑笑的問:「需不需要幫忙?」
章節試閱
楔子
那棟位在陰桑坊,像三品以上官宦人家居住的大宅邸,只要是住在穰原的人都聽聞過。
他們聽說那是一個因外州礦產而發跡的富戶人家,光是老爺一人,就娶了三妻四妾,膝下兒女與孫兒多得可羅列門庭,還說有時在廊上相遇了,竟想不起來對方是哪一房的親戚或孩子……
這都是在穰原的市街上,口耳相傳的傳說。
大家都相信傳說,便沒什麼人會再去探究這傳說底下,到底有幾分真實。
一日,住在陰桑坊附近的平民百姓,又看到一輛氣派、裝飾精緻的豔紅馬車,從大街轉進了陰桑坊,停在那大宅邸門前。
「喔,瞧,那老大爺的兒子回來了。」一個生得福態福態的婦人說。
「咦?妳怎麼這麼清楚?」一個瘦得像根竿子的婦人剛搬來,不太熟悉這裡。
「住久了,總會看到。」胖婦人指了指那從容下馬車的男人。「看,那就是那老大爺的大兒子,聽說,好像叫﹃韓分﹄吧?是他老大爺生意上的頭號助手呢!」
瘦婦人定睛細看那男子,心裡不禁暗暗悸動了一陣。實在是因為這個男人的面容輪廓生得太雅太俊了,就像個女子一樣清秀,但他絕不是像個娘兒們一樣嬌柔的弱人。他的眉就像劍一般剛硬,直直地刺入兩鬢,又生了一雙銳利細長的眼,使他的眼神充滿英氣肅穆。加上他那一身挺拔修長的身材,裹在深色的藏青袍子裡頭,隱隱可見肌理服貼,看起來更是強壯而不可侵犯。
胖婦人嘲弄地說:「唉,看久了他也不會理妳,想當初住這兒的良家婦女,誰不希望韓少爺可以看自己一眼?因為他家世不但好,生得又俊,不公平的老天把所有的好處都推給他啦!可惜,他從來不會看任何女人一眼。」
瘦婦人失望了。「是覺得我們窮,看不起?」
「倒不是,聽說他個性就是這樣,對女人沒興趣。也有富戶人家的女兒想嫁給他,他甩都不甩呢!」胖婦人哼哼笑說。
瘦婦人點點頭,又看了那男子一會兒,忽然一愣,咦了一聲。「他的手?」
「怎麼了?」
「那少爺的手好像沾了什麼東西……」瘦婦人不太確定。「是血嗎?」
「好啦!人家要進府啦!那庭院多深,我們是沒機會了。走,去買菜吧。」說著,就把瘦婦人給拉去耕市了。
那男子一進府邸,馬上就有一個總管模樣的老爺子靠了過來。「寒爺,辛苦您啦!」
男子擺擺手,低聲問:「師父呢?」
「在書房研究近日從蒿山派手中搶來的祕笈。」
「我知道了。」男子說著,就要往書房走。
老爺子望著他的身影,忽然一驚,低叫了一聲。「寒爺,您的手?」
男子舉起左手,手上全是一條條從高處流下的血。
他知道,肩窩的傷口裂開了,但他不以為意。「那是別人的血。我趕著回來,沒處理好。」他淡淡地說。
「您要不要先去更衣,再見盛爺?」總管擔心地問。
男子背著老爺子,伸手迅速按了幾個穴,止了血,才說:「不,師父一定急著聽我行刺的結果,我必須交代,多謝您費心。」
「可……」老爺子不想明說,但他發現男子的臉色蒼白,像大病了一場。
男子卻不讓他說完,逕自往書房走去。
這獨獨占去一棟屋子的大書房,乍看之下沒有人,只有一座屏風獨立在室內。但男子依然撩袍、跨門檻,恭恭敬敬地跪拜在屏風前。
他叫了一聲。「師父。」
過了一會兒,屏風裡響起了一個低沉卻中氣十足的聲音。「回來了?如何?」
「徒兒已了結此人,不必擔心。」
「很好。」頓了一下,又問:「一切都好?」
「很順利。」男子馬上接話。
「可聽你的聲音,怎有些氣弱?」這聲音雖慢,卻十分有威嚴。
男子力持穩定。「徒兒趕路回京,有些累。」
其實左肩的痛,已經遠遠超乎他能忍耐的限度。這次他受的傷,不但整個肩窩被刺穿,更可恨的是,賊人還在兵器上餵毒,使他血流不易止。
但這一切,都不能讓師父知道。一旦被師父知道他在行刺過程中受傷,那他的殺手生涯就完了。在師父看來,會被傷到的人,都是廢物。他認為好的殺手,應該是誰都傷不了的。
若不殺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何用處?這是師父從小就強烈灌輸給他的觀念。
屏風後的聲音靜了一會兒,才不冷不熱地說:「寒芬,你不虧是我的好徒兒,這次行刺不易,你快去休息吧。」
這叫寒芬的年輕男子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卻有些暈,他努力把持意識,穩著聲音說:「謝師父,徒兒告退。」
寒芬緊緊握著左拳,故作從容地走出書房,好像一切都沒事似的。可一旦遠離了那讓人感到壓迫的地方,他的意識就渙散了。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敢放任自己的傷口疼痛。
他不斷告訴自己:撐著!寒芬!撐著!不可以在這兒倒下,要是被其他師弟妹看到了,他就全完了。他是大師兄,是師父最得意的門生,他不可以毀了自己的地位……
忽然,眼角餘光閃進了一個身影。
「師兄?」是一個女孩子的呼聲。「您怎麼了?」
糟了。他閃身,往庭院走去,想施輕功跳上屋簷。
可力勁一發,全身卻全軟了,腳甚至支持不了他的身體,一歪,他偏頭倒下。
「哇啊!師兄——」那聲音像被嚇到似的。
不可以……不可以倒……倒下前,他心裡這麼想。
但失去意識前,他只記得,他看到了一張清秀稚嫩的臉,毫不保留地顯露出對他的擔心。
第1章
當寒芬醒來時,看到自己身處的簡陋屋子,還以為自己來到了鄉野小村。
這個地方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只有一張床、一副桌椅,加上一口正在燒著東西兼取暖用的小火爐。若不是看到半開的窗外,種著他所熟悉的花草、建著他已看膩的亭閣屋樓,他不會認出這是宅邸裡的某一處。
師父是個很注重外表的人,宅邸的一切雕飾富麗堂皇到可以媲美皇親國戚,就連他們出門行刺,師父都要他們穿得像富貴人家,不但體面,也可避人耳目、逃開官府的盤查,畢竟他們無法將殺手與公子哥兒聯想在一起。
不過在如此富貴的表面下,也安排了幾處像這樣窮破的地方。他隱約記得,這是給未出師的師弟妹或不上道的殺手待的地方。他們的師父,就是一個賞罰如此分明的人。因為他出師甚早,很快在道上闖出名號,所以很快就脫離了這裡。
他緩緩地坐起身,扯動了左肩的傷口,他咬牙忍疼,看了一下左肩,發現自己正赤裸著上身,左肩的傷都已處理乾淨、包紮得整潔,隱隱有股令人身心鬆弛的藥香……
這藥香讓他感到安心,他本想再躺回榻上,休息一會兒,畢竟這次行刺,他連續三天兩夜沒睡,身體實在是累了。
可一沾枕,他大驚!
這裡可是全禁國最大、最教人聞風色變的殺手門!雖說這裡的人互稱師兄弟、師兄妹,但他可沒忘了,連他在內,大家都被師父調教得有如豺狼虎豹,誰都不可以信任!
他趕緊起身,發現旁邊的桌上有備著一件乾淨的襦衣,他抓起隨便套上,便要逃出這間讓他暫時放下警戒的屋子。
此時,這間屋子的門打開了。
那開門聲就像在耳邊突然爆炸的鞭炮一樣,驚得寒芬連忙拔下自己束髻的黃銅簪子,像刀一樣緊握著,困獸似的緊瞪著來人。他那緊張的模樣,彷彿自己還身在敵營似的。
「師兄?」
門邊冒出的柔柔嬌聲,與一室的緊繃大相逕庭。
看見受傷的師兄能夠站起來,女孩顯得很高興,好像壓根兒沒看見對方正拿著致命的武器對著她。
她關上門,走到小火爐旁。她笑得毫無防備、毫無心機。「師兄覺得如何?傷口還會痛嗎?要不要再躺一會兒呢?」
寒芬沒回答她,只是用一雙利眼打量著她。
他沒見過她,應該這麼說,他從沒在這間大宅內,看過可以笑得這麼天真、這麼單純的女孩——如果不是他頭昏、看錯的話。
她生得嬌嬌小小,一副弱不禁風、一陣掌風就可以吹倒她的模樣,連臉都一樣精小,只有那雙眼睛,大得可以洩漏出許多她內心的情緒。天知道,這在師門內是多大的禁忌——這女孩怎麼可以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來呢?
女孩走到小火爐旁,把藥簍裡的藥草一點一點、小心翼翼地撥進了爐上的陶鍋裡。
寒芬還是一樣警戒著,想看透她——看透她的天真底下,是不是藏著心機。
他知道,有些師妹會拿天真來當面具。
放好了藥材,女孩直起身,擦了擦臉上被爐子逼出的薄汗。她看到寒芬依然維持那姿勢不變,也是這時才發現他手上正拿著一枝簪子對著她。
寒芬看到她的臉色變白,好像嚇到了。他想,這女孩也太遲鈍了。
「師、師兄,那個……別誤會……」她急著解釋,貿然向前靠近他。「我只是替你療傷,我沒傷害你的意思,別、別誤會!」
「不要過來。」寒芬冷冷地警告她。
不過他心裡的警戒其實早放下一半了。他看著她那拙於防備、拙於言辭的笨模樣,不禁懷疑她和他是師出同門嗎?她這模樣怎麼可能當得了殺手?
可轉念一想,萬一她就是想拿這笨模樣,想讓他鬆下戒心呢?
他是寒芬,他不會被騙。
他用簪子隨意挽了個髻,把身上的襦衣穿好,又環顧四周,沒看到他原本穿的衣服。
他瞪向一臉焦急的女孩。「我的衣服呢?」
「師兄,你現在還不能動,傷口會——」原來女孩焦急,是因為看到他肩上泛紅的傷口。
「我的衣服!」寒芬凶她,女孩縮了一下。
她不知道,他是花了多大的力氣,才把她擔心他的表情扔到一旁——即使他看得出,那表情如此真實……但誰知道?誰知道師父在他不在的時候,又飼養了多少隻豺狼,要他們互相殘殺?
「我、我拿去洗了。因為,上面有血。」女孩顫抖地說:「還沒乾。」
寒芬皺眉。
意識到自己似乎做了什麼罪無可赦的事,女孩趕緊陪罪。「等衣服弄乾淨了,我會親自還給師兄,不會弄壞師兄的衣服的,請放心。」
寒芬不想多說。他瞥了一眼窗外,仔細聆聽,知道這屋子四周暫時無人經過,他要走的話,正是好時機。
他不再多留,一個箭步就要上前開門。
「啊!等一下!師兄!」沒想到那女孩竟拉住他。
他又瞪她一眼。難道她不知道,殺手最痛恨別人碰他們嗎?
女孩雖然怕他的眼神,但是這回她倒很有勇氣,堅持說完自己的話。
「藥,你得喝藥。」她指指火爐。「不喝的話,逼不出毒的。」
「不必了。」寒芬轉身要走。
女孩還是不放手。
「師兄,你得顧你的身子!」
寒芬怒了。「是誰要妳這麼做的?!是若袖?」若袖是他的二師弟,總與他不對頭。
難道這女人是若袖派來陷害他的?因為師門有一條規定,不許同門之間互助互濟,違者一律鞭笞。
女孩先是呆了呆,好像對若袖這名字不太熟悉。想了想,啊了聲,才說:「是二師兄?可這跟二師兄有什麼關係?」
「不要裝蒜!」寒芬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放手。」
「請你喝藥!」這女孩不知是不會看人臉色,還是真的找死,說不放就不放。
寒芬這回不說了,直接運氣,手只是輕輕一擺,就把她給逼退開來。
這推力太突然,女孩沒有防備,竟跌坐在地上,還撞上爐子,差點把陶鍋給撞下來。還好陶鍋只是虛晃幾下,那藥湯並沒灑出來。
寒芬心裡也是暗驚,不知道這女孩怎麼連最基本的防備也沒有,這麼容易就被人推跌在地。她真是他同門的師妹?
女孩想坐起來,撞上爐子的肩膀卻抽痛了一下,痛得她嘶嘶叫。
「啊,痛……」
寒芬緊握拳頭,狠下心,說:「妳根本就不該理我。」
女孩抬起頭,眼眶紅紅的。
寒芬選擇忽略那雙紅眼睛。
「妳難道不知道,同門互助,鞭笞二十?」他故意哼笑。「真是傻子。」
女孩一愣,臉終於出現了怒色。
「看到人受傷,替他療傷,有什麼不對?」她賭氣地說。「我不知道這裡的人到底怎麼了?為什麼一件普通至極的事,也要這樣緊張兮兮的?」
「隨妳怎麼想。」寒芬撇頭,不看她。「妳自己好自為之。」
說完,他匆匆地走了。
以往,即使是犯下滅門血案,他都能從從容容的走出大門。
可離開那女孩,他卻是用逃的。
他和那女孩一樣,也不懂、也困惑。
他不懂為什麼自己無法面對她?為什麼看到她被推倒在地的模樣,心裡會覺得愧疚?
難道是因為那顆關心他的心,是真實的、是純潔的?
看慣人心黑暗面的他,反而害怕,害怕自己會依戀、會無法捨去這份溫暖的感覺?
他不懂,他也不要自己再想。
▎ ▎ ▎
這棟大宅邸裡,有分前庭、後庭。這兩庭由一道中門分隔,過了中門,會發現這棟宅邸竟可同時容下這兩個有如天壤之別的殊異世界。
前庭的廂房,是師父以及幾個已出師的師兄姐所住,寒芬便住在這兒。這兒的生活就像一般富有人家那樣,有華麗的雕梁畫棟,精美的瓷器、梨木家具,還有一堆對他們唯唯諾諾、伺候得無微不至的婢女、門僕。華衣美服的他們,的確就如尋常人家對富家皇族的印象,是那樣高貴,高不可攀。
至於後庭,滿是骯髒破漏的房舍,間雜在雜亂的竹叢野草中。走出中門,好像來到荒煙蔓草的荒境中,無法想像這會是在同一棟宅邸內。這個後庭,便是那些剛入師門的師弟妹,或是已出師,成果卻不這麼亮眼的下等者所待的地方。
那些已出師、並在道上闖出名號的師兄姐,曾經也是從那兒爬出來的,對那後庭是畏懼及鄙夷的,從來都不願多看那兒幾眼。
寒芬對那兒也是感到輕蔑、不屑的。因為那裡正是無法向上爬的懦夫,終身必須待著的地方。
今天,他用完了早膳,婢女來傳話。
「爺,盛師父要您早膳後去見他,他有一門生意要請您接。」
寒芬面無表情的喝著茶,淡淡地說:「我知道,一會兒就去。」
他揮揮手,婢女退下。
房內無人,他輕嘆了口氣,探摸著傷口。傷口才放了幾日,還沒癒合,能負荷嗎?
但這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不管能不能負荷,他都一定得接,這是他在這師門裡保住地位的唯一方法。
他打理了一下,出了房,往師父的書房走去。忽然,他聽到了極輕如落葉的聲音,他凝著臉猛地回身,看向來人——
「嘿!師兄——」來人熱情的打著招呼,臉上那誇張的笑,就像雜耍的面具。
他依然冷著臉。「有事?」
這生得清秀、一笑就能蠱惑眾人的男人,笑道:「聽說,您又有案子要接?」
說著,他甚至伸手,想稱兄道弟的去攀寒芬的肩膀。
那肩膀剛好是寒芬的傷處,他盡量保持自然,閃過這男人的勾搭。
男人將這反應看進眼裡,又說:「師兄,怎麼?嫌我髒?」
寒芬冷冷看著他。
「還是……」男人露出狡詐的笑。「那裡碰不得嗎?」
「若袖。」寒芬開口。「我有事先走,日後再談。」
這叫若袖的男人逕自說:「師兄可得小心。您知道師父的,殺手受了傷,就跟自己的女人給別人搞過一樣,一點價值都沒有。」
寒芬停下腳步。
若袖興災樂禍地等著他的反應。
寒芬回過頭,也露出了一個看來很有親和力的笑。在外頭,要裝出這種笑來讓獵物放下警戒,並不困難。
他說:「你有時間在這兒說風涼話,何不多表現一點,讓師父肯定你的價值,好取代我的位置?」
若袖皺眉。「你說什麼?」
「你能嗎?」
若袖僵著臉,想反駁。
寒芬搶話,不讓他說。「若能,你今天不會還是大家嘴裡的二師兄。」
「你——」若袖不笑了,臉上盡是怒氣。
寒芬一笑。「先走了,師父找我。」
他從容地走過廊道,拐了彎,四周靜悄……
他臉上那帶笑的面具便卸下。卸下後,是一臉的疲憊。
這種日子,總是無邊無際的。不能與人交心,只能一直這樣勾心鬥角,鬥到永生永世……
他的肩膀抽痛,他皺眉忍著,調整內息,才往師父的書房走去。
可他又聽到後頭有腳步聲。這腳步聲竟不掩不藏,大剌剌的往他這兒跑來。
他想若袖這傢伙,竟氣到毫不隱藏自己的行蹤,果然是個成不了材的傢伙——
他的手弓成爪,猛地回身一攻——
「哇!師兄!」一張嬌弱的小臉大驚失色。
他也嚇了一跳,趕緊收掌,可掌風還是削到了那女孩的臉頰與耳邊的頭髮。一道血痕從女孩臉上流了下來。
「妳這是做什麼?!」他沒想到自己會氣到罵人。畢竟他差一點把她的心給挖出來。「妳難道不知道門規?」
女孩被罵,愣了好久,才問:「啊?這也有門規?」
這女孩,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可以在走廊上衝跑,尤其是在別人背後,因為很容易就會被前面的人當成刺客給除掉。殺手門樹敵太多,而這些刺客也都是精通此道的殺手,殺手永遠不會在目標的正面出現。
但寒芬本來話就不多,不願多說,冷著臉就要繞過這女孩。
女孩叫道,又伸手抓住了他。「師兄,等等!」
寒芬瞪她,看著她抓他的手。
女孩尷尬的收回手。
楔子
那棟位在陰桑坊,像三品以上官宦人家居住的大宅邸,只要是住在穰原的人都聽聞過。
他們聽說那是一個因外州礦產而發跡的富戶人家,光是老爺一人,就娶了三妻四妾,膝下兒女與孫兒多得可羅列門庭,還說有時在廊上相遇了,竟想不起來對方是哪一房的親戚或孩子……
這都是在穰原的市街上,口耳相傳的傳說。
大家都相信傳說,便沒什麼人會再去探究這傳說底下,到底有幾分真實。
一日,住在陰桑坊附近的平民百姓,又看到一輛氣派、裝飾精緻的豔紅馬車,從大街轉進了陰桑坊,停在那大宅邸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