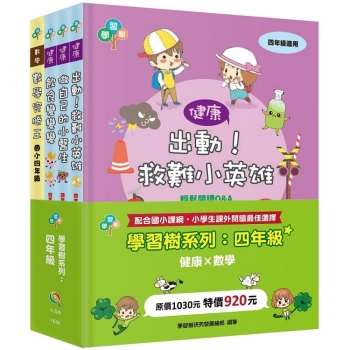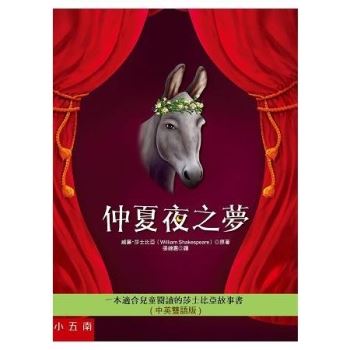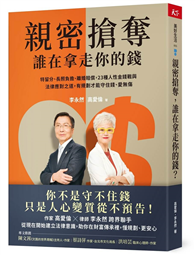VIDEO 當一位懸疑小說作家,受到神經功能上的損傷而失去閱讀的能力, 我看不到正在讀的那行字的行尾,就在我吃力地試著辨認內容時,好不容易讀讀讀到的一個字或一些字的後面,竟没有字了,能看到的就是空白,没有印任何字;而可以理解內容的部分,字的字母像是從一股熱氣中被辨識出來一樣,當我試著辨別它們時,字母們擺動且改變形狀。一個字母前一刻看起來像是一個a,下一刻卻又變成像是一個e,然後變成w,很像周末喝醉酒時散光的情況,透過我的雙眼,一個棋盤變成了抽象藝術。
● 我的腦袋還没完全地免於混亂,有幾次抓到自己把剩菜放在垃圾桶裡,把垃圾放在洗碗機內,並且還在那兒發現了一些衣物。 如果某一天,你原本習慣的語言,突然都變成了火星文,那會是多麼奇怪、恐慌的事情啊!二○○一年早晨,加拿大著名的懸疑小說家霍華‧安格走到門外去撿報紙,突然間,他發現自己無法如往常一樣閱讀了。報紙上的標題像是用其他國家的語言寫的,文章猶如亂碼一般。在醫院,醫生告訴他,大腦因受到劇烈撞擊,罹患了罕見的失讀失寫症──他仍然可以寫作,但不再具備閱讀的能力。
霍華‧安格在紙上寫下的每一個字,對他來說,都像是某種記憶密碼。街道名稱、湯罐頭標籤、看板,甚至是他自家的住址,都被轉化成一種難以理解的暗號。這次中風的其他影響,隨著時間逐漸浮現,但對一個靠著文字過活的人來說,沒什麼影響比這個來得戲劇化或說更具毀滅性。
霍華‧安格聯繫了著名的神經科醫師奧立佛‧薩克斯,而這個不尋常的病歷,就由奧立佛‧薩克斯接手了。漸漸地,安格通過奧立佛‧薩克斯長時間的訓練,又重新獲得一些閱讀能力。在家庭的支持下,和大量的治療過程後,安格再次執筆寫班尼.古柏曼系列小說,這本小說幫他贏得了廣大粉絲的敬愛。
【本書特色】 ● 可以寫卻無法閱讀的作家,從中發現讀和寫的一切奧祕
作者簡介:
霍華‧安格(Howard Engel)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媒體推薦:
「安格運用其寫小說的天賦,娓娓道出一個攪動且激勵人心、同時又帶著自我消遣趣味的一個故事。」──《筆與紙》書評雜誌(Quill & Quire)
名人推薦:
章節試閱
前言 ▎ 引言= 引言=
前言 ▎對我而言,重要的是,回首並記得使我身在此處的每一步履,我需要知道那些,如此我才不會忘記這一路上的奮鬥,以及有一些人幫助我攀爬了那所有的階梯。我的名字叫霍華.安格(Howard Engel),我寫偵探故事,那是當人們問我做什麼時,我告訴他們的答案。我可以說自己是位作家或是小說家,但那樣回答,會在我的腦袋裡引起一陣與事實不符的回響,所以我更喜歡「寫偵探故事」的這個宣稱,顯然更為貼切。至今,我已經寫了不少的著作。在提筆寫作之前,我是一位讀者,我閱讀的範圍很廣泛,從童年早期的識字課本《約翰、瑪麗及彼得》(J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