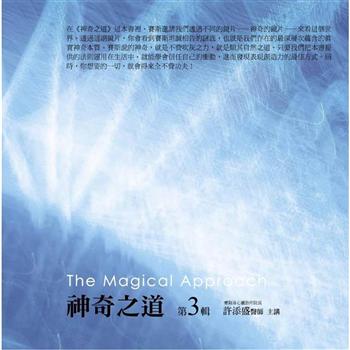序
贅言
我喜歡人。
這話聽起來很奇怪,卻是事實。我喜歡不同的人生中流露出的人性,看不同的人格和人品用各自的方式展示,在人海人潮中流覽不同的人面、不同的人聲、不同的人心,在人間人世裡閱讀紛繁的人情、紛繁的人事、紛繁的人道。
所以有了這本書,書裡面有二十個人。
每一次訪談──我稱為「讀人」,都是好玩的經歷,我讀過一隻手的葉廷芳、一條腿的江平,前者是因為天災,後者是因為人禍。我也讀過董秀玉的笑、資中筠的哭,前者是天理,後者是良心。
當然,對我來說,記錄他們的口述,也未使沒有太史公的難言之隱:「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我自然也清楚,他們不可能對我完全開放,他們的講述都是有選擇的,有意無意也是有目的的。這曾經是相當困擾我的問題之一,我也曾經將全部的力量用來跟他們較勁,刨開他們慣常對人說的那些浮土語言,掘出岩石層下深深的東西,甚至冒著惹毛對方的危險,提各種尖銳的問題。卻總不能滿意,絕對真相似總如早春的草色,「遙看近卻無」。
不過現在,這個問題對來我說已經不構成困惑了。世間並沒有一個完全客觀和真實的「過去」存在,過去只能以「被回顧」的形式存在,歷史本來就是現在加之於過去的一種顯現,是以一種不那麼真實的狀態存在和構成的。
所以,我所謂的讀人,不僅是使勁地挖他們,聽他們說什麼,還包括了咂摸他們為什麼說這些,為什麼這麼說。這是「讀」的趣味。這個趣味,不是講述者提供的,而需要讀者自己去完成。當然,這種趣味需要別的材料來支援,比如其他途經的說法、不同角度的訴說和評價。沒有一本書是單獨有趣的,也沒有一本書能單獨提供全部事實。歷史是複式的。
在編排上,我想過幾個方案:按姓氏筆順或拼音,沒有比這個更技巧卻犯傻的方式了,按聲望,那是自掘墳墓。我用的是年齡排序,讓最年長的排最前面,順著時間的臺階漸次從歷史的縱深走到近前來。事實上,我個人能從年齡中讀到兩代半知識分子非常明顯的不同來,他們用各自的人生,書寫著中國當代的知識歷史。我想展示的,不僅是人,還是這些人構成的一種形式的歷史。
一個必要的說明是,文章雖然是口述史形式(也確實沒有借助賈雨村君),但並不完全是被訪人口述的話,因為口語直接整理出來,是根本不可能成文的。比如,「我就那個什麼了,去她那兒,他也在,怎麼說呢,結果就這樣了」,這裡面的每個代詞,都得換成名詞。聊天中不確切的引經據典,言及的書名、地名、專用名詞,都要事後核實。所以,要刪節、補充、調整、裁剪,還要儘量保持口語的特點,很是繁瑣。(一句題外話,因為有了如許的採寫經歷,我對口述史這種形式是暗存疑慮的。)
另外,我並沒有完全按照被訪人的修改意見來定稿。有些東西,被訪人聊天中說到了,回頭又不願意公開,而這實在出於多餘的顧慮,我便保留了。(當然,也確實有些東西,重要或者有趣,卻不宜公開討論,便直接「甄士隱」了。)加上有些審稿來來回回好幾次,其中一兩字,改了或者沒改,便有些混亂。我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壞毛病:文章放在那裡,今天沒事改兩句話,明天沒事又改三個字,永不消停,無有止境。加上在幾臺電腦之間倒騰,一篇文章便有了無數個版本,有的只是幾個字詞的區別,有的則是章節的調整。另一個同樣可怕的情況是,常有媒體來找我要稿,而不同性質不同領導不同歷史的媒體在不同的時期,言論尺度是不同的,不同到了天壤之別和瞬息萬變的程度。有時候「大饑荒」是敏感詞,就刪掉這一句或那一段;有的編輯不敢用「三權分立」四個字,就改成「西方的分權理論」,到了總編那裡,又成了「西方的理論」;有時候報紙有骨氣,偷偷塞進去一句「一九八九年春天」,居然也發出來了;可有時候因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詞,或者對文革多用了一個形容詞,整篇文章就斃了。總之,這類遊戲永遠玩不完。我又習慣保存每一份文稿,這也是導致混亂的原因之一。總之,我要說的是,如果被訪者發現這裡展現的文章不是他審定後的版本,請原諒。我只保證:第一,我寫的東西都是被訪人確實表達過的意思。第二,被訪人嚴格說明不能說的,這裡面沒有。
上述兩項說明也表示,全部的文字都只能由我個人負責。
還有一個或許多餘的說明,鑒於這本書裡的人,多少都是「有身份」的,我字裡字外便可能透露出太多的「隨意」,讓人感覺不夠莊重或尊敬。但我實在很不喜歡「尊敬」這個東西,它在中國的傳統中過於隆重和格式化,設置好程式,一個機器人也可以表現出合格的尊敬。我更願意說,我很「喜愛」自己訪問過的人。我身上實在沒有哪怕一個能做粉絲的細胞,做不到在任何「Big Man」面前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更做不來頂禮膜拜、五體投地這類難度係數太大的動作。一個有成就或有身份的人,除了好家世、好運氣,多有超過常人的努力和能力,但他總還是人,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讓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俯首稱臣或頤指氣使。我更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天下所有人都會嫉妒、會貪婪,也有理智、會反思,相信所有人賺到錢了都會高興,憋著尿的樣子也一樣難看,我還相信,所有人被愛的時候心都會溫柔,而世界所有的問題,癥結只一個,就是缺乏愛。
這麼說,沒有對被訪者不敬的意思,我用我的方式表達尊敬,恰恰因為我喜歡他們。個人認為,喜歡是最高層次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