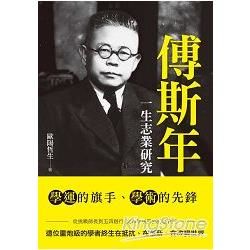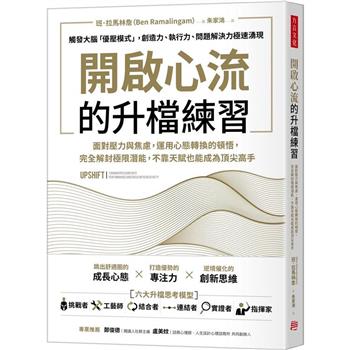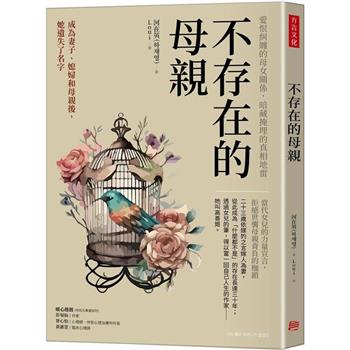學運的旗手、學術的先鋒
從挑戰師長到五四遊行 從革新研究到揭發貪污
這位重炮級的學者終生在抵抗、在革新、在改變世界
從挑戰師長到五四遊行 從革新研究到揭發貪污
這位重炮級的學者終生在抵抗、在革新、在改變世界
傅斯年,人稱「傅大炮」,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術領導者。他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率領一整群年輕學者,為歷史研究開展新生命。他是一個極為罕見的、在學術和行政能力上都極其優異的知識分子。
本書為五四運動研究者歐陽哲生探索傅斯年一生志業的總集,從傅斯年在北大以學生身分挑戰章太炎學派、擔任五四運動的遊行總指揮、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心推動的研究發展、揭發宋子文、孔祥熙的貪污舞弊,到他面臨日本侵華時展現的政治思想與戰略方針;作者以豐沛的歷史資料,完整呈現傅斯年魄力十足而成就非凡的生涯。
本書特色
本書以詳盡的歷史資料,重現傅斯年從學生到學者時期,在各種學運、學術工作中展現的革新能力與行動魄力,以及他對整個中國近代學術研究帶來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