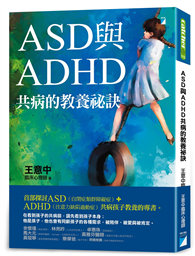在過往的研究中,唐代被認為是較不重視孝道的時代,
但本書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經驗,整合制度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角,
建立層次豐富的唐代孝文化圖像。
委別高堂愛,窺覦明主恩。今成轉蓬去,嘆息復何言。
──陳子昂〈宿空舲峽青樹村浦〉
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為求仕而離親;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倫理法制化形成的諸多規範,深刻影響士人的孝道實踐。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關注人與制度、文化如何互動折衝。從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脈絡,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