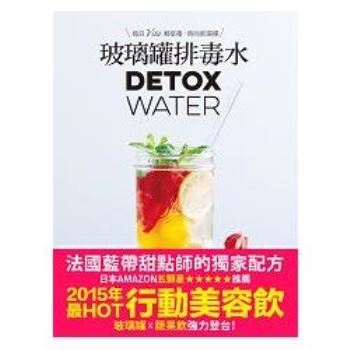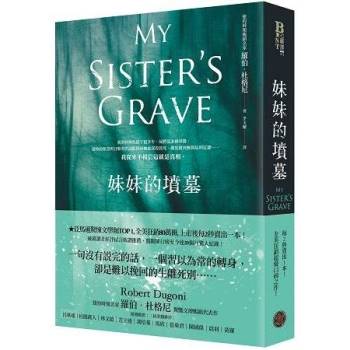初版於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是一本在德國內外哲學界以至整個人文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劃時代著作,也是海德格的成名作。
在20世紀50、60年代,海德格被視為存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一個重要代表,而《存在與時間》則被理解為一部深刻剖析人之存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巨著。
然而,這一理解方式並不為海德格本人認同。對人之存在的剖析,雖然確是《存在與時間》已發表部份的一個主題,但它僅僅擔當着預備性分析的角色;直至海德格1976年逝世,《存在與時間》仍處於未完成狀態。換句話說,從基礎存在論計劃入手支撐着整部《存在與時間》寫作計劃的「存在問題」(Seinsfrage)研究,顯然遇上了困難,以致該書的寫作中斷了,甚至最終放棄了。
為甚麼它一直處於未完成的狀態?是作者問錯了問題?抑或是問題問對了,但試圖回答問題的方法錯了?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劉國英:
法國巴黎大學索爾邦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主任,及《現象學與人文科學》主編。著有《永久和平的倡議者──康德作品選讀》;合編作品有Border-Crossing: Phenomenology, Intercultura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Phenomenology and Human Experience、Identity and Alterity: Phenomen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萬戶千門任卷舒──勞思光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寅卷》、《求索之迹──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校友卷》及《無涯理境──勞思光先生的學問與思想》;並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三卷及「思光學術新著」三卷的主編之一。
張燦輝:
德國佛萊堡大學哲學博士,退休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副主任、通識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及領袖培育課程主任,為《現象學與人文科學》主編之一。著有Earthscape、Kairos: Phenomenology and Photography、《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等;合編作品有Identity and Alterity: Phenomen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Space, Time and Culture及《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等;並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三卷及「思光學術新著」三卷的主編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簡介:
本中心以推動現象學及其與人文科學的關係之研究,同時促進兩岸三地及國際性現象學研究的合作與交流為宗旨,自成立至今已舉辦十多次國際性及地區性的現象學學術會議,並出版《現象學與人文科學》學刊及「漢語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叢書等。近期重要活動包括:合辦「Logos and Aisthesis: Phenomenology and the Arts──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會議」(2012),「第三屆世界現象學組織聯盟學術會議」(Organiz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Organizations III;2008),以及自2007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亞洲現象學大師班」(Symposia Phaenomenologica Asiatica)。本中心亦即將主辦2014年之「東亞現象學圈」(Phenomenology for East Asian CirclE, P.E.A.CE)國際會議。
「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的前身是「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成立於2002年3月。中心蒙鄭承隆博士鼎力支持,為表謝意,乃於2007年正式易名為「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
作者序
編者序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海德格哲學的閱讀與理解,經歷了數次重要轉變。在20 世紀50、60 年代,海德格被視為存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一個重要代表,而初版於1927 年的海氏成名作《存在與時間》,則被理解為一部深刻剖析人之存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巨著。然而,這一理解方式並不為海德格本人認同。早於1946年發表的〈論人文主義書簡〉中,海德格已明白表示,他探討的主要課題既非沙特(J.-P. Sartre)所強調的「存在先於本質」,《存在與時間》更與存在主義的前提毫無關連。 固然,海德格在該信及其後的著述中多番申明,他終身探索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存在意義一般」的問題。對人之存在的剖析,雖然確是《存在與時間》已發表部份的一個主題,但它僅僅擔當着預備性分析的角色;「存在意義一般」這一核心的指引性問題,在該書已出版部份中並沒有獲得正面處理。直至海德格1976 年逝世,《存在與時間》仍處於未完成狀態。換句話說,從基礎存在論計劃入手支撐整部《存在與時間》寫作計劃的「存在問題」(Seinsfrage)研究,顯然遇上了困難,以致該書的寫作中斷了,甚至最終放棄了。
從「存在之謎」到「海德格之謎」
《存在與時間》是一本在德國內外哲學界以至整個人文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劃時代著作,但為甚麼它一直處於未完成的狀態?2 是作者問錯了問題?抑或是問題問對了,但試圖回答問題的方法錯了?長久以來,海德格被視為現象學之父胡塞爾(E.Husserl)的得意門生,3 並被視為胡氏的傳人,故《存在與時間》也曾被視為現象學方法向存在問題伸延的結果。但此書之無法完成,是否意味着現象學方法並不適用於存在問題?海氏與胡氏是採用同一種現象學方法嗎?抑或海氏在面對存在問題作為現象學的新課題之際,為現象學方法帶來了轉變?對這一大堆問題,海氏從來沒有清晰的回答。誠然,在〈論人文主義書簡〉中,海氏說過,《存在與時間》仍受困於傳統形上學語言,因此無法找到一條通達存在問題的道路。4 然而,這一說法具體所指為何?現象學方法不是一種已經離開了傳統形上學的哲學方法嗎?為甚麼《存在與時間》仍會受困於傳統形上學語言?對此,海氏似乎也沒有進一步的清楚解釋。此外,海氏更提出了「哲學之終結」這一驚人論斷。5 這不禁使人疑問:後期的海德格是否也對自己前期的哲學工作作出某種否定?我們不難想像,對哲學思想和哲學語言有高度明晰性要求的讀者,會對海德格的整個哲學工作感到疑惑:海氏的存在問題,究竟是在問怎樣的問題?存在問題可以透過較為清晰的方式去表達嗎?為甚麼存在問題總顯得像謎一般?是存在問題本身成謎,抑或海德格發問存在問題的動機與方式成謎?
事實上,在1961 年出版的兩卷本《尼采》一書中,海氏自己就說過:「存在本身就是謎。」(“Das Sein selbst ist der Rätsel.”)由《存在與時間》提出存在問題到後來承認「存在之謎」,海德格經
歷了一條怎樣的思想道路?這條路是如何走出來的?在其晚期著述中,海德格對他早期學習現象學的歷程,曾有簡要的說明。然而,在同期的著述中,海氏也明確表示,自己的思想在《存在與時間》發表之後,出現了重要的轉向、轉折,甚至迴轉(Kehre)。這樣的思想上的轉折或迴轉為何會發生?是思維主體自覺到需要在思想方向上作出轉變(這時思維主體仍有自主性),還是思想的課題(存在問題)自身無法進一步推進,在前無去路下自身迴轉,因而迫使思維主體也作出轉向?這時思維主體還有沒有自由或自主性可言?「轉向」或「迴轉」在存在問題的探索上意味着甚麼?海德格自身的說明,是否有助解開圍繞存在問題的謎團?抑或在「存在之謎」之外,也加上了一個「海德格之謎」儘管「存在之謎」以至「海德格之謎」一時間不易打開,海德格哲學還是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間,激發了自60 年代起西方哲學界的新動向。在德國,伽達默爾(H. G. Gadamer)的哲學詮釋論,成為《存在與時間》中的詮釋論現象學最重要的後續發展。在法國,
德里達( J. Derrida ) 則把海德格對存在的歷史之毀構(Destruktion),徹底化成一種不單可施加在整個西方形上學史上的研究方法,還發展出一種可以廣泛地運用於其他人文科學領域的解構式(deconstructionist)閱讀策略。在北美,海德格對西方哲學傳統之終結的論斷,成為了羅蒂(R. Rorty)「新實用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之一和思考新起點。來自立陶宛、落戶法國的萊維納斯(E. Lévinas),則朝着海德格存在論思想的相反方向走:他認為存在論離不開西方傳統形上學式思維暴力,要擺脫傳統西方哲學的暴力色彩,就要改弦更張,以倫理思考為哲學的首要任務。
《存在與時間》與現象學的詮釋論轉向
海德格1976 年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在大家爭論這位繼胡塞爾之後入主弗萊堡大學的哲學大師留給20 世紀哲學界怎樣的思想遺產之際,年青海德格的課堂講義──包括1919–1923 年早期弗萊堡時期的講演錄,以及1923–1928 年馬堡大學時期的講演錄──在《海德格全集》中陸續整理出版,使我們對海氏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有了全新的理解。一方面,我們從此知道《存在與時間》是一個經多年醞釀才漸次成形的龐大研究計劃。海氏不單曾於1925 年在課堂上預演這一寫作計劃,10 也曾於1927 年在講演錄中補充處理《存在與時間》已出版部份所未及處理的課題,作為續寫該未完成著作的嘗試。另一方面,我們也從此清楚知道,年青海氏很早就自覺到他與胡塞爾現象學的分歧:從胡氏那裏,海德格只接受了「回到實事本身去」(“Zu den Sachen selbst”)這個形式的現象學概念;但他認為現象學要研究的具體課題,不應停留在胡塞爾所強調的意識及其意向性結構以至各類型的意向性對象之建構(Konstitution),而要轉往使一切建構活動可能的源頭那個主體、即海氏稱為「此在」(Dasein)這一存在者的存在性格,以及更一般的存在意義之問題。
有別於胡塞爾視笛卡兒的反思性主體哲學和康德的超越論主體性哲學為現象學的先驅模式,海德格更重視亞里士多德《解釋論》(“De Interpretatione”)所指引出的方向:既然主體的建構活動必須透過語言來進行,而語言則是主體、即此在的本有能力滲透到此在日常生活各類型的前反思活動中,要了解主體建構活動的源頭,就要了解此在作為於前反思狀態下運用語言從事着各種理解活動這一特殊存在性格。換句話說,此在前反思狀態下的實然生命(faktisches Leben)中所顯露的各種理解活動,是了解此在的特殊存在性格的鑰匙。因此,現象學若要了解其自身可能的基礎,就必須深化成存在意義一般的研究,即深化成存在論;而這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深化成關於此在的「實況性的詮釋論」。海德格早期弗萊堡時期講課稿──特別是1923 年夏季的《存在論──實況性的詮釋論》(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存在與時間》導論第7節海氏自己的現象學概念的線索。在這以艱深著稱的一節裏,海氏提出了一種與胡塞爾大為不同的現象學概念:從研究課題上看,現象學是一門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學,即存在論;從研究方法上看,現象學的描述就是解釋( Auslegung )。此在的詮釋論(Hermeneutik des Daseins),成為海氏推進現象學研究的新方向。
海德格以此在的詮釋論作為現象學研究的新任務來取代胡塞爾的意識現象學,原因之一是海氏認為胡氏現象學(起碼從《邏輯研究》到《觀念I》時期)缺乏歷史意識,而歷史意識或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卻正是此在的存在特性。《存在與時間》沒有就這點對胡氏現象學作出批評,但其實海氏早於早期弗萊堡時期的講課中,就明白地指出了他眼中胡氏現象學的不足。就他對此在作為歷史存在(Geschichtlichsein)的重視,海德格在1924 年的〈論時間概念〉一文,及1925 年關於狄爾泰的系列講座中清楚表明,他是受到狄爾泰的影響。不過,對海氏而言,此在的歷史性最終需要回到此在作為時間性存在來了解,因為此在首先是一個恆常地投射往未來的存在;此在意識到自身作為一個必有一死的存在者,是一個有限性存在,而就在這一有限性存在的意識中,此在活出其作為時間性存在的存在特性。雖然狄爾泰重視歷史意識及人作為歷史性存在的特性,但沒有把人的歷史性和時間性這兩面向結合在一門從時間性入手理解人之存在──即此在──的詮釋論現象學上去,故狄氏的工作沒有海氏要求的突破性成果。海德格的詮釋論現象學,就是在胡塞爾的形式現象學概念基礎上,接上新的研究課題,包括來自亞里士多德視人在前反思狀態的理解活動為一切意義活動的來源,以及狄爾泰所強調的人之歷史性存在性格。這些胡氏意識
現象學缺乏的面向,經過年青海德格的原創性綜合和建構,帶出了現象學運動中的「詮釋論轉向」(hermeneutical turn)。
與納粹主義的關係:「海德格事件」的衝擊
在《海德格全集》的出版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事故,令學術界對海德格思想的討論產生了一個一直鮮為人注意的面向,這就是海德格與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政權的關係。原籍智利的學者法里亞斯(Victor Farias)1987 年以法語出版的《海德格與納粹主義》一書,在大量歷史文獻的支持下,稱海德格畢生其實是一位納粹政權的忠實擁護者,因為海氏在1933 年納粹政權上台後不久便出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就任的十個月期間,多次透過撰文和演說來公開表達以至呼籲大眾對希特勒效忠;不僅如此,他的納粹黨員身份更一直維持到1945年納粹政權解體才終止。另一方面,海氏在二次大戰後發表的著述中,仍然保留着他對納粹政權作為一個擁有「內在真理和偉大性格的運動」的讚語。20 尤有甚者,海氏終其一生從來沒有公開譴責納粹罪行,即使他的早期猶太裔學生如馬庫塞(H. Marcuse)等曾勸籲他這樣做,他也不為所動。這顯示出,海德格對自己曾經支持一個對猶太人作出種族滅絕屠殺的納粹德國政權全無悔意。
這一堆事實的揭露,不單令眾多海德格研究者感到不安,更令有批判意識的讀者禁不住疑問:為甚麼作為20 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之一的海氏,可以與現代人類歷史上最殘暴和最非理性的政權安然同行?當然,當時支持納粹政權的德國學者和思想家不止海德格一人。是海氏個人抵受不住權力的誘惑,還是他的哲學思想與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有相容或可以銜接之處?換句話說,海德格哲學是否有某種納粹主義成分?海氏前期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中的存在論,雖然表面上與政治無關,但是否隱藏了一定的政治傾向以至政治立場,使得他一直堅定而無悔地支持納粹政權?一時之間,海德格個人的政治取向、他的存在論哲學的政治意涵以至政治成分,成為了海德格研究和討論的新焦點。其實,有關海德格其人其思想與納粹主義之關係的辯論,早於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便在沙特和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創辦的《現代》月刊(Les Temps Modernes)中展開,但當時只在少數熟悉海氏思想的歐洲哲學家之間進行,且為時不長,故一直沒有引起知識大眾注意。由法里亞斯上述書籍引發的討論,因為受到西方大眾媒體廣泛報導,並透過北美傳上世界學術舞台,在全球化效應之下,轟動國際學術圈,成為了所謂的「海德格事件」。
「海德格事件」的發生,也引起了海德格研究的另一個關注點:海氏以失敗告終的政治參與經驗,對其後來的思想發展、特別是其思想的「轉折」或迴轉有無影響?這一問題,恐怕是希望對海德格思想發展有較為整全掌握的研究者難以迴避的。也許有見及此,《海德格全集》的編者在法里亞斯《海德格與納粹主義》一書出版之後兩年,推出了《海德格全集》中的新系列,即海德格的遺著;而這系列中的第一冊,就是海氏1936–1938 年間撰寫的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 s(《哲學研究──論發生》)一書。是書的姊妹篇Besinnung(《反省》),也於八年後出版。二書成為探討海德格政治參與經驗與他後期思想演變之關係的新文獻。
「泰然任之」──晚期海德格的末世論話語
不過,即使在上述海德格遺著出版之前,已經有不少文獻幫助我們了解海氏後期思想的輪廓。扼要來說,《存在與時間》顯示的是一種「實存的決斷論」(existential decisionism),強調此在要脫離日常生活中從眾的沉淪狀態,在每一當下決斷地面對一己之為必有一死的存在,積極地回應存在之召喚,為存在之真理、即存在的開顯服務,成為本真的實存者(authentic existence)。「轉折」之後的海德格,一改《存在與時間》中鼓吹的積極人生態度,認為我們要對當前被現代技術支配的世界,採取一種「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態度,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作出思想上的準備,因為此時海氏強調的是存在作為命運(Geschick)。人類與存在的關係,就是西方人自先蘇格拉底時期思想家對存在的本源綻開之短暫經歷,及其繼後哲學家各種不同方式的對存在遺忘的經驗,而西方文化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對存在遺忘的諸個不同時代的歷史。此時海氏以對存在的歷史(Seinsgeschichte)的思考,取代了前期的基本存在論計劃。雖然海德格思考的課題仍是存在問題,但他思想的情感基調(Stimmung, mood)由積極的本真自我之追求, 變成寧靜致遠的期待主義( attentisme, wait-and-see policy):人類──起碼是西方人──的救贖,要靜待「再一個上帝的到來」(“Nur noch ein Gott kan uns retten”, “Only once more a God can save us”)。海德格還間中引用老子「無為」和莊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論說,來支持自己「泰然任之」的態度。海德格這一舉動,被視為帶來了東西方哲學溝通的契機。
然而,在尼采(F. Nietzsche)宣佈上帝已死、在韋伯(M. Weber)宣告現代世界是一個已經解昧(disenchanted)的世界之後,海德格要我們「泰然任之」,靜待「再一個上帝的到來」,這一舉措是否重新向我們傳遞一種末世論和先知式的話語?「泰然任之」的態度,真的可以為現代人準備迎接下一個時代嗎?我們如何識辨哪一個時刻才是海德格心目中那「下一個時代」的到來?對這「下一個時代」的辨認,是出於客觀知識還是先知式的啟示真理?海氏的存在之歷史的歷史觀中命定論的性格,是否另一套歷史決定論?它與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式的歷史決定論有何分別?在海氏存在的歷史之思考下,一切倫理與價值問題都只是人類文明中的衍生問題,沒有存在之開顯的本源地位;而一切藝術活動,都只是為存在之開顯這一本源課題服務。在海德格晚期思想的框架中,人類文化生活內部的各種多樣的分殊樣態都沒有本質意義,它們之間的差異被取消,或被視為僅僅是衍生的,因而沒有重要性。
唯一重要的是存在與存在者之間這最基本的存在論差異(ontologische Differenz)。這是否回到了普洛提尼(Plotinus)新柏拉圖主義的「純一」(the One)式思維?25 這一思維方式真能
有助我們理解當前人類的處境嗎?它真能有助跨文化的哲學溝通嗎?
圍繞海德格哲學的另一個有趣課題是:多位對海氏思想有正面評價和有所推進的重要歐陸哲學家,如沙特、梅洛龐蒂、德里達、傅柯等,都是二次大戰後在德國以外崛起的學者;反之,海氏最早期的一批原籍德國的猶太裔學生,如洛維特(K. Löwith)、馬庫塞、約納斯(H. Jonas),和亞蘭特(H. Arendt)等在現象學運動邊沿、後來卻都成為獨當一面的哲學家,對他們早期這位極具魅力的老師之思想,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以至批判的態度。我們在了解海德格的哲學遺產之際,對這現象不也是應該一併考慮嗎?
海德格研究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本專輯雖然只能探討箇中部份問題,但不失為兩岸三地漢語哲學界一次可貴的集體努力。
編者序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海德格哲學的閱讀與理解,經歷了數次重要轉變。在20 世紀50、60 年代,海德格被視為存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一個重要代表,而初版於1927 年的海氏成名作《存在與時間》,則被理解為一部深刻剖析人之存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巨著。然而,這一理解方式並不為海德格本人認同。早於1946年發表的〈論人文主義書簡〉中,海德格已明白表示,他探討的主要課題既非沙特(J.-P. Sartre)所強調的「存在先於本質」,《存在與時間》更與存在主義的前提毫無關連。 固然,海德格在該信及其後的著述中多番申明,他終身探索的問題...
目錄
編者序 : 如何面對海德格的思想遺產? 劉國英
1.傳統語言與技術語言 海德格 著 靳希平 譯
2.佇立時間邊緣的希臘神殿 張鼎國
3.通過《老子》第11 章重新理解《存在與時間》 張祥龍
4.從亞里士多德思想來詮解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 汪文聖
5.《存在與時間》的「存在論」概念與傳統形而上學 梁家榮
6.梅洛龐蒂錯解海德格? 劉國英
7.本己與他者──《存在與時間》中的他者概念的現象學定位 吳俊業
8.海德格《存在與時間》對「他人共在」(Mitsein)的探討 王耀航
9.「誰是此在?」——同等本源的本真性與非本真性 黃浩麒
10.無:從《存有與時間》到《哲學文獻》 姚治華
11.從《存在與時間》到「時間與存在」 柯小剛
12.是與易——道之現象學導引 丁 耘
13.為什麼這種物化一再取得統治? 呂炳強
14.萊維納斯對《存在與時間》的依附和批判 孫向晨
書評
解釋還是挑戰海德格?評賈尼科的《海德格在法國》(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Paris: A. Michel, 2001)
編者序 : 如何面對海德格的思想遺產? 劉國英
1.傳統語言與技術語言 海德格 著 靳希平 譯
2.佇立時間邊緣的希臘神殿 張鼎國
3.通過《老子》第11 章重新理解《存在與時間》 張祥龍
4.從亞里士多德思想來詮解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 汪文聖
5.《存在與時間》的「存在論」概念與傳統形而上學 梁家榮
6.梅洛龐蒂錯解海德格? 劉國英
7.本己與他者──《存在與時間》中的他者概念的現象學定位 吳俊業
8.海德格《存在與時間》對「他人共在」(Mitsein)的探討 王耀航
9.「誰是此在?」——同等本源的本真性與非本真性 黃浩麒
10.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