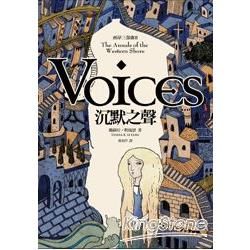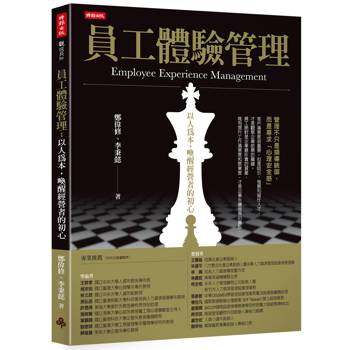再現「地海」的壯闊與美好
娥蘇拉‧勒瑰恩嶄新奇幻之旅
話語文字的刀刃,有時比刀劍武力更為鋒利。
阿茲人用武力輕易毀滅安甦爾城,然而,話語文字的力量何以令他們恐懼?
安甦爾城,人稱「慧麗安甦爾」,城中聳立孕育知識的大學、保存文化與智慧的圖書館、壯麗宏偉的高塔建築,以及千百座大理石建造的大小神廟。安甦爾深受神諭眷顧。
然而,現在的安甦爾,是一座到處斷垣殘壁,充斥飢餓、恐懼與絕望的破敗之城。入侵的阿茲人認為文字是邪惡的魔法,藏書萬千的安甦爾城更是罪無可赦。
玫茉系出高華氏系,解讀神諭、為安甦爾城指點迷津本該是高華家的職責,但神諭沉寂已久。十七年來,玫茉學習閱讀祕室中最後的藏書,文字滋潤她的心;但家園被毀、親人受盡折磨,讓她心中仇恨不斷滋長;她只知道,阿茲人是永遠的敵人,她要殺光阿茲人。
知名的詩人歐睿久聞安甦爾文風鼎盛,他受阿茲人之邀,與妻子馴獸人桂蕊一同到來。阿茲人雖視文字為惡魔,卻熱愛詩人講述的故事,意料不到的是,歐睿講述的故事不僅娛樂了阿茲人,也擾動了潛伏於安甦爾城底下的暗流。
安甦爾人失去信仰與文字,在被壓迫的沉默中度過十七年。
延續已久的仇恨與戰爭,該如何結束?
沉默了二百年的神諭,何時會再重新發聲?
當你被迫面對深惡痛絕的敵人,竟發現他們並不全然殘忍可恨,你該視而不見地對他們採取報復手段,或是說服自己忘卻仇恨、寬恕敵人?
勒瑰恩《沉默之聲》如她以往的作品恬淡、優雅,但也為族群衝突頻傳的世代提供了一種解釋,唯有盡可能地了解、認識,才有和平共處的可能。
本書特色
西岸的故事從遺世獨立的高山地區來到海邊的大學城安甦爾,整個氣氛突然繽紛了起來。我們姑且擱下情節,你可以看到曾經繁華的宅邸,還可以跟著假扮男裝的少女玫茉一起到熱鬧的市集購物,買魚、買青菜,一邊還要計算家裡人口得吃掉多少食物。
但稍稍拉近鏡頭,你會發現宅邸破敗,曾遭人蓄意毀壞;市場裡沒有女人,倒是有高高在上的異族士兵梭巡。表面的平靜底下,蘊藏著阿茲人對未知的恐懼,以及安甦爾人對壓迫的隱忍。
阿茲人雖然武力強大,成功地在物理條件上完全壓制了相對來說溫文儒雅的安甦爾,但在骨子裡,他們不識字,甚至害怕文字,而恐懼又因為未知而一再自我強化。他們表面上統治了安甦爾,但內心永遠不安。
而安甦爾人,若以玫茉為代表,她當然痛恨異族統治者,不曾想過阿茲人身上可能有任何可取之處。直到喬裝成馬童,陪詩人歐睿進入阿茲人宮廷,被思鄉又渴望友誼的阿茲少年西姆纏上,她才發現阿茲人也是人,不是什麼張牙舞爪的野獸。西姆和所有青春期的男孩一樣,滿臉青春痘、對性好奇,甚至還有點愚蠢,看在冰雪聰明的玫茉眼裡實在庸俗得緊,「他表情迷惑。他經常表情迷惑。不管是誰,這麼迷惑的人,似乎不好占他便宜。但,占便宜的誘惑卻幾乎無法抗拒。」但也因此,玫茉心中那道線條分明的界線模糊了。
《沉默之聲》最厲害的元素,或許就在於它怎麼從「非黑即白」切入有各種階調的灰。歐睿相信所有人的內在都有美好之處,而玫茉則是被迫了解她深惡痛絕的入侵者,她漸漸了解入侵者雖然毀了她的家,但並不全然殘忍可恨,他們有時候只是天生和她不一樣,不了解她的生活方式。或許可以說,就算面對你討厭的人,與其報復,試著了解或許會發現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勒瑰恩的《沉默之聲》如她以往的作品一樣恬澹、優雅,但也為這個族群衝突頻傳的世代提供了一種解釋,唯有盡可能地了解、認識,才有和平共處的可能。
作者簡介: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美國重要奇幻科幻、女性主義文學作家,1929年生。著有長篇小說20餘部、短篇小說集10本、詩集7本、評論集4本,已為兒童、青少年創作逾40部作品;並編纂文選與從事翻譯,包括將老子《道德經》譯成英文。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號角書獎、紐伯瑞獎、世界奇幻獎、軌跡獎、星雲獎、雨果獎、小詹姆斯.提普翠獎、卡夫卡獎、普須卡獎……等,以及SFWA大師、洛杉磯時報Robert Kirsch終生成就獎等榮譽。此外亦獲頒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資助,由「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負責遴選之「The Margaret A. Edwards終生貢獻獎」。
她的奇幻成長小說系列「地海六部曲」與「魔戒」、「納尼亞傳說」並列奇幻經典,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等也是科幻迷心目中永遠的經典。小說探討的議題,從自我成長與認同,到社會制度探討與性別問題,都鞭辟入裡,在優美恬澹的敘事風格中予人寬廣深沈的省思空間。西洋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將她列為美國經典作家之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是她的書迷。
她目前住在美國奧瑞岡州波特蘭市,仍持續於其個人網站發表各種文學評論與創作心得:www.ursulakleguin.com。
譯者簡介:
蔡美玲
英國University of Reading「兒童青少年文學」碩士。曾任主編及大學講師。青少年小說譯作有《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地海彼岸》、《天賦之子》、《44號神祕怪客》、《河豚活在大海裡》、《妖精的孩子》、《地鐵求生121》、《史庫樂街十九號》、《凱希的空間》、《薇拉的真愛》、《敏娜的琴音》等;心理學書籍《愛孩子,愛自己》、《了解人性》等;並參與編寫家扶自立青年故事集《光明行》、社工服務合集《與你同行:家扶社工的故事》等兒童福利相關書籍。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美國「合作童書中心」CCBC特選優良書籍
★勒瑰恩的絕頂表述與敍事本領,就連最微不足道的那許多瞬間,也有真理振盪,而且富含美感。│《學校圖書館雜誌》重點書評
★依舊是……很好看。勒瑰恩的語言兼具通達與美感,她的種種關懷,氣勢非凡,深奧睿智。│《華盛頓郵報》書評
★《沉默之聲》和勒瑰恩的前作《天賦之子》是以有機的方式相互匹配;它們所探討,關於復仇、家族傳承、個人道德等主題,也相互呼應。本書不可思議的人性馨香,更多著力於塵世的奧祕,較少傾注於電光火石的巫術表演……占領者與被占領者之間的文化衝突,徐徐惡化,作者恰到好處的火候,不可錯過。│《書單雜誌》重點書評
媒體推薦:
美國「合作童書中心」特選優良書籍
《學校圖書館雜誌》、《華盛頓郵報》、《書單雜誌》
好評推薦
得獎紀錄:★美國「合作童書中心」CCBC特選優良書籍
★勒瑰恩的絕頂表述與敍事本領,就連最微不足道的那許多瞬間,也有真理振盪,而且富含美感。│《學校圖書館雜誌》重點書評
★依舊是……很好看。勒瑰恩的語言兼具通達與美感,她的種種關懷,氣勢非凡,深奧睿智。│《華盛頓郵報》書評
★《沉默之聲》和勒瑰恩的前作《天賦之子》是以有機的方式相互匹配;它們所探討,關於復仇、家族傳承、個人道德等主題,也相互呼應。本書不可思議的人性馨香,更多著力於塵世的奧祕,較少傾注於電光火石的巫術表演……占領者與被占領者之間的文化衝突,...
章節試閱
與 勒 瑰 恩 聊 天
問:《沉默之聲》中,玫茉主張,故事,而非歷史,給了她「所需及所盼的諸多真理:關於勇氣、友誼、忠誠的真理。」有的人將故事與歷史看作相同,只不過歷史是個別故事的集合。您認為──至少在玫茉心目中,歷史與故事的分界線在哪裡?
勒瑰恩:我不覺得玫茉對歷史與故事做了什麼或深或淺的分別;她只是喜愛閱讀歷史與故事之類的內容而已。玫茉閱讀的一大堆詩作和故事,其實是歷史;還有一大堆是神話;也有一些同時就是歷史與神話──對多數歷史而言,的確就是這樣,既是故事,也是神話。
問:玫茉漸漸相信,話語一旦誤用和扭曲,就失去了它們的意義。竭力還原其真實的必要責任,在詩人身上。以您之見,詩人與小說家是否為讀者提供不同的真理;或者,他們只是以不同方式去接近相同的真理?
勒瑰恩:詩與小說使用文字的方式有點不同,但它們都是想嘗試述說可能根本無法述說的不同事物。或者你也可以這麼說:藝術不是「談」真理,它是「製造」真理。
一般人肯定能藉由詩或故事,而認識──或再認識──「他們的真理」,但,其意義終歸在於,詩或故事所追尋的真理,是否擺脫了扭曲的含意,擺脫了半真理,擺脫了謊言或廣告。
問:《沉默之聲》中一個重要的主題是,讓人思考好過給人一清二楚的答案。您希望本書的讀者去深思什麼特別的主題呢?
勒瑰恩:《沉默之聲》涵括很多主題,只是,並非所有主題都一望即知。坦白說,我寧願不把它們挖出來加以剖析。教師與學生比我更擅長分析各項主題;所以,就留給他們詮釋吧。
其中有個相當明顯可見的主題,是針對「暴力」的辯論。何時須使用武力?在有力又正確的情感驅策下,何時採取激烈行動才是正確的行動?為了遏制暴力,什麼時候該遏制情感,才是較佳的選擇?如何知道何時爆發反叛才是對的?你如何說服自己,暴力或反叛可能是愚蠢、殘酷、無用的──即使「真理」很明顯是在你這邊?這些是多數年輕年必須經由不同方式去面對的問題,不管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都一樣。
問:說故事的力量──不論是向群眾大聲朗誦,或私下展讀古代讀物──是《沉默之聲》中的一個關鍵概念。您何時開始領會,您天生是說故事的料?您童年時代,哪些書籍激發了您,或進一步激起您編織故事的欲望?
勒瑰恩:如同億萬個別人家的小孩一樣,從小,夜晚躺在床上,我就開始對自己說故事了。我猜,我比多數小孩更需要故事,而且長大後依然把它們當作理解身邊人、事、物的一個途徑。走進虛構世界,幫助我在這個所謂真實的世界,找到我的路。以前讀過的所有圖畫書,都激勵甚至指引我日後這許多的探究──至今仍是。
問:您相當多產。除了小說,您也寫詩,還創作短篇故事、圖畫書。您每次同時處理一個以上的寫作計畫嗎?關於持續專注於日復一日的寫作工作,您有任何忠言與我們分享嗎?
勒瑰恩:我實在太多產了,有時我感覺自己像正在產卵的鮭魚呢!我不但多產,而且迷信──從未清點我到底已經出版幾本書了。
假如我正在寫的是小說,那麼,通常我就整個投入那部小說的寫作一段時間:幾個月、一年,或更久一點,以便完成那個寫作計畫。不過,寫小說的同時,我還能寫詩和非小說。短篇小說很需要突然爆發的大量精力,才能快速寫完,這很像《小婦人》裡面,喬所稱的「旋渦」。一個時間有限的人,短篇故事似乎是最實際的類別嘗試,但同時,短篇故事也可能最難寫,因為,突然爆發的能量無法打破成碎片。小說則以它自己的衝力穩步前進,而且可以分為好些短的小節來寫,不得不停時,就停,第二天再接續。
我不曾聽過舞者徵求忠言,請教別人如何專注於足下功夫;也不曾聽過畫家抱怨日復一日的繪畫工作太無聊。哪一種值得做的工作不值得每天為它努力付出呢?你認為,米開朗基羅躺著畫西斯汀大教堂的天花板時,是鬧著玩的嗎?
無論如何,作家的情況怎麼樣呢?一旦做得夠久,累積了一些技巧之後,創作任何一種藝術或工藝都能給你持續的滿足。那種滿足很少是一種令人興奮、即刻的報償。很少會有一個時刻說:「噢,哇,瞧,我剛創作了一件傑作!」
下面我要很腳踏實地說,假如你必須找到一些妙招來哄騙你持續專注於寫作,那麼,你可能不應該繼續寫你正在寫的東西。還有,假如這種「缺乏動機」是個經常性的問題,那麼,寫作可能不是你的特長。我是說,問題出在哪裡?假如寫作讓你厭煩,那就很嚴重了。假如你的情況並非這種,只是你發覺自己很難進展,你覺得它就是不源源不絕地流動。噯呀,你原本期待的是怎樣啊?這是一種工作,藝術是工作。沒有人說過它是容易的,他們說的是:「人生苦短,藝術恆長。」
問:您以六部「地海系列」的創作者馳名。關於展望及發展新系列的相關故事群組,您如何進行?著手一部小說時,您是否預先計畫作品角色未來將發生的事件?
勒瑰恩:但願我能說,有;但其實沒有。是故事自己在編織自己,它們這樣做的時候,彼此的關連自然會漸漸讓我明顯看見。不過,當我說「編織自己」時,並不是說,就在我寫作時,故事與它們的關連就出現了──雖然有時候也會這樣。我意思是說,我下意識日夜思考;而那個寫作的我則始終埋首於:再來誰做什麼、為什麼那樣做。但,那並非「計畫」,也不是「發展」,過程不是那麼理性而且受操控。它是暗中摸索、發現、出錯、回頭再想、看出關連、想像這故事有可能往哪裡去,以及一下子說「噢,不」,一下子又說「啊哈!」假如這個下意識的工作進行順利,那麼,有時我坐在鍵盤前,故事很輕易就出來了──它「編織自己」。若非此種情形,那就變成是:動手,然後停手,然後陷入泥沼,動彈不得。若發生這種情況發生,我大概會花兩個鐘頭寫十行字,接著,按下「清除鍵」。
問:《天賦之子》中的兩個主角,歐睿與桂蕊,在《沉默之聲》中又出現,而且對安甦爾的百姓有深遠影響──包括玫茉。在「西岸」系列的下一部《Powers》裡,我們會再聽到更多玫茉的故事嗎?
勒瑰恩:噢,會的,我們都會再聽到。在書尾,玫茉會出現,歐睿與桂蕊也會出現,那頭半獅也一樣。我很高興能把他們找回來重聚!
【第三章】
即使是十年之後的現今,還是很難老實寫出我當年如何欺騙了自己。但若要寫出我的勇氣,困難度也同於寫出我的懦弱。不過,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盡可能真實;希望它成為「神諭宅邸」的有用紀錄;我也希望藉這本書來榮耀母親狄可蘿──這本書的正是獻給母親的。我盡可能把那幾年的記憶釐清順序,這樣才能找出該從哪裡把我第一次遇見桂蕊的情景說清楚。然而,在我十六、七歲的腦袋和心裡,卻沒什麼秩序可言。當時有的,全是無知,還有激烈的憤怒與愛。
當年我若有什麼平安詳和、有什麼理解領會,都是來自我對通路長的愛、他對我的好,以及書本。在我正執筆的這本書裡,「書籍」是它的核心。書本使我們置身危險,書本害我們冒了許多風險,但,書本也給了我們力量。阿茲人害怕書本是對的。假如有那麼一位「書神」的話,肯定就是「建造者與摧毀者山帕」了。
通路長讓我閱讀的書籍當中,詩篇的話,我最愛《轉化》;故事的話,我最愛《萌華列王故事集》。我知道故事集就只是故事,不是歷史,但它們給了我許多當時我需要而且想要的真理──關於勇氣、友誼、効死、抵抗並驅逐族人。十六歲那年的一整個冬天,我都去祕室閱讀阿德拉與瑪拉兩位英雄之間的友誼。我渴望擁有一個像阿德拉那樣的友伴,與他一同被趕入甦爾山的雪地,與他在那兒一同受苦,然後與他並肩出擊,撂倒斗芬人,把他們趕回自己的船上──那些內容,我一讀再讀。我展讀這位古代甦爾王的事蹟時,宛如看到通路長──深膚色、瘸腿、高貴、無畏。在我居住的城市裡,與我有關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生活,都充滿恐懼與不信任。每天在街頭見到的景象都讓我的心退避畏縮。我對萌華英雄們的愛,提供血液給我的心臟。我對他們的那份愛,賦與我力量。
就是那一年,我們把流浪女波米帶進家裡,通路長在宅邸的祭壇前,以古代儀禮將「高華」這個姓氏送給她。她入住莎絲塔房間那條甬道走到底的房間。她做事又認真又規矩,多數時候連依思塔都滿意;而且,她也是很好作伴的人。她約莫十三歲,對於自己何時出生、誰是她母親,完全不清楚。起初她在我們住的那條街附近晃蕩,乞討維生一陣子。後來,顧迪開始招呼她進家裡來,把她當成走失的貓咪一樣哄著。等到顧迪終於成功讓她在院子的小屋睡覺,顧迪也開始要她協助清理馬廄換取食物,馬廄裡有很多燒毀的木料和損壞的廢家具。顧迪堅決認定通路長將重新養馬。「這是有道理的呀。」他會說:「一個通路長遊走四方,怎麼可以沒有座騎?你們要讓他走路嗎?一路走到宜桑梗或多摩嗎?他那兩條腿怎麼成?要他像普通小販那樣,毫無尊嚴嗎?不行。他需要馬匹。這是有道理的呀。」
碰到顧迪這個人,誰都拿他沒輒,只能同意他所說的。他年紀大了,性情古怪,又駝背,雖然不一定總是擔任最有用的職務,但他工作一向極賣力。即使嘴巴壞,但他有顆清淨之心。依思塔僱用波米取代我,開始負責屋內清潔工作之後,顧迪很火大。他發火倒不是針對依思塔,而是針對波米──因為波米「遺棄」了他、也遺棄了他珍愛的馬廄。一連好幾個月,只要見到波米,顧迪就以她祖先的亡靈來詛咒她。其實,那詛咒對波米沒有什麼作用,因為她不認得半個祖先,也不曉得他們的亡靈在哪兒。後來,等顧迪的氣頭消散,波米只要做完分內家務,就回去幫他忙──就是那個清理、重建馬廄的可怕任務。因為,波米也是有顆清淨之心。如同最初顧迪把她帶進家裡來一樣,波米如法炮製,也把流浪貓帶進家裡來。那年夏天,馬廄的院落擠滿了小貓。依思塔說,波米吃東西好像十個女孩,我個人則以為,她吃東西,像一個女孩,外加二十隻貓咪。不管怎樣,馬廄最後總算清理乾淨了。事後看來,即使繁重的清理工程未必那麼有道理,結果畢竟還是招來幸運。而且,我們家再也沒有半隻老鼠了。
依思塔花很長時間才接受通路長把我納入他的特別管轄之下;也花很長時間才接受我正在「受教育」。講到「受教育」這種字眼時,她總是非常小心,彷彿那是別種語言。而確實,在阿茲人的管轄之下,說這話是要小心沒錯,因為他們認為閱讀是一項明知故犯的惡行。因為擺明著有那種危險,而且就如她所說,也因為她自己早已忘記小時候大人教了她什麼雞鴨魚鵝,所以,對於我日漸變得知書達禮這件事,她就是不大舒服。(「說嘛,我倒是問問妳,學那麼多,對於當個廚子到底有什麼用處?用筆和墨水要怎麼製造醬料,妳就作給我看看,行啊!」) 不過,叨念歸叨念,她從來不想拿這件事來反抗我,也從來不想質疑通路長的判斷或意願。想來,我之所以深愛「忠誠」,說不定就因為我知道,這宅邸是受「忠誠」所祝福的。
不管怎麼說,我仍然協助依思塔做廚房的粗活,也依然上市場採買──波米如果有空,就與她同行;如果她沒空,我就獨自前往。那陣子,我的體型依然矮小骨感,若穿上改短的男人衣服,看起來還相當像個小孩,或者,起碼也像個不起眼的少年。在街頭廝混的少年有時看出我是女孩,會用石頭丟我──安甦爾的我族少年,行徑就像卑劣的阿茲人。我討厭經過他們旁邊,所以總是遠遠避開他們聚集的地方。我也討厭神氣活現的阿茲衛兵在每個市場周圍站哨,說是要「維持秩序」。所謂的維持秩序,就是欺凌市民,就是不付錢而從小販的攤子拿走他們喜歡的任何東西。要是經過他們,我都盡量不顯出畏縮的樣子,盡量慢慢走,忽略他們。藍斗篷、皮護胸,加上刀與棍,他們一個個盛氣凌人地站在那兒,很少向低處看──低到像我這麼矮的高度。
好了,這就要講到那個重要的早晨了。
時為晚春,我十七歲生日過後四天。沙絲塔預定夏季結婚,那陣子,波米忙著協助沙絲塔縫製婚禮的行頭,包括新娘的綠袍和頭飾、新郎的外套和頭飾;一連數週,依思塔和莎絲塔談的盡是婚禮、婚禮、婚禮;縫製、縫製、縫製。甚至連波米也是繞著相同的主題叨念不已。我自己是連想都沒想過要學縫紉;也沒想過要戀愛、要結婚。有一天吧,將來有一天,我自會準備好,去尋找那種愛,但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必須先找出我是誰,這是首要之事。我有個諾言待實現,我有親愛的通路長讓我去愛,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去學習。因此,那天早晨我獨自前往市場,讓她們留在家裡繼續討論。
那是個燦亮甜美的日子。我步下宅邸通往神諭噴泉的臺階。噴泉的綠色大淺盆裡沒有水,只有垃圾;淺盆中央的雕塑已毀損、破裂,掉落在送水進噴泉的水道裡,鋸齒狀的碎片堆堵塞住水道。這個噴泉在我來到世上之前很久就已乾涸,但我照舊站在噴泉旁,向「泉與水之主」誦念祝禱之辭。而這一回也如同之前的每一次一樣,我總是很想知道,為什麼這個噴泉叫做「神諭之泉」;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高華世系本身有時候被稱做「神諭宅邸」。我心想,這件事應該問明通路長才是。
我的視線從那個已死的泉噴抬起,掠過全城,看見海峽對面的甦爾山,有如岩石與白雪共同鑄造的滔天巨浪。它的峰頂有一道雲霧向北方吹去。我想著阿德拉與瑪拉,偕同麾下疲累至極的士兵被逼到那冰凍的高峰之上,沒有糧食和火,他們跪下來讚頌山神與冰河眾神靈。一隻烏鴉飛來,將嘴中所銜的帶葉樹枝放在阿德拉面前。眾人謝過烏鴉,把僅餘的一點點麵包奉獻給牠。「鳥喙如黑鐵;恩賜綠希望。」我的心思總離不開那些英雄。
我讚頌甦爾山,以及從海岬之外僅可見白色頂峰的修昂山,接著,向地基石誦禱;經過巨石角,左轉至西街時,我摸摸街神的神龕,決定今天到港口市場採買,雖然它比山腳市場遠,提東西回家得多走些路,但它比山腳市場好。我很高興來到戶外,很高興看著陽光將藍綠色照進運河,很高興看見陽光把幾座橋上的雕像照出亮眼的影子。
陽光與海風令人愉快。我走著走著,愈來愈確定我的眾神明與我同在。我無所畏懼了,走過那幾個在市場邊站崗的阿茲士兵時,覺得他們彷彿是幾根木樁而已。
港口市場鋪了大理石地板,面積寬廣,北側和東側有海關大樓的紅色拱廊,南側有「海將塔」,西側向港口與大海開放。淺而長的大理石階有雕刻的曲欄搭配,石階最下層銜接海軍大樓的船屋以及碎石海灘。那天早上,處處是陽光、海風、白色大理石、湛藍海洋。不遠處有市場攤位五顏六色的遮篷和傘蓋,以及歡暢的市場喧鬧聲。我從市場神旁邊走過,市場神是一顆圓石,代表本城最古老的神明「樂若」,這名字代表公義、協同、正行。我坦坦然向這位神明敬禮,甚至沒想到阿茲士兵就在附近。
那是我這輩子從未有過的舉動。十歲那年,我目睹幾名士兵當街毆打一個老人,地點就在老人剛剛致意過的神明臺座下方,老人血流如注、不省人事,被棄置街頭。士兵在時,沒人敢靠近老人,我哭著跑開,始終不知道老人究竟被打死了沒有。我一直忘不了那件事,但沒有關係,這天,我一無所懼,這是個受祝福的日子,一個神聖之日。
我繼續前進,穿過廣場,每樣東西都瞧它一瞧,因為我愛這些攤位,我愛百物雜貨,我也愛那些誘哄顧客出手購買的攤販,以及說話粗俗無文的攤販。我的目標是魚市,但見到海將塔前正在搭一個大帳篷,便走過去,問一個販售髒岩糖的小僮那帳篷要做什麼用。
「從高山區來了一個偉大的說書人,」他說:「很有名的哩,我可以幫你占個位子,小少爺。」人家都說,就算是一堆大便,市場小僮也有能耐把它變成一個錢子兒。
「我可以自己占位子。」我剛說完,他就說:「噢,很快就會爆滿的啦──他預定在這裡停留一整天,有名得要命──半便士給你一個靠近的好位子如何?」
我對他笑笑,繼續前進。
不過,我還是上鉤了,被吸引到帳篷邊。我感覺想做點什麼蠢事──比如聽說書人講故事就是一樁。阿茲人對詩人和說書人很瘋狂。據說,每個富有的阿茲人隨扈裡都會有一名說書人;每個兵團裡也都會有一個說書人。我聽通路長說過,阿茲人來之前,安甦爾城裡沒有很多說書人,可是如今書籍被禁,說書人反而多了起來。我的族人裡有幾個男人會在街角講故事,賺點小零錢。我曾經駐足聆聽一、兩回,但他們大多講阿茲人的故事,才能從阿茲士兵那兒賺幾文錢。我不喜歡阿茲人的故事,全是關於戰爭、戰士、以及他們那位暴虐之神的故事,沒一個是我想聽的。
吸引我的是「高山地區」這幾個字。高山地區來的人不會是阿茲人,因為高山地區在很遠很遠的北方。以前,我聽都沒聽過高山地區,也不曾聽人提及遙遠北方的任何一塊土地。直到去年,我讀了埃朗撰述的《大歷史》,書中附有「西岸」所有土地的地圖。市場小僮只是重術別人講的話述,他並不明白那幾個字的意義,頂多曉得那是是離這裡很遠很遠的地方罷了。甚至對埃朗本人而言,高山地區的種種想必大多也僅限於風聞。我經過補鍋匠,繼續往賣魚婦的攤位前進,一邊試著回想那幅地圖,卻只記得地圖裡的高山地區有一座大山──我想不起來那座大山的怪名字。除此之外,我不記得其它。
我討價還價買了一條大紅斑,想必足夠全家人今天吃,甚至貓咪們也有分,魚頭還可以留到明天煮湯。我繞過攤位,買了一塊新鮮乳酪,以及一些賣相不差的便宜蔬菜。準備起程回家之前,我轉去大帳篷那邊,想看看是不是已經有什麼動靜了。群眾滿滿的。人頭鑽動之中,可以看見有騎馬的人鶴立雞群,馬頭上上下下擺動。那是兩個阿茲士官。阿茲人沒把女人從沙漠帶來,倒是帶了漂亮的好馬來。阿茲人善待馬匹,以至於有個街頭笑話戲稱那些馬匹為「士兵的老婆」。
群眾中有人想讓路給那兩匹馬,但後頭好像有什麼騷動和混亂。這時,其中一匹馬尖聲長嘶,先是衝撞,接著用後腿人立起來,繼而又像小雄馬般四腿僵硬地跳動。站在我前方的群眾為了閃躲,猛然後退。於是,那匹馬就朝我直衝而來。我後方有群眾簇擁著,我動彈不得,而馬匹對準了我──騎馬人已經不在馬背上,馬匹的韁繩連枷似地鞭打我的手。我伸手抓住韁繩並用力拉。馬低下頭,位置剛好在我肩膀一側,一隻眼睛狂野地轉動著。那個馬頭,看起來真是巨大,彷彿充塞整個世界。我縮短韁繩,握住靠近轡頭的位置,並穩穩站定,不曉得還能做些什麼。馬兒想甩頭,那個舉動一把將我提離了地面,出於純粹的恐懼,我儘管騰空,卻沒有放手。馬兒從鼻孔噴出一大口氣後站定了──甚至還輕輕拱拱我,有如要保護我一般。
周圍群眾,呼喊的呼喊、尖叫的尖叫,當時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怎麼使他們別再驚動馬匹。「安靜,安靜。」我呆呆地對大呼小叫的群眾說。他們好像聽懂了似的,紛紛後退,空出馬匹後面的大理石路面。而就在那個陽光照射的白色地面上,剛才被重摔下馬的阿茲士官還嚇傻了靜躺著。他的不遠處站著一個女人,身旁還有一頭獅子。
女人和獅子並肩而立,她們一走動,空出來的路面範圍就跟著移動。四周幾乎鴉雀無聲。
在女人和獅子的後面,我瞧見一個類似四輪馬車的車頂。他們走向那輛馬車,群眾也隨之後退,白色路面有如變魔術般在他們面前展開。那是一輛有篷的小馬車,拉車的兩匹馬平靜站著,並沒有看向我們這方向。女人打開馬車後門,獅子跳了進去,消失不見時,尾巴彎曲成一個可愛的弧度。女人將後門閂好,隨即返回,雖然這次並沒有獅子同行,群眾依然為她後退讓路。
她走到士官身邊跪下,士官這時已坐起來,一臉眩惑不解。她對士官講了幾句話,起身向我站立的地方走來。我那時依然抓著馬兒,不敢鬆手。群眾後退時有一點推擠,害那匹馬再度受驚,用力拉扯轡頭想掙脫我的掌握,結果,掛在我手臂上的菜籃掉落地面,魚啦乳酪啦青菜啦,全部飛蹦而出,馬兒更是大受驚嚇,我抓不住牠了。但,那個女人在。她伸出一隻手放在馬脖子上,對牠說了什麼,牠搖搖頭,胸臆間好像有一股不滿,但牠終究站定了。
女人伸出一隻手,我把韁繩交給她。「做得好,」她對我說:「做得真好!」然後她又貼近馬耳,柔聲對牠說了些什麼,然後朝馬兒的兩個鼻孔吹進一點點她自己的氣息。馬兒於是吐吐氣,低了頭。我趕緊彎身撿拾地上那些買回去準備給家人吃兩天的食物,免得被踩爛或被偷走了。那女人看我急著往地面抓東西,先是用力拍一下那匹馬,也彎腰來幫我。我們把那條大魚以及青菜丟進籃子。人群中有人把乳酪丟給我。
「謝謝各位,安甦爾的善良百姓!」那女人以清朗的聲音說話,但帶著外地腔。「這個小男孩應該獲得獎賞!」然後,她對那個已經顛危危站在馬匹另一側的士官說:「隊長,這個男孩抓住你的牝馬。是我的獅子嚇著了她,所以我請求您原諒。」
「那隻獅子,對。」阿茲人說著,依然恍惚。他看看女人,再看看我,一會兒才探手到腰帶小包內,取了什麼東西出來要給我──是一個便士。
我正在幫菜籃拉緊扣帶,不想理他和他那一個便士。
「噢,真慷慨啊,真慷慨啊。」群眾交頭接耳,而且有人輕聲讚歎:「好個財源哪!」士官怒目環視眾人,最後才又定睛看著那女人。她站在他面前,手裡握著他馬匹的韁繩,。
「放開妳的手,別碰她!」他說。「妳──女人──是妳帶了那隻動物來──一頭獅子──」
那個女人把韁繩丟過去給士官,輕輕拍拍那隻牝馬,然後沒入群眾當中。這回,群眾都緊挨著她。一會兒,我看見四輪馬車的車頂慢慢遠離。
我心想,這時還是別引人注目才聰明,所以趁那士官登上牝馬馬背,我迅速轉身,走進舊衣市場。
被喚做「高帽子」的舊衣女攤販剛才站在凳子上觀看整場好戲。這時,她爬下凳子。「你很熟悉馬性,是吧?」她對我說。
「不。」我說:「那是獅子嗎?」
「管牠是啥。反正是和那個說書人一道的,還有他老婆。人家是這麼說的囉。留下來聽他講故事吧。據說,他是首席故事大王喲。」
「我得把這條魚帶回家去。」
「唷,魚可是不等人的。」她銳利的小眼睛定定注視我。「喏,」她說著,丟了什麼東西給我,我反射動作接了下來。原來是一個便士。這時,她已經轉身走開了。
我謝謝她。那個便士,我把它放在樂若神下方的空位中,那是人們留置各樣神賜物品的所在,窮人會去那兒找東西。我跟之前一樣,不在乎警衛是否看見我,因為我曉得他們不會看見。我離開了市場,朝西街方向前進。經過海關大樓高高的紅色拱廊時,我聽見得得馬蹄和轆轆車輪。那兩匹馬和那輛四輪馬拉貨車順著海關街駛來,獅女高坐在駕駛座。
馬匹停步,她開口問:「搭便車嗎?」
我猶疑了,差點謝謝她並回絕。但那天是異乎尋常的,之前可不曾發生半件異樣的事情,所以我不曉得如何是好。畢竟,陌生人向來讓我感到不自在,人總是讓我感到不自在。但,那天是受祝福的,而回絕祝福乃是作惡。我謝謝她,然後爬到她旁邊的座位中。
座位好像非常高。
「上哪兒?」
我指向西街。
她彷彿沒有任何動作──沒有像我見過的其他車夫那樣晃一晃韁繩、或動一動舌頭,但馬匹就是動了。比較高的那匹馬是順眼的紅棕色,幾乎和《若思坦》的封面一樣紅;比較矮小的那一匹是亮褐色,四腿、鬃毛和尾巴是黑色,前額有一撮星形白毛。兩匹馬都比阿茲人的馬匹高大許多,看起來也更為平和。他們的耳朵前後擺動,不間斷地聆聽著;這景象看了就讓人心情愉快。
馬車駛經幾個街區,我們都沒交談。從馬車駕駛座的高度俯瞰很有趣,我看見幾條運河、河上的橋梁、建築的立面和窗牖、來往的人群,還看見馬背上的騎者由高處往下看著行人。我發現,這情形讓我感覺自己是優越的。
「那頭獅子──後面那個──在馬車內?」我終於發問。
「她是半獅,混血的。」她說。
「來自阿蘇達沙漠!」她一說到「半獅」,我立刻回想起在《大歷史》裡讀到的內容和圖片。
「正確。」她說,瞥了我一眼。「可能就因為這緣故,她才惹毛了那匹牝馬。牝馬曉得她的身分。」
「但妳不是阿茲人。」我突然害怕起她會是阿茲人──儘管她長了深色皮膚和深色眼睛,不可能是阿茲人。
「我是從高山地區來的。」
「那地方在最北邊!」我說完,差點沒把自己的舌頭咬成兩截。
她斜睨我一眼。我等著她控訴我竟讀了書。但那卻不是她留意的重點。
「妳不是男孩子。」她說:「噯呀,我可真笨哪。」
「對。我穿戴成男孩樣子,因為──」我住口了。
她點點頭,意思是無需解釋。
「說說看,妳是怎麼學習御馬術的。」她問。
「我沒學。之前,我沒碰過半匹馬。」
她吹一下口哨。那哨音小小甜甜的,像隻小小鳥的叫聲。「唔,那麼,妳要不是抓到訣竅,就是運氣好。」
她的微笑那麼窩心,我不禁想告訴她那是運氣使然,是樂若神和好運神,也就是那位耳聾神賜給我一個聖日的關係,可是,我害怕自己太過多嘴。
「妳知道嗎,我本來是想,妳應該能帶我去一個不錯的馬房,給這兩匹馬休息。我原以為妳是馬僮。因為妳又敏捷又冷靜,不輸給我見過的任何一位馬夫。」
「噯,那匹馬就朝著我衝來呀。」
「牠是走向妳。」她說。
馬車又轆轆地經過一個街區。
「我們有個馬廄。」我說。
她笑起來。「啊哈!」
「我得問一下。」
「當然。」
「目前馬廄裡沒半匹馬,也沒有飼料,什麼都沒有。已經好幾年了。但是裡面乾淨。有一些麥桿,給貓咪用的。」每回我張口說話,總是說得太多。我咬咬牙。
「妳真好心。假如不方便,直說無妨。我們可以找別的地方。其實,統領已經說過了,我們可以使用他的馬廄。但我寧可不要蒙他們照顧。」她匆匆瞥我一眼。
我喜歡她,打從看見她站在獅子旁邊那一刻起,我就喜歡她了。我喜歡她說話的樣子,喜歡她說話的內容,喜歡她的一切。
祝福降臨時,萬勿拒絕。
我說:「我是高華世系的玫茉,狄可蘿高華的女兒。」
她說:「我是樂得世系的桂蕊貝睎。」
介紹完自己,我們都有些害羞,也就沉默地進入了高華街。「宅邸到了。」我說。
她敬畏地說:「真是一棟漂亮的房子。」
高華世面積龐大,氣勢尊貴,這棟宅邸有寬濶的院落,石造的拱門,挑高的窗戶;只是如今已泰半遭毀。因此,聽見來自遠方、見識過許多豪宅深院的人看出它的美,真教我感動莫名。
「這就是『神諭宅邸』,」我說:「通路長的住處。」
聽我這一說,馬匹猛然停住。
桂蕊茫然注視我好一會兒。「高華──通路長──嘿,馬兒,醒來呀!」兩匹馬於是繼續耐心前進。「今天真是大大出乎意料的日子。」她說。
「今天是樂若神的日子。」我說。馬車駛達臨街大門,我跳下座位,碰觸地基石,然後引領桂蕊入內,經過大前庭那個已枯乾的神諭噴泉,繞過宅邸側邊,來到馬廄院落的拱門前。
顧迪沉著臉出來。「看在妳那些笨祖先亡靈的分上,妳認為我到哪兒找燕麥來餵?」他大吼,一邊過來替紅馬解開馬具。
「等等,等等。」我說:「我必須先秉報通路長。」
「談你們的去吧。你們談的時候,牲口可以點喝水,不行嗎?來,放輕鬆,女士。這裡我會照料。」
桂蕊由著他為兩匹馬解套,然後牽去飲水槽邊。她看著這個老人打開水龍頭,目睹清水流入飲水槽。她很有興味地看著,滿臉讚賞。「這水是從哪兒來的?」她問顧迪,他於是滔滔不絕跟她講起高華世系的泉源始末。
我經過四輪馬車時,它振動一下。裡面有一頭獅子呢。我很好奇顧迪會怎麼說。
我跑進屋子。
與 勒 瑰 恩 聊 天
問:《沉默之聲》中,玫茉主張,故事,而非歷史,給了她「所需及所盼的諸多真理:關於勇氣、友誼、忠誠的真理。」有的人將故事與歷史看作相同,只不過歷史是個別故事的集合。您認為──至少在玫茉心目中,歷史與故事的分界線在哪裡?
勒瑰恩:我不覺得玫茉對歷史與故事做了什麼或深或淺的分別;她只是喜愛閱讀歷史與故事之類的內容而已。玫茉閱讀的一大堆詩作和故事,其實是歷史;還有一大堆是神話;也有一些同時就是歷史與神話──對多數歷史而言,的確就是這樣,既是故事,也是神話。
問:玫茉漸漸相信,話語一旦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