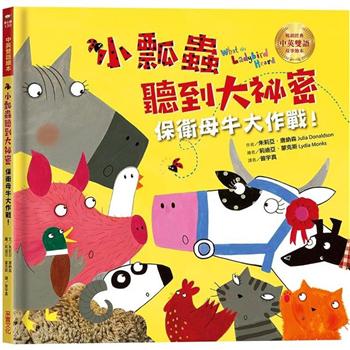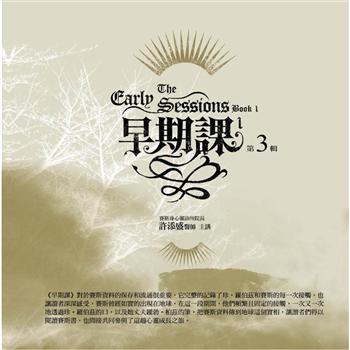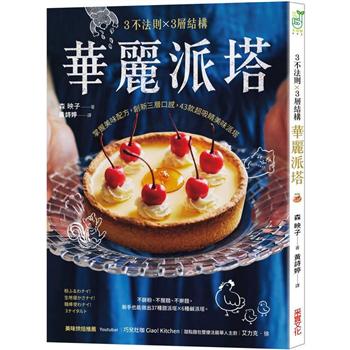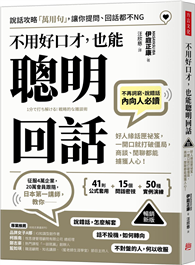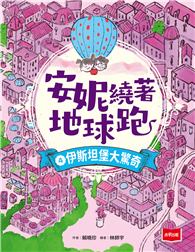得獎紀錄:
2010年曼布克獎決選作品之一
名人推薦:
甘耀明(作家)、伍軒宏(政大英文系講師)、柯裕棻(作家)、臥斧(文字工作者)、駱以軍(作家)、莎娣‧史密斯(《論美》、《白牙》作者,英國當今最重要青年小說家)
甘耀明(作家):
閱讀這本書像是一趟不攜帶氧氣設備的「自由潛水」(Free-diving)──吸一口氣然後挑戰能潛入幾米深。作者湯姆‧麥卡錫佈下的語言學關卡、細膩寫實與知識系統,往往「挑逗」讀者的下潛能力。別忘了,還有主角瑟吉的古怪經歷:聾啞、戰爭、冒險與性,也形成了閱讀上的引力。
只有閱讀到最深的結尾,讀者才從主角的病痛掙扎中發現,生命到頭來只有「愛的深刻」才是最棒的氧氣。那是抵達最黑最冷的深海往上一蹬的力量呀!也是這本書給人閱讀上最棒的一擊。
伍軒宏(政大英文系講師) 導讀
也許《C》看起來像是遲到的後現代作品,但它可能在支解與重組的過程中,釋放出無限延異的差異性。
柯裕棻(作家) 專文推薦
《C》內含一個不可言說的強烈慾望,與其說作者隱晦地書寫慾望,不如說他巧妙地以文字反寫它:文字一再遮掩或埋葬慾望。即使寫的是戰爭、性愛或飛翔,那高亢的場景也悲傷至極,哀痛的死慾如鬼魅從主角的心底瀰漫浮昇,讀者恍若聞見腐壤敗壞的氣息。
此書的文字本身即是加密的符碼,讀者若有心,可一一拆解作者的暗喻;若不執著於此,讓文字順眼流過,則是一個哀痛逾恆,難以言喻的故事。
悲傷密織於話語之中柯裕棻(作家)
收到《C》這本書的中文譯稿我立刻就打開來看了。過去這一年來在各英文報刊雜誌上看過很多關於此書的好評,我屢屢想買原書來看,卻又因書評講得玄之又玄,我沒把握,也就拖著沒下手。
一口氣讀完譯稿之後,我驚奇不已,一方面震撼於作者的才華和文學功力,另一方面也被這悲傷故事之後的隱喻魘著了,它彷彿緊緊掐住我的喉頭,我因為理解作者的隱喻密碼而啞口無言。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書評會不斷強調德希達的解構理論,我也明白了那些讚歎和推崇本書的實驗精神是為甚麼─都是為了這張口結舌的瞬間。我又仔細重讀一遍,並且上網買了英文版,以便中英對照再讀一遍─已經不知多少年我沒有這麼興緻盎然地精讀任何一本小說了。
因此這序也就特別難寫,我極力避免寫成那些令人望而卻步的書評,又不想道破作者的各種伏筆和佈局。這故事的敘事完整,它完全涵納了文學分析需要的理論元素和結構,可是它不玩弄形式,故事流暢,經得起任何小說讀者的細讀。書中才華洋溢的強力段落不勝枚舉。第一部分關於語言和電波的漂浮感以及第二部分關於飛行與墜落的描寫,筆力驚人,幾乎是拎著讀者一路翱翔翻飛。而第四部分結尾大膽,狂亂揮灑,寫幻覺和覺醒,從地底直上雲霄,尤其撼人。
《C》內含一個不可言說的強烈慾望,與其說作者隱晦地書寫慾望,不如說他巧妙地以文字反寫它:文字一再遮掩或埋葬慾望。即使寫的是戰爭、性愛或飛翔,那高亢的場景也悲傷至極,哀痛的死慾如鬼魅從主角的心底瀰漫浮昇,讀者恍若聞見腐壤敗壞的氣息。
故事的時間設在百餘年前,但這是一則關於現代的寓言,作者對於此刻人類現況的提問是:我們何以成為如此?他以科技、愛慾、語言三個主題交纏勾畫出一個哀傷的人生故事。故事始於無線電在英國成立的一八九七年,結束於英國廣播公司(BBC)成立的一九二二年。主角瑟吉生在通訊科技狂飆的十九世紀末,他的命運惘惘漂流在時代的電波之中,科技使他更通達,卻也更孤單,言辭和符碼使他更流暢,卻也更喑啞。那是個追求遠距傳播的狂熱時代,人類追求對話,渴望更多的理解,更多的言談、訊息和符號,穿越海峽和平原,最好也能穿越時空,穿透人鬼殊途的幽冥。人類渴望將話語傳送到遠方,卻又以同樣的科技將訊息加以鎖密,以防他人探聽。
全書的四個部分各安排幾個主導情節發展的時代科技和科學概念,這些科學理念籠覆著主角瑟吉和所有人的命運,他們捲進時代的颶風,那是金屬與炸藥、幾何與連結的新時代,不祥的科技將他們朝向未來拋擲,他們能留下甚麼呢?留下聲波和隱隱的能量在空氣間成為靜電雜音嗎?或是成為留聲機唱盤上的鬼哭刻痕呢?或者,誰的記憶能鐫刻在陵墓的石牆上永不斑駁?誰的愛情會在黑墨中光輝永存呢?
語言的可能與不可能是《C》的故事核心。語言能溝通思想,但也是思想加密的過程,是真相隱遁的路徑。語言能揭露、顯示、傳達、溝通、表示、說明,它也欺瞞、矯飾、曲解、掩蓋、扭轉、甚至虛構事實。我們不因言談而更誠實或赤裸,我們借語言文字閃躲並包裹真相。語言不使我們明白事實,反而使之晦暗難解。這故事是關於人心的加密,因此作者以典故、詩詞、同音字、同義字或複合字的陷阱來展現加密的工程。此書的文字本身即是加密的符碼,讀者若有心,可一一拆解作者的暗喻;若不執著於此,讓文字順眼流過,則是一個哀痛逾恆,難以言喻的故事。
書中沒有點明主角瑟吉的慾望,而是將之化為各種密語,潛伏在語詞的底層。慾望假借語言的誤差與變形,不時一明一滅閃現,如同暗夜墳坡的燐火,照亮了枯骨同時也點明了恐懼和憂傷。它每一次從潛藏之處浮現都更危險,更糾結。我們隱藏慾望的方式正如同我們的文明處理歷史創傷,即使燃犀洞照,也僅見亡靈幽物,鬼氣森森,不見真實。
逝者杳杳,現代文明以震耳欲聾的言說、修辭和話術,埋藏過去。或者,更沈痛的憂鬱是,這個時代其實不知如何妥善埋葬過去。這些科學和技術,話語和符號,都是我們想方設法讓過往的創傷留下。我們不讓它走,以各種方式提醒自己,慾望與傷痛同源。所有的傳播方式都是悼亡的儀式,傳播複製各種事物並掩飾時間的逝去,它留下的種種紀錄都指向主體的死亡。一塊墳碑上的銘文或一段電波上的話語,一柱電桿或一道圖騰,永遠面向未來的沈默,面向那言說主體終將消亡的喑啞虛空。
那麼,為何還執著於尋找希望的蛛絲馬跡呢?既然一個人已經無愛,也無任何溝通意願?也許,是為了能與死者長相左右,為了找尋通往死蔭幽谷的祕徑,因為此後,即是黑夜……
媒體推薦:
麥卡錫書寫絕技的每一段落都如同神祕、繁複的立體方塊拼圖,富於明顯、詳細的線索與一致性;有野心的讀者會一再重讀這沒有盡頭的可多樣解釋的世界,而普通讀者也會因為作者有企圖心地交織了科學與科學帶來的夢想的傳奇冒險故事而讚嘆。──《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本書內容如喬伊斯作品般宏觀而緊密,著實令人嘆服,麥卡錫能將之寫成結構明確俐落的故事,才華亦使人拍案叫絕……。--克里斯多福.泰勒《衛報》
一本手法精巧的成長小說……無論《C》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這都是一本美妙且不難理解的小說,故事精采刺激。這是今年最優秀的新書之一,而麥卡錫寫出本書值得我們大力讚譽,他筆下這部包羅萬象的作品,不只應該拿來享受、閱讀,也該仔細分析、討論。--貝絲.瓊斯,《每日電訊報》
《C》是鳳毛麟角般的稀世奇珍:一部前衛史詩,……是自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後我所能想到的第一部此類作品。……麥卡錫的風格注重行文的精確,而不墨守習以為常的文字美學。他筆下的畫布遼闊寬廣,包容性愛、毒品、戰爭、亂倫、自殺、情報工作與埃及考古學。無論他在書中把影響他的前人作品寫得多麼明顯,《C》讀來仍令人覺得耳目一新,我們很難再給與其他作品這種評價了。 --強納森.迪,《哈潑》雜誌
本書引人去解開它的密碼,相信許多讀者會覺得轉譯文中如印象派色彩般的「點」與「畫」樂趣無窮。--思嘉莉.湯馬斯,《金融時報》
湯姆.麥卡錫寫了一部前衛巨作--一個蔓延無邊的密碼--寫成史詩般描寫主角成長的歷史小說。……《C》將成長寫成哲學,將哲學寫成故事,將故事寫成「假墓」(也就是「真正的東西藏在後面」)--小說正是人生的密碼。--密罕.克里斯特,《洛杉磯時報》
〔閱讀本書〕像是參加夢中派對,派對主人學識異常淵博,讀過我很久以前讀過但忘了大半的東西、一直想讀卻沒讀的東西,還有我見識過麥卡錫如何妙筆生花之後一定會去讀的東西。--珍妮.透納,《倫敦書評》
他寫出了一部絕妙、複雜又有趣的小說,這是極罕見的事。出版界為了書本已死、文學的前景堪慮等說法焦慮無比--這些都是麥卡錫在本書字裡行間持續探討的主題--然而這部小說卻是活生生的,且無懼死亡。儘管《C》宣告著文學歷時最古老的期望已經終結,它也在高塔間嗡嗡哼出迭起的高潮。--班.艾仁賴亨,《國家》期刊
麥卡錫在《C》中的敘述策略跟瑟吉吸毒後的冥想十分相近--他將迥異的東西排成較大的圖樣,充滿反覆出現的畫面:人體與大地、機器互相類比;哼哼聲、唿唿聲;電影銀幕;肚腹與隧道;電路;圓帽與其他絲緞般的膜。--珍妮佛.伊根,《紐約時報書評》
很明顯,小說的劇情由片段組合成骨架,麥卡錫的各主題纏繞其上:電訊傳輸、反覆、平面空間、死亡與秘藏知識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終究無法完全溝通。這些主題絕大部分來自麥卡錫長期以來對法國文化理論的興趣,而他以非常高明的文筆加以展現。……除此之外,本書尚有許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強納森.貝克漢,《觀察家雜誌》
湯姆.麥卡錫寫了一部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小說:與眾不同,別出新裁,巧思機智敏銳,讀來妙趣橫生。--史都華.艾佛斯,《每日電訊報》
《C》無疑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以它絕無僅有、令人炫目的方式一窺現代主義,打擊我們這個保守時代慣用心理寫實的模式,深具效果……--尼爾.穆柯吉,《泰晤士報》
麥卡錫的作品將自身的故事及人類的文化回收反芻,形成,一部深具原創性的小說。--珊曼莎.韓特《華盛頓郵報》
《C》的魅力有部分仰賴瑟吉這個角色……與其說他是受限於道德力量,不如說他是摸索出路的反英雄。有時他顯得毫無生氣、機械化,令人毛骨悚然。在我們看來,他像是某種立體派畫風的拼圖……《C》是一部關於『認知』的小說。瑟吉一路追根究柢、探索調查,讀者也同樣必須抽絲剝繭,發掘本書主角與故事的秘密。--亞歷山大.舍羅,《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