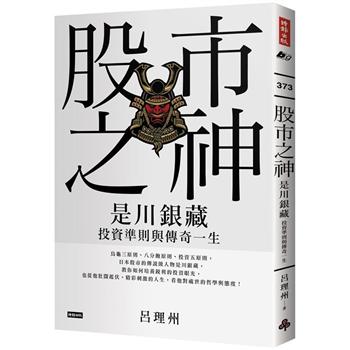在接下來的星期五,我們正式替樹屋揭幕。安東向我保證,像這種這麼小、又足以做為楷模的兒童建築創作,決不需要相關部門批准。他已經寫信向建築管理局說明一切,他還和青少年管理局以及警察局取得了聯繫,寄了封友好的信給貝克先生。在信中,他警告貝克先生的客戶,即亨姆佩爾夫婦,不得再發出損害名譽的報告和申訴,否則他的客戶,就是我,會對亨姆佩爾夫婦提出控訴,而根據法律條款,我無疑會控訴成功。從那以後,貝克先生就再也沒來信煩過我了。
綠化管理局則好好地研究了安東的信。有一天,一個姓朗浩司的先生就上門了,想對我家地產上的植被狀況做個記錄。我還沒搞懂這是福還是禍,他就把我家幾乎所有的樹都列為具有保護價值的植物,嚴格禁止我在無書面批准的情況下砍伐它們。只有病懨懨的紅杉樹我可以砍掉,這個朗浩司先生不會反對。
亨姆佩爾夫婦一直從他們的窺望窗口盯著這位先生的視察行動,開始的時候,他們歡欣鼓舞,但是當他們發現朗浩司先生完全沒打算砍光伐平我的園子時,他們一下子怒不可遏。
「嘿,我們寫信叫你來,是讓你來幹嘛的?」亨姆佩爾先生喊道。
亨姆佩爾夫人也尖叫道:「如果今年秋天,我們屋頂的水槽又被那些樹葉堵住,而我的海因里希在爬梯子的時候摔斷腿,我們就要你負責!」
「上週一,孩子們在這裡找到一隻蠑螈。」我說。我知道,從純粹的生態角度來看,一隻活著的蠑螈比一個快死的退休老鬼要有價值多了。
朗浩司想立刻向自然保護協會報告這件事。「在塞滿柏樹籬笆和桂櫻樹的城市大自然裡,這樣的花園可是最後的綠洲。」他說,「您真的應該覺得很幸福,繼承了這樣一片美妙而寶貴的植物。您們也是。」他轉向亨姆佩爾夫婦說。
亨姆佩爾先生有點詭譎地說:「我們家裡住著一個小孫女,她歡樂的童年就靠您憑良心關照了。」
「啊,說的是您吧。」我對朗浩司先生說。他完全被搞糊塗了。
無論如何,我們在週五下午慶祝樹屋的落成。實際上,慶祝的人主要是孩子們:馬克斯和娜妮,娜妮的朋友娜拉,尤利亞斯和雅斯帕。
我替他們烤了一個大蛋糕,配上沒有酒精的波列酒,他們把這兩樣東西用馬克斯自製的吊繩拉到三百五十公分高的屋中。為了慶祝首航,海盜船的大旗也拉開了,那是我請吉娣做的,黑色底上加一個交疊的白色骷髏頭,拼貼縫製技術無懈可擊。
這個樹屋蓋得非常漂亮,不像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造的。當我和安妮一起參觀的時候,我看著那些不可思議的細節,心裡清楚地知道馬克斯肯定已經瘋狂地愛上了娜妮,而且他很可能有著極高的天分,真正的天分。
那些被用來當作欄杆的樹枝,有一部分還有雕刻花紋,整體上看起來很簡樸,而且似乎不經意地迎合著娜妮的心思。就連馬克斯在屋頂上做出的假煙囪上頭的人臉,都和娜妮有幾分相似。在兼做艙房、城堡大廳和臥室的五角形小房間裡的一根屋梁上,以細小的字體刻著「心願如浮雲,靜靜空中行,熏風誰人識,夢影或幽情?」
「這句是歌詞嗎?」我問馬克斯。
他有點臉紅了,「是艾辛爾多夫的,」他說,「我們上課時讀過。」
我深深被打動了。
「真讓人心醉,不是嗎?」我們回到地面的時候,我對安妮說:「你的兒子簡直不可思議,這麼有天分、富有想像力,又心靈手巧——而且還有這樣的睫毛。如果我是十四歲,我絕對會無可救藥地愛上他,而且終生不渝。」
「如果我及早把他送去學雙簧管或者中文,真不知道他會變成什麼樣。」安妮說。
「有沒有人送過這麼浪漫的禮物給妳?」
「沒有,」安妮說,「我丈夫沒送過,我也從來沒送過他。我們都是無情趣的現實主義者,我們幾十年前就取消送禮物這種事了,各人要什麼就自己去買。」
「而這個小笨蛋娜妮都沒發覺他的心意,」我說,「她就只會坐在她的大象叢林宮殿裡打手機。真是不懂風情!」
從樹屋裡,傳來響亮的放屁聲,和嘰嘰喳喳的多聲部笑聲。
「而且一點都不浪漫。」我說,「她這可不是遺傳自我的。」
安妮的手機響起了「不可能任務」的鈴聲。她的一個准媽媽在超市收銀台羊水破了。
在安妮趕去處理那個孕婦,而孩子們奔向大蛋糕和波列酒的時候,我們大人們就開始工作了。羅尼爾和他的胖同事里夏爾德開始整修一樓的洗手間。大便顔色的馬桶已經被移到前面的花園裡。咪咪和我忙著把娜妮的房間刷成粉紅色,而苔露蒂在整棟房子裡進行著奇特的儀式,她四處撒著鹽,把薔薇石英放在房間角落裡,神祕兮兮地邊走邊揮舞著手臂。
門鈴響起的時候,我猜是E-bay上名叫德可信的買家,他驕傲地給一個帶木架子的黑色皮椅出了二千五百歐元。據說這把椅子是一個叫查爾斯˙伊姆斯的設計師設計的,他付這麼多錢也值得,至少羅尼爾和咪咪是這麼說的,他們自己也試著競拍了,不過這是他們在德可信已經得標後,才告訴我的。
「你們瘋了嗎?」我叫了起來,「我本來很樂意把這個醜東西送給你們的!」
但是這個咪咪和羅尼爾可不願意聽。
「妳需要這筆錢的。」咪咪說。
在門口站著的是安東,帶著艾梅麗。
「您就是德可信?」我有點驚慌地問道。
「不是,」安東說,「我是安東˙阿爾斯列本,您的律師,您不記得了?」
在我身後,咪咪從樓梯上下來了。「啊,是安東,太好了!」她說。接著她對我說:「是我邀請安東和艾梅麗來看看小貓咪的。我很希望艾梅麗能說服安東養一隻。安東本來不知道他能不能過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過來,所以我就在門上貼了字條,告訴他我們在哪兒。」
「原來如此。」我邊說,邊試著隨意撥一下我臉上的頭髮,但是卻在臉上畫出一條紅色印子。
咪咪下意識地搖了搖頭,我不明白她又哪裡不滿意了,上一次我把安東送出門的時候,我還被身後維爾瑪斯奶奶的黃銅傘架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呢。但是我根本沒跟咪咪提過這件事。
「想知道我們要幹嘛嗎,艾梅麗?我們現在就到那邊去看看小貓咪。」她開心地說,「就讓妳爸爸和康絲妲澤喝杯咖啡。他會在這段時間裡面帶微笑,講講笑話,證明他確實像我常說的那樣,是個有魅力的男人。」
安東有點臉紅了,只有一點,但是我馬上滿懷感激地捕捉到了這一點。這說明他至少也會感到難為情。
當艾梅麗和咪咪走了之後,我有點尷尬地朝他微笑一下,「她總是想撮合我們兩個。我真希望她能表達得含蓄點,那樣我們就不至於這麼難堪了。」
「啊,我已經習慣了,」安東說,「我的那些朋友和我母親一直在試著替我作媒。」
我的心頭立刻湧起一點妒意。我母親從來沒有想過替我作媒。在我還沒有和羅倫茨在一起的時候,她總是說:「要是有哪個男人跟妳在一起,那他真是夠可憐的。」等到我和羅倫茨分手以後,她就反覆說,她無法想像像我這樣的年齡和這樣的狀態,還能找到哪個傻瓜蛋要我。
「喝咖啡嗎?」我邊問,邊看了一眼牆上的鐘。「現在已經過了五點,我們可以倒杯白蘭地,說不定等咪咪回來的時候,我們都在廚房地板上瘋狂抱在一起跳華爾茲了。」
「哦,那可能一杯白蘭地不夠。」安東說著,笑了起來。
「還需要什麼,比如說?」我刮著我臉上的粉紅色印子說。
安東沒有接話。可能他腦中的回答太輕浮了:兩瓶威士忌,催眠術,再在頭上扣個鍋當頭盔——這樣我才能試著碰碰妳。
「您丈夫的律師希望我們能坐下來商量和解。」他嘴裡說出的卻是這個。
「這樣做明智嗎?」我問。
「我們可以聽聽他們有什麼好說的。」安東說,「顯然您先生準備每月付更高的贍養費,用來作為交換,要您放棄一部分本該付給您的資產;這一部分資產暫時還處於不可動用的狀態。」
「啊,他要樂意,可以保留他那些醜陋的沙發椅和畫作。」我說。
突然,安東走到我面前,離我非常近;他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擦著我的臉頰。
我吃驚地喘著氣。
「這裡還有些顔料。」他邊說,邊盯著我的眼睛看。
一聲響亮的「媽咪——母雞跑掉了」,隨後緊接著的「喔喔喔」聲,剛好阻止了我腿發軟。
我以慢動作順著櫃子滑下去。「我就來!」我叫道,臉也紅了,因為我真的都快感覺到高潮了。摸臉頰的做愛——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事。
通過暖房敞開的門,可以聽到孩子們和苔露蒂的大笑聲,還有亨姆佩爾夫人「太無恥了」的尖叫聲。
「這裡不可以養母雞,更不能養公雞!」亨姆佩爾先生叫道,「我們是有法律保障的,我們有權利早上好好睡覺。這裡是純粹的住宅區,不是農業用地。」
娜妮的手機又在啼叫了,孩子們簡直笑得快要岔氣。
「請您跟我來,我來介紹一下我的鄰居。」我對安東說。
儘管安東只是把我臉上的顔料刮去了一點點,但是我一下就意識到,我已經愛上他了,絕對地、匪夷所思地愛上他了。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年輕,如此充滿活力,在我這一生中,從來還沒有這麼精神振奮過。
在我心底有個聲音對我說:儘管看起來是一連串讓人難堪的事,將我們連在一起,但是安東的感覺跟我是類似的。或許我們還沒有走到共同面對這份感覺的地步,但沒有關係,我能時不時見到安東,和他談論我離婚的事,盯著他的眼睛看,精神振奮充滿活力地絆倒在傘架上,這樣的開始就已經足夠了。進一步的事,就順其自然了。
兩個小時後,當安東和艾梅麗準備道別的時候,咪咪看起來很惱火。「你們可以留下來吃晚飯啊,康絲妲澤的廚藝可是一流!不,不要給任何藉口!你什麼時候不能去狄斯奈樂園啊!」
但是我最後還是愉快地向兩人揮手道別了。
欲速則不達。
我上一次戀愛的時候,就可悲地在速度上創了紀錄:相識、上床、懷孕——一切都在一週之內完成。這樣的速度導致了什麼結果,我現在也看到了。不,這一次我要讓心頭的小鹿盡可能地多跳一段時間。
等安妮接生完後回來,安東已經開車走了。這個女人在兩個半小時之內就完成了任務。我第一次生孩子的時候,也以為會這麼快,結果娜妮足足花了二十五個小時才出生。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
安妮還非要去長跑不可,好在度假的時候能穿上我的黑色泳衣。於是我們就拜託馬克斯和娜妮,在我們離開的時候,照顧尤利亞斯和雅斯帕。
「還有,拜託,讓那隻公雞離開房子吧。」我說,因為亨姆佩爾夫婦還一直罵罵咧咧地蹲在窺望的窗口邊,而且始終不明白這方圓百里內根本沒有什麼公雞,只是一支該死的手機在作怪。
我們像平常一樣繞著小區跑,因為苔露蒂是第一次參與,所以我們跑得比平常慢。確切地說,我們慢得連一個一百歲的老太婆拄著拐杖都能輕輕鬆鬆地追上我們的速度。
「就這個比做愛還好?」苔露蒂隨口就問道。
「誰這麼說的?」咪咪問。
「嗯,是我覺得這比做愛都好。」安妮說。
我什麼都沒說。我想起了安東。
「嘿,我得跟你們說件事。」咪咪說。
「我也有事要說。」安妮說,「前面跑來了薩賓娜˙西根壞蛋-蘇澤爾毛和福勞克,媽媽社的頭號傻瓜!加快速度。不能讓她們以為這裡是一群戴心臟節律器的老人俱樂部,我們可是祕密成立的媽媽黑手黨領隊,要讓人聞風喪膽!」
福勞克和薩賓娜看到我們之後,同樣加快了腳步。當我們面對面停下的時候,就好像電影「賓漢」中的狂熱賽馬鏡頭一樣。我們就差打響鼻、嘶叫、搖搖鬃毛了。
薩賓娜照例給了咪咪一個飛吻。「見到妳真好,寶貝。福勞克,這是我跟妳提到過的老同學咪咪。妳知道的,就是想生孩子但是一直無法懷孕的那個。」
「很榮幸見到妳。」福勞克說,笑容燦爛。
「福勞克有三個孩子,現在馬上要生第四個了。」薩賓娜說,「她就是無法脫離替孩子更換尿布的生活!」
「這本來是個祕密。」福勞克說,更加心花怒放了。
「也許福勞克可以出些好點子給妳,」薩賓娜說,「要說有誰知道如何懷孕的話,那就一定是她了。」
「哎,就是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多點葉酸,再加上幾小時的兩人時光——其他的都沒必要。」福勞克謙虛地說,「不過我從半年前開始,就按照專業的食譜吃東西,這會影響子宮裡的酸性成分,從而決定孩子的性別。因為我非得再生個男孩不可。女孩子真是麻煩!」
「我想,對咪咪來說,性別完全無所謂,」薩賓娜說,「最主要的是要生一個,對不對?我個人更喜歡女孩子。順便說一句,卡斯塔馬上會成為兒童模特兒了。」
「什麼?就那個小卡斯塔?」我大惑不解地重複一次。那個醜得不堪入目的小孩子,可以替什麼樣的產品拍廣告呢?難道是特大號的奶嘴?
「您的孩子也這麼帶不出門嗎?您和孩子上街會覺得羞恥嗎?那您可以買個漂漂奶嘴,這樣就沒人會發現孩子的真面目了。漂漂奶嘴——不會再有人在您寶寶面前扭頭躲開了。」
或者給卡斯塔一個特寫,救生艇似的大嘴一張,雙下巴往胸前一壓,還一手擦著馬鈴薯鼻子裡流出的鼻涕。配上一個口白:小卡斯塔不是無可救藥的。德國美容手術協會。
當我們回到家的時候,我還是大惑不解。
苔露蒂一下子倒在草地上,喘著氣說:「妳們往回跑的時候,怎麼那麼急沖沖的?」
「哎,我們可不想在那兩個女人面前露怯。」咪咪說。
「但是我們已經露了!下一次我們絕對不會只張大嘴聽她們說話,我肯定。」安妮氣沖沖地說,「到時候我們也會給她們點顔色瞧瞧。說到底,我們可是讓人膽戰心驚的媽媽黑手黨。」
「我們要進行角色扮演訓練。」苔露蒂說。
「咪咪,」娜妮從樹屋往下喊,「過來一下,發生了一件糟糕的事。」
「小傢伙們在哪裡?」
「在羅尼爾那裡,他們沒事,」娜妮說,「我們在這上面測試望遠鏡,用這個可以看到老遠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別人家裡。然後尤利亞斯看到那個胖女孩,蘿菈-克里斯蒂,她在小公園後面的小木屋裡,正要把自己的脈管割開。」
「噢,我的上帝!」安妮說。
咪咪用手按著心臟,苔露蒂有幾秒都忘了喘氣。
「別擔心,她沒做對,」娜妮說,「她不知道割脈要豎著割,她只是橫著割傷了自己。而且在她用力切下去之前,我們已經趕到她那裡了。」娜妮呼了口氣,「真不專業。」
「那她現在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樹屋裡。」娜妮說,「她怎麼都不願意回家,就只是哭個不停,還說下一次她要上吊。妳現在來把她接下去,好嗎?」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媽咪黑手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38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媽咪黑手黨
德國百萬暢銷作家克斯汀.吉兒
繼13封自殺告別信後,又一搞笑鉅作
比義大利黑手黨更殺的祕密組織
─媽咪黑手黨─誠摯邀請妳一起加入
----------------------------------------------------------------------------
她原本擁有一個人人欽羨的幸福家庭,
卻晴天霹靂地被丈夫炒了魷魚,
瞬間,她從天堂掉入十八層地獄,
甚至變成孩子眼中的黑心媽媽。
為了脫胎換骨躋身好媽媽行列,
她立志加入社區裡的模範媽咪社,
但是當她參加下午茶面試會時,
卻發現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真相!
這群外表看似完美的超級模範媽咪,
骨子裡是一群彼此揭短,互掐脖子的偽善者。
她甚至懷疑,她們可能患有嚴重的經前綜合症。
為了守護孩子、對付這群假面媽咪,
一個自立自強的對抗組織誕生了:「媽咪黑手黨」!
她們不動刀不動槍,卻用最犀利的方法,
懲戒那些自認為高人一等的媽咪們。
現在,那些愛慕虛榮的媽咪們,可要小心了……
作者簡介:
克斯汀.吉兒(Kerstin Gier)
出生於1966年,曾學習過德語文學、英語文學、音樂和教育學,1995年開始寫作,2005年獲得德國愛情小說作家聯盟的德國最佳愛情小說獎。
譯者簡介:
李雙志
1982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至2007年在北京大學德語系就讀,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07年夏天起任教於南京大學德語系,2009年4月起在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德語文學博士學位。曾在北京歌德學院兼職,為中德文化網擔任翻譯和撰稿人,譯有:(顧彬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古典散文、筆記、書信》,(雅諾什著)漫畫書《卡斯帕》系列等。
TOP
章節試閱
在接下來的星期五,我們正式替樹屋揭幕。安東向我保證,像這種這麼小、又足以做為楷模的兒童建築創作,決不需要相關部門批准。他已經寫信向建築管理局說明一切,他還和青少年管理局以及警察局取得了聯繫,寄了封友好的信給貝克先生。在信中,他警告貝克先生的客戶,即亨姆佩爾夫婦,不得再發出損害名譽的報告和申訴,否則他的客戶,就是我,會對亨姆佩爾夫婦提出控訴,而根據法律條款,我無疑會控訴成功。從那以後,貝克先生就再也沒來信煩過我了。
綠化管理局則好好地研究了安東的信。有一天,一個姓朗浩司的先生就上門了,想對我家地產...
綠化管理局則好好地研究了安東的信。有一天,一個姓朗浩司的先生就上門了,想對我家地產...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克斯汀.吉兒 譯者: 李雙志
- 出版社: 核心 出版日期:2010-06-30 ISBN/ISSN:986650333X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