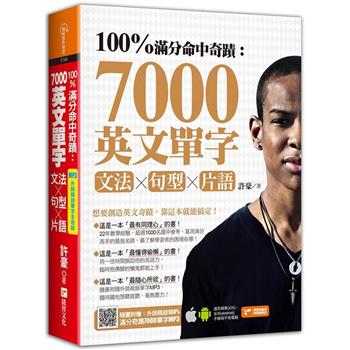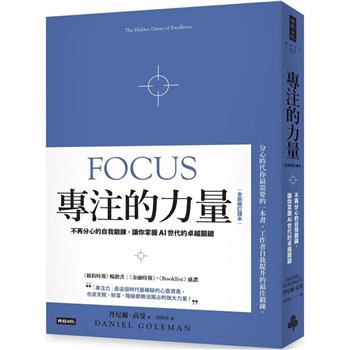若沒有美洲這片新市場,五百年來的歐洲,以及今天的歐洲,會是一個非常不同且比實際上貧瘠甚多的地區。 ──克羅斯比
克羅斯比在人類史中加入了生態學,解釋了許多長久以來讓人困惑的歷史事件。
──內華達拉斯維加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羅斯曼
每當我們談起世界史,主角總是圍繞在歐洲;一旦談起我們這本書所研究的美洲,卻也往往把它依附在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登陸巴哈馬後歐洲軍事、政治、財富等歷史事件之下。直到本書作者克羅斯比在一九七二年揭開深深影響歐美以及現代世界的關鍵力量後,這段消失五百年的歷史才又重回人類史冊,人類也才意識到,植物、牲畜乃至細菌,才是新舊二個世界交戰的真正火力,而且它們的後果絕不只是一些美洲國家的誕生,更是全球生活文化、飲食風俗的大轉變。
歐洲人用槍砲征服了新世界,美洲則用植物改變了我們餐桌上的風景乃至日常生活的文化。幾個影響重大的例證包括:
.玉米:原生於美洲的營養穀物,目前已成全世界人類與牲口最重要的糧食之一,也是全球最夯的生質能源的原料。
.馬鈴薯:這種原產美洲的高澱粉植物,現在變成全世界速食店的必備主食。
.辣椒:十七世紀還沒沒無聞的美洲辣椒,今日已成麻辣鍋與印度咖哩飯裡不可或缺的成分。
.菸草:原作為殺蟲劑與藥品使用的菸草,自美洲傳出後卻演變成了嗜煙癮君子的最佳良伴,迄今已荼毒了為數不少人的肺臟和口袋裡的金錢。
.可可(巧克力):美洲人拿來做藥的苦味種子,如今成為甜蜜、浪漫,每年情人節必定熱賣的愛情象徵。此外巧克力內含的高抗氧化成分,更讓重視健康、養生的人士趨之若鶩。
就連一向被視為台灣「國食」與認同符號的「地瓜」,也是美洲原產,爾後在「大交換」下來到台灣。又稱甘薯或番薯的地瓜,被哥倫布當成海外奇物帶回西班牙獻給女王,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已遍植地瓜,然後西班牙水手又把它帶到菲律賓。再於明朝傳入福建,十七世紀透過荷蘭人進入台灣,從此與台灣的生命與文化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
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美洲的世界,我們的餐盤還剩下什麼呢?
然而在這個歐洲獲利的歷史過程中,歐洲人所帶過去的細菌,卻殺害了無數的美洲印地安人,成功解釋了為何一小隊西班牙士兵即能攻下當時位於墨西哥已高度組織化和軍事化的社會。當時甚至有人描述:「一群印地安人只要嗅到一個西班牙人的味道,他們就會立即死去。」此外,歐洲人有意無意帶過去的生物,也掠奪了美洲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自哥倫布登陸美洲大陸這五百年來所消滅的物種,可能比一百萬年演化而滅絕的物種都還要多。
對於這段可說是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全球化」歷史事件,本書作者克羅斯比切入的角度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同,也開啟了史學、人類學和生態史的新領域,將過去人類所忽視的史實重新拉回歷史。因此本書一九七二年一出版(中譯版譯自二○○三年慶祝三十週年紀念新版),書名「哥倫布大交換」即成為經典術語,更刺激了許多以生態解釋歷史的著作誕生,例如《槍砲、病菌與鋼鐵》。
在今日糧食短缺、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的困境,本書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反省。
這個奇異的大交換,主導著我們如今所生存的世界,影響既長遠且全面,可是我們極少認識,也沒有完整研究。這是在本書原版出版三十年後,我們終於能推出中文版,最覺得慚愧但仍然感到欣慰的地方。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慧宏 專文推薦
◎ 各界學者、專家一致好評推薦
生態學科
王琄嬋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邵廣昭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侯平君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宣大衛 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主任
彭鏡逸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主任
程建中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副教授
程樹德 哈佛醫學院博士 現任教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系
公共衛生學科
楊倍昌 成功大學醫學院微免所教授兼所長
孫建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歷史學科
王文霞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周雪舫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周惠民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美香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秦曼儀 台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楊肅獻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人類學科
翁玲玲 佛光大學人類學暨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系主任
莊英章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文化人
楊 照 「新新聞」副社長
◎ Amazon讀者★★★★★深刻推薦
目次
推薦序 從環境史重新解讀全球化 陳慧宏
三十周年新版前言 以生態觀點重新解讀歷史 麥克尼爾
三十周年新版作者序 自大陸冰河融化以來人類的全本演義
初版前言 人類和其環境長遠互動的史實 梅令
初版作者序 把人當做一個生物性實體的歷史考察
第一章 新舊大陸,對比分明
第二章 大征服者與奪命疫疾
第三章 舊世界植物、動物移居新世界
第四章 梅毒現身:一頁病史
第五章 食物與人口
第六章 至今未停止的大交換後效
注釋
參考書目
三十周年新版參考書目
中英名詞索引
一段人類忽視了五百年的歷史,一則遲了三十六年才傳到台灣的史實,將深刻改變我們的全球史觀。
作者簡介:
克羅斯比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地理、歷史和美洲研究的榮譽教授,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和華盛頓州立大學。他花了大半生的時間在研究,為何歐洲會在歷史上崛起?和許多歷史學家探索的路徑不同,作者深入人類生存的生態面向,揭露了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人類史。其重要著作有《生態帝國主義》、《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等,其著作也曾榮獲愛默生獎、醫學作家協會獎、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選書。
章節試閱
三十周年新版前言
以生態觀點重新解讀歷史
美國名史學家 麥克尼爾
美洲博物學家、評論家,以及現代環境主義之父李奧波德,在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沙郡年記》中呼籲,應該以生態觀點重新寫作歷史。一整代史家都未理會他的呼聲。然後在一九六○年代的社會騷動與混亂之中,本書作者克羅斯比來了,通過他自己另一條路,也抵達了與李奧波德相同的結論。可是接下來他更進一步,真的動筆寫了這樣一本著作,嚴肅看待生態在人類事物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你現在手上拿的這本書。
李奧波德一定會很感欣慰;克羅斯比那些專業同行則不見得。《哥倫布大交換》一書,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出版,直到一九七二年才終有綠林出版社接手。學術刊物上的書評反應,從嚴厲苛評到客氣禮貌均有,許多甚至不屑一顧懶得評論。克羅斯比任教大學的同事則抱持懷疑態度,不能確定這種寫法真能算是歷史。這本書卻不肯就此消失。它的文字清晰簡潔,它的主題似乎越來越形重要,因此它不斷在全美許多大學書單上出現。而且還譯成西班牙文與義大利文。
我自己與這本書初相逢,是一九八二年一個雨天。在我暫用的某間研究室裡,隨手從齊肩高的架上取下它來。然後一口氣就讀完,連晚餐也全忘了。任何許久之前所讀的書,我都很少能精確憶起當時的情境因由,只有《哥倫布大交換》是例外,連那時心中激起的興奮刺激,都一起深深刻蝕在腦海裡。從那一刻開始,歷史對我而言,就再也不大一樣了。或許,當時的我特別容易接納此書,因為已在大英國協的憲法史堆內,埋頭苦幹了好多好多個月了。
許多人都在克羅斯比這本書中發現了新視野,用以觀看美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以及整個世界歷史。它也成為建立環境史領域根基的文本之一,這項新學門於一九七○年代在美國開始興起。主流史家也漸漸注意此書,及至一九九○年代,「哥倫布大交換」的觀念,已開始進入好幾本美洲與世界史教科書內。
「哥倫布大交換」一詞本身,也如同它的同名書表現極佳。歷史家並不是常常能有這種機會,可以新鑄出一個簡單新詞,成為涵蓋某些複雜現象的標準用語。可是今日美國幾乎所有專業史家,以及海內外許多學者,都聽過「哥倫布大交換」一詞。許多甚至能做出相當正確的概述,解釋克羅斯比此詞用意──即使未曾讀過此書。克羅斯比提出的這些概念,三十年前飽受史學界漠視、出版界忽略、甚至某些評論界敵意對待,如今卻成為近代史標準論述的重要一環。
克羅斯比的理論,當然也是建立在前輩學人的研究成果之上。他並未親入檔案庫藏搜索,未在故紙堆中挖出有關麻疹、綿羊、牧草的文獻。地理學家對農作的傳播分布有興趣。人類學者及少數歷史學者,則想弄清楚一四九二年後發生在美洲的多起疫疾與人口大災難的現象。讀者可以在克羅斯比書中註腳尋見這類著作。可是在克羅斯比之前,卻沒有任何人把這些不同面向結合起來,也沒有任何人把這些主題寫得如此風趣生動。1
因此對史學界來說,克羅斯比構架出了一個新的主題。他在一九八六年的著作《生態帝國主義》中繼續追探生態因素議題,焦點轉向世界其餘地區,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兩地;並主張過去幾世紀來,歐洲人之所以能夠獨霸世上大部區域,就是因為背後有這種有系統而不對稱的生物交換衝擊相助。其他學者也進一步豐富他的理論,指出哥倫布大交換中的某些西非元素,比方一六九○年後鞏固了卡羅萊納低地大栽植場型經濟的稻米,即可能來自非洲。
2
克羅斯比在本書中對非洲著墨不多,並非沒有理由。回到一九六○年代,有關非洲的史觀史論方才正在成形,因此他需要的那類資訊,當時並不似後來那麼容易取得。他雖然探討了美洲作物對現代非洲的重要性;可是在舊世界對美洲提供的生命貢獻上,非洲的作物、疾病、人民,其實也同樣舉足輕重──在某些地區甚至占有支配地位。別忘了,一八八○年之前跨越大西洋來到美洲的人,絕大多數是非洲人。一八二○年之前每五名橫渡大西洋的移居者,就有四名來自非洲。雖然他們是繫著鎖鍊而來,他們的某些動植物也跟著他們來了:包括非洲的稻米、秋葵、山藥、黑眼豇豆、小米、高梁、芝麻,以及那些引發黃熱病與瘧疾的病原。咖啡也來自非洲,雖然不是搭奴隸船而來。此外,非洲人也帶著他們極有效的稻作技術,以及他們不怎麼有效的黃熱與瘧疾療法來到美洲。
克羅斯比提出的哥倫布大交換概念,價值不在其完整全面,卻在他建立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態與社會事件。的確,只要稍用一點想像力,就可以發現克羅斯比揭櫫的那類交換幾乎無處不在,卻遮蔽在時間迷霧之中,永遠無法像克羅斯比為哥倫布大交換提供的細節那般,詳細為人了解。早在哥倫布之前,印度洋上的水手就知道順著季風航行,在東非與印度之間往來。他們載著作物、蟲害、雜草,疾病,來回返復兩地,也帶著高梁、珍珠粟、龍爪稷來到印度。順著季節風而去的其他類似交換,也在東南亞群島與中國之間發生。某種早熟型的稻品種:占城稻(#占城即今日越南%),令中國糧產自十三世紀起變得豐足甚多,也為宋明兩朝的國力與繁榮作了保證。亦如克羅斯比在《生態帝國主義》書中指出,另一場時間上離現在較近,但是規模同樣浩大,卻相當單方面的生物交換,也在另一處新舊世界之間發生:一邊是太平洋上諸島與澳大利亞,另一邊是歐亞大陸。也就是十八世紀後期,隨著英國庫克船長在太平洋上的多次航行之後,前此各自存在的生態系統從此結合,後果之戲劇驚人,直可與哥倫布大交換齊驅。雖然這些兩極相逢事例,並沒有馬鈴薯或玉米等級的禮物送給世界(它們最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數桉樹屬植物),可是對澳大利亞、紐西蘭、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與生態系統來說,這個或可稱之為「庫克大交換」的事件,絕對震撼衝擊到了極點。
與哥倫布大交換平行發生的事例,也在陸上出現。西元前一百年,商旅車隊首度確立中國與地中海世界之間的商業交換。種籽、胚芽,搭著顛簸之旅而去。櫻桃,或許連同天花、麻疹,來到了羅馬世界;中國則換得了葡萄、苜蓿、驢子、駱駝,或許其中也包括了天花、麻疹。
當駱鈴叮噹,商隊穿越撒哈拉沙漠來往於馬格里伯(#摩洛哥、阿爾及尼亞、突尼西亞%)與西非之間,類似的事情也必然同樣發生。西元五百年之前,也有過一位非洲的哥倫布,他的名字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為定期的交通來往正式揭幕。於是馬兒來到西非,造成的革命性政治後效,與馬兒在北美印地安大平原上帶來的衝擊效應若合符節,雖然在西非養馬的難度令情況稍有不同。儘管如此,馬的軍事用途,尤其是用來對付那些無馬之族,也幫忙重組了西非的政治版圖,遂有迦納、馬利、桑海等大帝國於焉興起。
跨沙哈拉沙漠行走的商隊,也在西非與地中海世界之間交換病原。一四九○年代梅毒爆發,或許係自美洲輸入,但也代表西非雅司病某種突變。反向而去,歐亞大陸某些人類群體型與動物群體型疾病,或也藏在駱駝客身體組織內進入西非。老鼠、跳蚤,可能也是以這種方式穿越了沙哈拉,於十四世紀疫疾大流行時期,將淋巴腺腫鼠疫帶到了沙漠南方半乾旱區域薩赫耳。
種種生物大交換事件,如果確如上述所形容般曾經發生,它們對歐亞大陸與非洲歷史的塑造影響,必如哥倫布大交換一般確定。雖然衝擊規模或許較小,而且,至少在目前如此,記錄的資料文獻也不及克羅斯比聚光突顯的完備。但是或許,有一天,它們也終將找到它們的克羅斯比,為它們寫下專書,不但令李奧波德在天之靈欣慰,也會在一個潮濕午後,改變某個人的歷史視界。
梅毒現身:一頁病史
舊世界投之以桃,新世界不遑多讓也回報以極多的李。但凡發生於一五○○年前後數十年間的每一樁重大事件、人物、流行、愚事、聖戰、不幸,大文藝復興大哲伊拉斯謨斯筆下幾乎都曾提及。而當他在世之日,臨到歐洲頭上的所有不幸事件之中,伊拉斯謨斯認為,最恐怖者莫過於那個法國佬病,或稱梅毒。他覺得沒有比這個病更會傳染、更折磨受害者、更難治癒……或者說,更時髦的了!「簡直是一種最不像話的疹子!」他的《對話錄》中一個角色嘆道:「真要攤牌比一比,決不會輸給痲瘋、象皮病、金錢癬、痛風、或鬚瘡。」
伊拉斯謨斯那一代的男女,是第一批見識到梅毒的歐洲人;至少,他們是如此表示。英格蘭人稱之為「疹子」的這個惡疾,於十五世紀最後幾年間如雷電倏然擊來。可是它卻不似其他也是如此突兀而至的疾病,後者往往迅速填滿墓園,然後便隨之遠颺,另俟他日再行歸來出擊,或永遠不再露面。反之,梅毒從此駐足,再也不走,成為人世永遠的共同存在。
歷史學者對梅毒有一股特別的著迷,因為在肆虐人類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它最獨具「歷史性」。多數疾病之始,早在人類最早記憶之前。只有梅毒,擁有一個所謂的歷史起始時刻。自十五世紀最後十年以來,不乏有人堅稱:自己幾乎可以確切指出梅毒現身於世界舞台的那個時間點,甚至知道來源地點所在。「就在主後一四九三年間或左右之際,」伊拉斯謨斯通信對象之一的當代人文主義者胡滕寫道:「這個最汙穢、最悲慘的惡疾,開始在眾人中散播了。」另一位同時代人西班牙醫生伊茲拉也表同意,認為一四九三年是梅毒元年,並表示「此病原生之地,來自那座現稱艾斯班紐拉的島嶼。」哥倫布把它帶了回來,連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事物的樣本。
從十六世紀第三個十年之際起,有關梅毒源始的諸家理論之中,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這個「哥倫布帶回說」,可是再流行也免不了駁斥意見。事實上梅毒源始一事,無疑是所有醫藥史學中爭議最大的一環。單單是蒐編出一張完整的相關書單,就要耗上好幾個月的工夫。
直到最近數十年間之前,關於梅毒出身之謎,一般只有兩種普遍為人接受的看法:一是哥倫布帶回說,一是完全與之相反的對立理論,認為早在一四九三年前梅毒即已存在於舊世界。如今又出現單源論說,挑戰胡滕、伊茲拉及其他哥倫布帶回派等人士的看法,主張這個梅毒性病只是一種併發症狀,屬於一個具有多面向、遍佈全世界的密螺旋體病。但是在我們檢視這項最新學說之前,不妨先來探討一下前人的舊說法:到底在一四九二年時,大西洋兩岸都已有梅毒,還是只存在於美洲大陸?
哥倫布登陸美洲之前的舊世界文獻,找不到任何對梅毒證據確鑿的描述。類似的痘疹描述固然有所發現,卻也可能是在描述痲疹、疥瘡、或其他疾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崇奉祖先,只要有機會便引經據典,卻沒有任何中國作者引述過一如古書所言梅毒云云。蓋倫、耶維森那,還有古代、中古的其他醫學作者,雖然對細菌或抗生學一無所知,卻都極富臨床經驗,描述起疾病的表象症狀,功力不下於任何現代醫生。如果某個疾病未曾在他們筆下有所描述,我們或許可以假定:不是此病當年性質有異,就是他們從未見過此病。用這個假定來搜尋像梅毒這一型疾病的記錄,尤稱允當,因為在任何不幸曝露於其魔掌之下的社會裡,它都會蔓延極廣。
舊世界的內科大夫、外科醫生,甚至包括非醫學中人,但凡於十六世紀寫過有關梅毒性病一事者,都幾無例外,指稱它是一種新惡疾。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全都錯了。從伊茲拉到中國明代傑出醫學家汪機的《石山醫案》──西班牙人、日耳曼人、義大利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眾口一聲,全都表示之前從未見過梅毒疹。若說他們在同一個題目上同時全都錯了,實在不太可能。
即使找不到任何記載,直指梅毒是舊世界居民面對的新疾,語言現象中卻有足夠證據支持這項看法。它有各式各樣的名稱,而且這些不同名目,卻幾乎都意味著它乃是外邦傳來的惡疾。這些語言事實,在在有力地證明梅毒之「新」。義大利人稱它法國佬病,結果這也成為梅毒最通行的外號;法蘭西人稱它那不勒斯症;英格蘭人則稱它是法國佬病、波爾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蘭人稱它日耳曼症;俄羅斯人稱它波蘭佬病;等等等等。中東人叫它歐洲膿包;印度人叫它法蘭克人病(指西歐)。中國人叫它廣州潰瘍,廣州是中西接觸的主要港埠。日本人叫它唐瘡,唐指中國;或者更切題些,葡萄牙佬病。早期眾人賜予梅毒的大名,洋洋灑灑,可以寫滿好幾頁紙。直到十九世紀,義大利名醫佛拉卡斯特羅於一五二○年代新鑄的那個字眼「syphilis」,才終於變成全球通用的標準定名。
三十周年新版前言以生態觀點重新解讀歷史美國名史學家 麥克尼爾 美洲博物學家、評論家,以及現代環境主義之父李奧波德,在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沙郡年記》中呼籲,應該以生態觀點重新寫作歷史。一整代史家都未理會他的呼聲。然後在一九六○年代的社會騷動與混亂之中,本書作者克羅斯比來了,通過他自己另一條路,也抵達了與李奧波德相同的結論。可是接下來他更進一步,真的動筆寫了這樣一本著作,嚴肅看待生態在人類事物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你現在手上拿的這本書。 李奧波德一定會很感欣慰;克羅斯比那些專業同行則不見得。《哥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