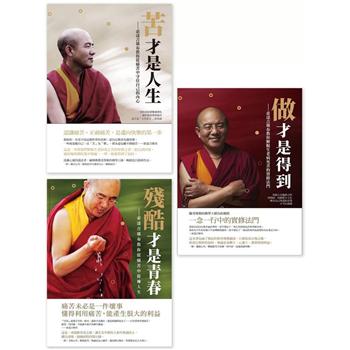顯然魔法與這對姊妹都是危險的玩意兒,
一趟旅行就連整個歐洲的和平都攪和進去了……
★《壁花姊妹祕密通信》系列作II
★號角選書指南、布告雜誌推薦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青少年書籍
親愛的讀者:
這次的蜜月旅行,即將發生許多大事。
首先,在加萊的旅店,有個神祕女士送來一件神祕小包裹,不久之後我們就在夜裡遭竊。令人想不通的是,小偷為什麼要穿一雙行動一點都不方便的土耳其便鞋?接著,當我們參觀亞眠的神殿時,竟然碰到討厭的史傳戈先生!他看起來又在荼毒哪個可憐的年輕人,而且一點都不像是對歷史文物有研究的人!
等我們好不容易抵達巴黎,不幸與意外更是接二連三來訪,甚至還發生了命案!古怪不止於此:一些古老皇室文物不翼而飛;有人擅闖教堂遺跡並留下奇怪的魔法痕跡……而這一切怪事跟我們的蜜月旅行路線,還有文物學家爸爸 / 亞瑟舅舅建議我們參觀的古蹟路線,竟然不謀而合!因此我們的蜜月旅行搖身一變,成了緝凶查案千里追!
顯然魔法是一項危險的玩意兒,連整個歐洲的和平都攪和進去了……但願我們能早日結束這趟旅行!
愛你們的
瑟西和凱特
瑟西莉亞和凱特這對親愛的表姊妹同時有了美滿的姻緣,更攜手一同踏上蜜月旅行!不料旅途多災多難,她們碰上小偷、搶匪,還有討人厭的史傳戈先生!但她們更沒料到,這一切竟然只是一樁大陰謀的開端,而她們的聰慧、正義與勇氣,正將她們捲入危機的漩渦中……
一瓶所剩無幾的香油是啟動古老魔法儀式的關鍵,而有人正想再度奪取歐洲的和平……可想而知,這趟蜜月旅行一定同頭到尾都不平靜!凱特跟瑟西,還有她們親愛的新婚夫婿,能夠追查到足夠的線索,及時阻止陰謀嗎?
兩位作家好友玩起角色扮演遊戲,各自化身成瑟西和凱特,細數身邊趣事、窘事和大事,還不忘把小說中常見的老梗拿來毒舌嘲諷一番!透過作者洋溢全書的幽默感,女孩們敏銳的觀察力與機智的表現都令人樂趣無窮!
本書特色
《壁花姊妹祕密通信》好評連連,欲罷不能;系列作《壁花姊妹交換日記》不僅維持一貫的毒舌詼諧風格,事件格局也擴大到半個歐洲,並且綜攬歷史與文化面,陰謀也更趨複雜,令人讀來一邊提心弔膽一邊卻十分上癮!
作者簡介
派翠西亞.蕾德 Patricia C. Wrede
美國奇幻小說家,擅長幽默風格與非傳統奇幻冒險。著有「魔法森林四部曲」等暢銷小說。在本書中扮演瑟西莉雅。
卡洛琳.史帝夫莫 Caroline Stevermer
美國奇幻小說家,以歷史奇幻小說著稱。在本書中扮演凱特。
兩人是好友,目前均居住在明尼亞波里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