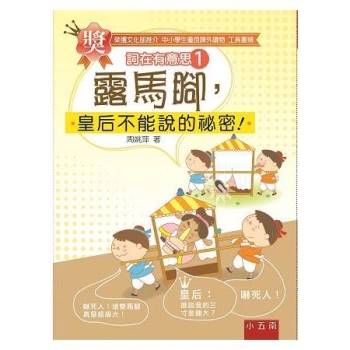凱琳.瑪菲正在麥迪遜飯店外面等著我。凱琳和我正好相反,我長得高高瘦瘦,她則短小精幹;我有著一頭黑髮和一對黑眼眸,她則擁有秀蘭.鄧波兒的金色捲髮和湛藍的雙眼;我的輪廓全都細瘦得有稜有角,還有個鷹勾鼻加尖下巴,她則渾圓玲瓏,還有個在啦啦隊長臉上可看到的可愛鼻子。
這是個有點風的沁涼天氣,宛如一般的三月天。她穿著一件長外套,搭在長褲套裝上面。瑪菲從未穿過洋裝,我一直懷疑她應該有一雙結實、有形的小腿,就像體操選手一樣。她的體能很發達,這一點從她辦公室裡那兩座合氣道比賽的獎盃即可證明。她的頭髮齊肩,在春風裡狂野地飛拂著。她沒有戴耳環,也只略施脂粉,讓人很難分辨出她到底是否化了妝。與其說她是位強韌的刑案探員,不如說她看起來更像是個討喜的阿姨或是親切的媽媽。
「德列斯登,你沒有別件大衣可穿了嗎?」當我走到可以打招呼的距離時,她問道。有好幾輛警車違規停放在大樓前。她瞥了我的眼睛約半秒鐘,接著迅速移開;為此我得好好表揚她,因為她已經比絕大多數人撐得更久了。除非你的目光停留好幾秒,否則並不會有什麼危險。對此我已經習以為常,任何人只要一知道我是巫師,就會特別小心不要正視我的臉。
我低頭看著這件有著厚重的垂帷和防水襯裡,袖子和手臂等長的黑色帆布防塵大衣。「這件大衣有什麼問題嗎?」
「那基本上是『龍虎盟』的戲服。」(譯注:約翰.韋恩一九六六年的影片,用來諷刺德列斯登的過時、與流行脫節。)
「所以?」
她嗤笑著。一個小個子女人竟然發出此等不雅聲音。她後腳跟一轉,走向飯店的正門。
我趕上去,稍微走到她前面。
她加快腳步,我也加快。我們比賽看誰先走到正門,兩人愈走愈快,穿過昨晚的雨所留下的水坑。
我的腿比較長,所以先到了。我為她開門,表現紳士風範請她進門;這是我們的老遊戲了。或許我的價值觀有些過時,但我是個守舊派,認為男性不該只是把女性當成比較矮小、瘦弱、有胸部的男人而已。倘若各位認定我這樣想是不安好心也無妨。我樂於將女人當成淑女、幫她們開門、一起吃飯時由我付帳、送花……諸如此類。
此舉卻把瑪菲氣瘋了,她得在芝加哥與那些最粗野的男人們爭鬥、耍心機,才能走到今天這個位置。當我站在那裡開門時,她瞪視著我,但眼神裡有種安心、放鬆的感覺。她在我們的這個儀式裡得到一種奇異的撫慰,每次當她發現到這點時,就更覺得氣惱。
然而,七樓上面到底有多糟呢?
我們搭著電梯,突然一陣靜默。我們彼此都相當熟悉對方,所以這樣的靜默並不是很自在。我很瞭解瑪菲,能用直覺抓住她的情緒和思考模式--只要我跟某個人相處一段時間,都能建立起這種直覺。這是天賦呢?還是超自然能力?不知道。
直覺告訴我瑪菲很緊張,跟鋼琴的弦一樣地緊繃。雖然她沒有表現在臉上,但是從她肩膀和脖子的姿態,以及背部僵硬的樣子就可以感受到。
或許是我將這股感受投射到她身上,電梯的封閉感讓我有點緊張。我舔舔嘴唇,環視電梯內部,我和瑪菲的影子落在地板上,看起來彷彿在那裡攤爬著。還有某件事困擾著我,一種讓人坐立不安的本能反應--那就是我若很緊張就會放屁。要忍住,哈利。
就在電梯慢下來時,她用力吐了口氣,在電梯門打開前再吸入一大口氣,彷彿她打算在這層樓要一直屏住氣,到重回電梯時才會再呼吸一樣。
血腥味聞起來有種黏稠的感覺,類似金屬的味道,當電梯門打開時,空氣中就瀰漫著這種氣味。我的胃翻騰了一小下,但是我硬著頭皮跟著瑪菲出了電梯、沿著走廊走下去,經過幾個穿制服的警察,他們都認識我,在我經過時揮手跟我打招呼,沒有要求檢查市政府給我的那張小巧輕薄的卡片。的確,在芝加哥市警局這樣的大城市單位裡,就算沒有一狗票的顧問(我在文件上登記的是心理諮詢,我想是這樣的),也還是有幾個非正職的條子。
瑪菲先進入房間,血腥味愈來愈濃,在第一道門後面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景象。這間套房外側的房間是以艷麗的紅色和金色為主調的起居室,看起來儼然是三○年代老電影裡的布景--奢華,卻有些虛假。椅子表面是黑色亮麗的皮革,我的腳陷進了厚厚的鐵灰色絨毛地毯裡。天鵝絨窗簾已被拉起來,雖然燈全都開了,這個地方還是有點太暗,質感和色彩都稍嫌肉慾;這並不是你會想坐著看書的那種房間。聲音從我右邊的門口傳過來。
「在這裡等一下。」瑪菲一面告訴我,一面穿過門去到走道的右邊,進入我猜想是這間套房的臥室。
我幾乎是閉著眼睛在起居室裡踱步,記下些筆記。皮沙發,兩張皮椅,亮黑色的視聽中心有音響和電視。香檳瓶放在一個盒子裡退冰,盒內滿盛著昨晚原本應該是冰塊的水,旁邊放著兩個空的玻璃杯。地上有一片玫瑰花瓣,和地毯顯得格格不入(不過說真的,在這房間裡任何東西都很突兀)。
一旁那張皮製躺椅的下方露出了一小塊緞布。我彎下腰一手拾起那塊布,小心翼翼不去碰觸其他東西。原來那是一件黑色緞質內褲,小小的三角形褲身每個頂點都有繫帶,其中一條像是被人扯斷似的與褲身分了開來。夠淫蕩。
那套音響相當先進,但不是很名貴的品牌。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枝鉛筆,用橡皮擦那端按下「播放」鈕。柔和、肉慾的音樂洋溢在房間裡,低沉的貝斯、扣人心弦的鼓聲、無語的人聲,背景則是女人的嬌喘聲。
音樂持續了幾秒鐘之後停頓了約兩秒,然後便不斷重複播放。
我做了個鬼臉。正如方才所說的,我對機器就有這種效應。這和巫師是肯定有關的,我們這行都在跟魔力打交道。愈是精巧、先進的機型,在我靠近的時候就愈有可能會出狀況。我可以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廢掉一台影印機。
「愛--情套房。」一個男人的聲音,而且故意把愛字的尾音拖得很長。
「客倌,您覺得如何?」
「嗨!卡麥克警官。」我沒轉頭便說道。卡麥克那細微、具有鼻音的聲音很特別。他是瑪菲的搭檔兼強烈的懷疑論者,堅信我不過是個神棍,不斷將市政府的民脂民膏騙走。「你打算把那件小褲褲留著帶回家,還是只是觀察一下?」我轉過身來看著他。他矮胖且微禿,有著一對明亮而充滿血絲的雙眼,還有著一個短下巴。他的夾克都皺了,領帶上有著沾了食物的痕跡,這些特徵掩蓋了他的機敏。他是個精明的條子,在追查兇手時更是完全鍥而不捨。
他走到椅子邊往下看。「不錯嘛,神探。」他說道。「不過那只是前戲罷了。你等下會看到主秀,我還幫你準備了一個水桶讓你嘔吐用。」他轉過身來用鉛筆的橡皮擦那端輕輕一觸,就把那台故障的CD唱盤給關了。
我張大眼睛看著他,讓他理解到我有多麼多麼害怕,然後走過他,進入臥室。我馬上就後悔了。我看著現場,機械性記下筆記,靜靜地把我腦袋裡想要尖叫的那個念頭給壓下去。
他們一定至少已經死亡一天了,因為屍僵狀態已經出現。他們躺在床上,她跨坐在他身上,身體向後仰,佝僂得像個舞者,她胸部的曲線勾勒出一道美麗的輪廓。他在她下方伸直身體,精瘦結實的男人,手臂向外伸出,緊抓著綢質床單,雙拳握實。假使這畫面是刊在色情雜誌上,肯定是個相當誘人的畫面。
……只不過這對愛侶左上身的軀幹是整個被炸開的。在他們的皮膚下,肋骨向外伸出,活像是一大把長短不一的小刀。由大動脈噴出的血液飛濺出他們的身外,一路噴到牆壁上的鏡子,一併噴出的還有已成黏糊狀的大塊血肉,八成原本是他們的心臟。站在兩人上方,可以看到他們屍體中的大片空洞。我記下在毫無生氣的左肺和肋骨旁已呈灰色的內膜,看起來很明顯是向外噴出,而且是被某種內在的力道扯斷的。
當然這看起來一點情色的感覺都沒有了。
床是放在房間的正中央,造成了微妙的加強效果。臥室的裝璜和起居室一樣--大片的紅色、大片的長毛絨織品,若不在燭光下,看來就稍嫌俗艷。牆壁的架子上確實有蠟燭,不過現在已燒盡而且熄滅了。
我走近床邊,繞著它走了一圈,地毯隨著我的走動而嘎吱作響。我腦中想要尖叫的念頭雖然被自我控制和嚴格的訓練壓抑住,但仍蠢蠢欲動。我想要忘掉這個念頭,真的,我很想。但要是我不趕快衝出門外,有可能就會像個小女孩一樣哭泣。
所以我趕快記下細節。這女人約二十來歲,身材姣好。至少我想她原來是,只是現在很難看出來。她的頭髮是棕色的,剪成童花頭(編注:pageboy style,長及肩,髮尾內捲的髮型)的髮式,而且感覺是染過色的。她的眼睛微啟,我只能依稀猜測那不是黑眼珠。也許是淺綠色?
那男人大概是四十歲上下,有那種一天到晚都在健身的體格。二頭肌上有道刺青,是一把長了翅膀的匕首,有一半被拉扯過來的床單給遮住了。他的膝關節上有好幾道疤,還滿深的。下腹部則有一大道細長且已經起皺的疤,我猜想應該是被刀子捅出來的。
到處都是散落的衣物--男人的燕尾服、女人的黑色緊身洋裝和一雙淺口便鞋。還有兩個旅行箱,沒有打開且排放整齊,應該是服務生擺好的。
我抬起頭來,卡麥克和瑪菲正默默看著我。
我向他們聳了聳肩。
「如何?」瑪菲追問道。「這個案子到底有沒有牽扯到魔法?」
「就算沒有魔法,也有轟轟烈烈的性愛。」我告訴她。
卡麥克噗嗤笑出聲。
我也笑了一下--不過那是腦中想要尖叫的念頭在被壓抑住時,想要發洩的反應。我感到胃部一陣噁心,蹣跚著走出房間。卡麥克果然言而有信,準備了一只不鏽鋼桶子在房間外面,我馬上跪下,開始嘔吐。
我只花了幾秒鐘時間便恢復了--不過我可不想走回那房間。我不想再看裡面的景象,不想再看那兩個心臟從胸膛裡炸出的死人。
一定是有人用魔法幹的。這些用魔法傷害他人的人,已經違反了第一戒律。聖白議會看了一定會氣到全體中風。這不是惡鬼或是惡靈幹的,也不是幻想世界裡諸如吸血鬼或洞穴巨人之類的生物在作祟,這是一個幻術師、巫師,或是一個有辦法操弄創生之基本能量的人,有預謀和有計畫的行動。
這比謀殺還惡劣。這是歹毒、卑劣的變態行為,有如用波提伽利(譯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畫家,「維那斯的誕生」之作者)的畫將一個人毆打至死。美麗的事物反而變成毀滅的工具。
倘若你還沒接觸過魔法,這是很難解釋的。魔法是由生命產生,絕大多數來自於人類的感知、智慧與情感。用同樣由生命所創造的魔法毀掉生命本身,這是很駭人的,從某種角度來看,幾乎等同於亂倫。
我再次坐直身子,用力呼吸,吞下口內殘留的膽汁。瑪菲和卡麥克一起從房間走出來。
「好了,哈利。」瑪菲說。「來搞清楚狀況吧,你覺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回答前先花了點時間集中思緒。「他們走進屋內,喝了點香檳,在音響旁邊跳了一會兒舞,愛撫,走進臥房,在裡面待了不到一個小時。在正要高潮時遭到攻擊。」
「不到一小時。」卡麥克說。「你怎麼知道?」
「這張CD只有一小時又十分鐘長,扣掉跳舞和喝酒花掉的那幾分鐘時間,他們就到房間裡去了。發現屍體時,CD還在放嗎?」
「沒有。」瑪菲說道。
「所以CD並沒有重複播放。我想他們是用音樂來營造完美的情調,以符合這間房間和所有的這一切。」
卡麥克不懷好意地嘀咕著:「他想到的,我們也早就都想到了。」他對著瑪菲說道:「他最好是能多想些東西出來。」
瑪菲白了卡麥克一眼,說道:「閉嘴。」她輕聲道:「我需要多點消息,哈利。」
我抬起手整理了一下頭髮。「只有兩種方法可以造成這種傷害。第一種是召喚術,召喚術是最直接、最具破壞力、最華麗的一種魔法,也可以說是幻術。會產生爆炸、火燄之類的東西。不過我不認為這是召喚師幹的好事。」
「為什麼?」瑪菲問。我聽到她的鉛筆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書寫的聲音。
「因為你得要看到或是接觸到你想要施法的目標。」我告訴她。「視線所及之處才能使用。兇手必須要和這對男女待在同一個房間,這樣子就很難掩飾住警方所需的證據,而且有能力使用這種法術的人應該會領悟到--那還不如用槍。槍比較簡單。」
「另一種方法呢?」瑪菲問。
「血魔法。」我說道。「宇宙之道,即為人心。先在小範圍裡引發一些破壞,再用能量造成大範圍的破壞。」
卡麥克哼笑道:「真是鬼扯。」
瑪菲疑惑地問道:「那要怎麼樣使用,哈利?有可能從別的地方施展嗎?」
我點頭。「兇手只需要一些被害者身上的東西就好,諸如頭髮、指甲、血液樣本之類的。」
「就像巫毒娃娃?」
「沒錯,就是同樣的玩意兒。」
「那女人的頭髮才剛染過。」瑪菲說。
我點頭。「妳可以去找出她做頭髮的地方,應該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也許吧。」
「有沒有一些其他有用的消息?」
「有,兇手是認識被害者的,而且我覺得是個女的。」
卡麥克訕笑道:「我真的覺得我們沒必要在這裡聽這些廢話,十個兇殺案裡有九個是兇手認識被害人的。」
「住嘴,卡麥克。」瑪菲說道。「哈利,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站起身,用手掌抹一抹臉。「那是魔法運作的必要方式。當你要施展這種魔法時,它是由內心所發出的。巫師必須要對他們所要做的事非常專注,先想像它,相信它,然後讓它發生。你無法讓不是發自內心的念頭成真。兇手其實可以殺了這兩個人,隨後弄得看起來像個意外,但她偏要搞成現在這樣。這麼做的目的,應該是非要致這兩個人於死不可。八成是為了報仇,妳要找的人可能是個情婦或妻子。
「而且也因為他們死的時候正在作愛,這可不是個巧合。情緒也是魔法的一種管道,一種可以連結到你身上的路徑。她特別挑了一個他們兩人共處而且大展肉慾的時刻,用樣本來作為施法的焦點,且事先就已經準備好了。你不會對陌生人這樣下手。」
「廢話。」卡麥克說道。不過這回聽起來倒像是心不在焉的咒罵,而不是特別針對我。
瑪菲怒視著我。「你老是一直強調『她』。」她質問我。「你他媽的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比了比房間。「因為若不是無盡的恨意,人是不會幹出這麼惡劣的事的。」我說。「而女人恨起人來可比男人還猛。她們更容易專注,讓魔法的效果更好。拜託,女巫就比巫師們狠得多了。對我來說這感覺就像是女性的復仇。」
「但是男人也有可能幹出這種事。」瑪菲說道。
「嗯。」我不直接回答。
「老天,德列斯登,你真是頭沙豬。難道這種事本來就只有女人才會做嗎?」
「嗯,不是,我不認為。」
「你不認--為?」卡麥克拉長調子說道。「好一個專家。」
我對著他們兩人氣憤地蹙眉。「小瑪,我還沒有研究出來需要哪些玩意兒才能讓一個人的心臟炸開。只要我找到答案,就一定會讓妳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再跟我說?」瑪菲問。
「我不知道。」我舉起手,擋住她的下一句話。「我沒辦法給妳時間表,小瑪,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搞定這個案子,更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
「看在時薪五十美元的份上,最好不要太久。」卡麥克嘀咕著。瑪菲瞥了他一眼,她雖然不太贊同他的說法,但也沒有出聲制止。
我利用這個空檔深吸了幾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然後看著他們兩人。
「好吧。」我問道。「他們是誰?那兩個被害人。」
「你沒必要知道。」卡麥克不耐煩地說。
「隆恩。」瑪菲說。「幫我去買咖啡。」
卡麥克轉身朝向她,他並不高,但他整個人籠罩著瑪菲。「喔,拜託,小瑪,這傢伙根本就是在唬弄妳。妳該不會以為他真的能講出些有價值的消息吧?」
瑪菲用冷若冰霜的眼神傲視著她搭檔那汗如雨下但目光銳利的臉,她的眼神足以撼動比她高六吋的傢伙。「不要奶精,兩顆糖。」
「媽的。」卡麥克說。他冷冷看了我一眼(但不太敢直視我的眼睛),雙手用力插進他的褲袋裡,大步走出房間。
瑪菲跟著他走到門口,步伐無聲無息,隨後把門帶上。起居室瞬時間變得更暗、更狹窄,彷彿原本這間俗麗的幽室中有個獰笑的惡鬼,在血腥味和隔壁兩具死屍的記憶中跳舞。
「那女人名叫珍妮佛.史丹頓,她是絲絨房的人。」
我吹了一聲口哨。絲絨房是高價的應召中心,由一個名叫碧昂卡的女人經營。碧昂卡底下有一票美貌、迷人、機敏的女人,她以一小時數百美元的代價把她們仲介給本區裡最有錢的男人。碧昂卡提供的是絕大多數男人在電視和電影裡才會看到的女伴。我還知道她在幻界是個很有影響力的吸血鬼,力量大到可以包山包海。
我以前曾經試過向瑪菲解釋幻界是什麼,她並不是很能理解,但她明白碧昂卡是個經常搶奪地盤的吸血鬼惡女。我們都知道如果碧昂卡底下的女人被牽扯進來,那這隻吸血鬼一定也脫不了干係。
瑪菲切入正題。「這有可能是碧昂卡的地盤糾紛之一嗎?」
「不可能。」我說道。「除非她是和一個人類幻術師槓上了。吸血鬼或甚至是吸血鬼幻術師,都不會在幻界外造成這樣的破壞。」
「她有可能是和人類幻術師發生衝突嗎?」瑪菲問我。
「有可能。但是這不像是她的作風,她沒那麼笨。」我沒有告訴瑪菲的是,聖白議會將讓任何找老百姓麻煩的吸血鬼沒辦法活到他可以炫耀的時刻。我不常和一般人提到聖白議會,就是不太適合。「還有。」我說道。「如果有人類要用傷害碧昂卡的女孩那種方式來打擊她,應該是要在殺了那女孩後留那客人一個活口,這樣他才能宣傳這個故事,影響到碧昂卡的生意。」
「喔。」瑪菲不是很相信,但是她把我的話抄在筆記上。
「那個男的是誰?」我問她。
瑪菲注視了我一陣子,接著平靜地說道:「湯米.湯姆。」
我對她眨了眨眼,讓她知道她還沒有揭露這天大的謎團。「誰啊?」
「湯米.湯姆。」她說。「強尼.馬孔的保鑣。」
這下可有意思了。綽號「紳士」的強尼.馬孔,在瓦格西家族因內鬥而沒落後,由小混混崛起而成為龍頭老大。在經過多年與瓦格西家族的殘酷爭鬥和血腥交火後,馬孔對警方來說是一份五味雜陳的禮物。強尼紳士無法容忍他組織內的任何過當暴行,他也不喜歡他的城市裡有獨行俠出沒。只要不是他組織裡的走私客、搶匪和毒犯,最後都會因不明原因而被趕出城外或是被出賣給警方,或甚至失蹤,再也不見人影。
馬孔在犯罪上的影響力是很文明的--只要他觸角所及,所造成的問題在規模上來說就會比以前更大。他是個非常狡猾的生意人,有一狗票的律師在為他工作,幫他擋住法律上的所有麻煩,徹底封鎖住證詞、文件和電話錄音的威脅。警方從來不願承認,但其實看起來他們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馬孔是實至名歸的--黑道獨裁者。
「我記得我聽說過他有一個打手。」我說。「看樣子現在沒有了。」
瑪菲聳肩道:「看起來是吧。」
「妳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想,先從美髮師這個方向追查吧。我會和碧昂卡及馬孔談一談,不過我已經可以跟你說他們會說些什麼了。」她輕輕把筆記本閤上,不快地搖搖頭。
我看了她片刻,她看起來很疲倦,我也這麼告訴她。
「我是累了。」她回答道。「我對於自己老是被看成瘋子感到很累。連我的搭檔卡麥克都認為我太過頭了。」
「整個警局的人也都這麼想嗎?」我問她。
「他們大多是趁我不注意時皺皺眉頭,用食指在太陽穴上畫圈圈,連看都不看就把我的報告歸檔。其他人則是神經兮兮,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對於以前小時候在Discovery頻道上從來沒看過的東西,都一概不予置信。」
「妳自己呢?」
「我?」瑪菲微笑,她彎曲的唇線帶出動人的嬌柔表情,以她這樣的女強人來說實在是美得過頭了。「這整個世界都快崩潰了,哈利。我想人類是太過自大了,以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我們就已經瞭解了所有的事物。去他們的,我敢說我們只不過才又開始能觀察到我們周遭的未知事物。我變得很憤世嫉俗囉。」
「我真希望每個人的想法都跟妳一樣。」我說。「我就可以少接點惡作劇電話了。」
她繼續淘氣地對著我淺笑。「不過你能想像全世界的電台都在放阿巴合唱團(編注:--BA,為一九七○至八○年代的瑞典流行合唱團,團名為四個成員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歌嗎?」
我們一起大笑。天啊,這間房間真的需要笑聲。
「對了,哈利。」瑪菲奸笑著說。我感覺到她腦中有鬼點子。
「啊?」
「你剛才說你可以找出兇手犯案的方式,只是不確定能否搞得定。」
「嗯?」
「我聽你在鬼扯,你幹嘛要騙我?」
我全身僵直了起來,天啊,她還真是厲害。或許是我太不擅於說謊。「小瑪。」我說。「有些事妳就是不會去做。」
「有時候我也不想去想我所追查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但是為了工作你還是得要去做。哈利,我瞭解你的意思。」
「錯。」我簡單說道。「妳不會瞭解的。」她是真的不瞭解。她不瞭解我的過去,也不瞭解聖白議會,更不知道我頭上正吊著一把德摩克里斯之劍(譯注:借自希臘神話中的典故,表示自己朝不保夕)。絕大多數時間,我都會假裝連自己都不知道此事。
聖白議會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藉口,區區一個藉口就能讓他們裁決我違反了魔法七戒律的任何一條,屆時懸在我頭上的那把劍就會落下。倘若我拼湊出一道製造謀殺法術的配方,而且讓他們發現了,那可就剛好是他們要找的一個藉口了。
「小瑪。」我告訴她。「我不能去研究這道法術,我也不能把這道法術所需要的材料集合起來。妳真的不瞭解。」
她瞪著我,但不對著我的目光,我還真沒遇過第二個人能像她這樣瞪人的。「喔,我瞭解,我瞭解到我現在有個逍遙法外的兇手一直抓不到,我也瞭解到你知道如何幫助我,或是你至少能找出些蛛絲馬跡。而且我也瞭解如果你現在還對我守口如瓶,我就會把你的名片從名片盒裡抽出來撕掉,扔到垃圾筒裡去。」
這招可真婊,警局付給我的顧問費可幫我付了好多帳單--好吧,是絕大多數的帳單。我想,我能體會她的感受。要是我也像她一樣在一片迷霧中辦案,可能也會緊張得跟隻狗一樣吧。瑪菲對於魔法、儀式和護身符之類的東西一竅不通,但是對於人類的仇恨和暴力的認知卻已經是太足夠了。
我對自己說,我並不是真的要準備施展黑魔法,我只是在研究施法的方式。這是有差別的。我可是在幫助警方辦案,就這樣了。也許聖白議會能夠理解的。
最好是啦。搞不好我該找一天到美術館去,尋求全方位的發展。
瑪菲一會兒就把餌丟出了。她勇敢地注視著我的眼睛約一秒鐘後才轉開臉,她的臉看來疲憊、誠懇而且自傲。「拜託,哈利,你要告訴我所有的事。」
標準的憂鬱女人。她這位專業、崇尚自由的女人還真的很會玩弄我這舊觀念的人。
我磨了磨牙齒。「好吧。」我說。「好吧,我今晚就開始。」哎呀,聖白議會會很樂的,我只要想辦法不讓他們發現就好了。
瑪菲點了點頭,在不注視我的情況下吐了口氣,她說:「我們走吧。」接下來便走向門口。這回我沒有搶在她前面先走了。
當我們走出去時,穿制服的條子還在外面的穿堂打混。卡麥克已經不見人影。法醫和驗屍小組已經到了,不耐煩地站在一旁,等待我們走出去。接著他們便帶著塑膠袋、鑷子、燈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一擁而上,從我們身邊走進那房間裡。
當我們在等那座史前時代的電梯慢慢爬上七樓時,瑪菲用手整理了一下她那被風吹亂的頭髮。她戴著一只金錶,這倒是提醒了我。「喔,對了。」我問她。「現在幾點鐘了?」
她看了一下錶。「兩點二十五分,怎麼了?」
我暗自咒罵了一句,轉身走向樓梯。「我和人有約,快遲到了。」
我輕巧地滑下樓梯--這招我練了很久--然後慢慢跑到門廳。我成功閃過了一個滿手提著行李從正門走進來的服務生,大跨步晃進人行道。我有雙身經百戰的長腿,一陣風剛好吹來,我的黑色大衣在背後不斷搖曳。
距離我的辦公室還有好幾條街遠,在跑過一半路程後,我放慢腳步,改用走的。我可不想像隻狗一樣邊喘著氣,邊帶著滿頭被風吹亂的頭髮和汗濕的臉龐,去和找尋走失老公的摩妮卡碰面。
都怪冬天行動不便害我體態失衡,我用力呼吸。這讓我的注意力渙散夠久了,所以我並沒有看到那台深藍色的凱迪拉克駛近我身旁,一位身材頗為高大的男人下車走到人行道上,擋在我前面。他有一頭亮紅色的頭髮和粗厚的脖子,臉看起來活像是小時候被人用木板反覆打扁--除了那對突出的眉毛外。他有著細小的藍色眼珠,而由於體型龐大,使得他的眼珠子看起來變得更小。
我停了下來,後退,然後轉身。又來了兩個人。兩人長得跟我一樣高,而且都是練家子,他們正好也慢下腳步來,顯然是在跟蹤我,而且看起來並不好惹。其中一個有點跛腳,另外一個則蓄短髮,但是他把頭髮用髮膠之類的玩意兒弄得沖天直伸。我總覺得我又回到了高中時代,被一群足球校隊的惡煞團團圍住。
「各位有什麼事嗎?」我問道。我看看四周有無警察,不過我想他們都到麥迪遜飯店去了。人總是喜歡看熱鬧。
「上車。」站在我身前的這人說道。另一個人則把後車門打開。
「我喜歡散步,對心臟比較好。」
「如果你不上車,對你的腿就不大好了。」那人粗暴地說道。
車內傳出一個聲音:「韓崔克斯先生,拜託客氣點。德列斯登先生,我們能聊一下嗎?我本來想載你回你的辦公室,不過你的突然消失造成了一些問題,剩下的這一段路,希望你能讓我送你一程。」
我彎下身看了看後座,那是一個英俊且不裝腔作勢的人,身穿一襲很普通的運動外套和Levi’s牛仔褲,正微笑著注視我。「請問您是?」我問他。
他笑得更開懷了,我敢保證這讓他的眼睛看起來更閃亮。
「我叫強尼.馬孔,我想要跟你談點生意。」
我看了他一下,接著眼神往旁移到那位相當高大也相當孔武的韓崔克斯先生身上。那人一邊呼吸還一邊發出低吼聲,聽起來活像狂犬庫丘撲到女人身上前所發出的聲音(譯注:《狂犬庫丘》是史蒂芬.金的暢銷小說,許多美國人喜歡用庫丘來形容壯碩且脾氣暴躁的人)。我可不想招惹庫丘和他的兩位兄弟。
所以我只好和強尼.馬孔紳士一起坐在凱迪拉克的後座。
這真是忙碌的一天,而我的約會還是遲到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巫師神探H.D.FILES:血魔法之罪(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69 |
小說/文學 |
$ 175 |
中文書 |
$ 175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巫師神探H.D.FILES:血魔法之罪(新版)
哈利.德列斯登是全美唯一掛著巫師招牌執業的私家偵探,也是巫師議會的黑名單No.1。法力高強、腦袋還算聰明的他,最擅長的卻是讓自己捲入無盡的麻煩之中……只不過這對愛侶左上身的饇幹是整個被炸開的。肋骨向外伸出,活像是一大把長短不一的小刀。由大動脈噴出的血液飛濺出他們的有外,一路噴到牆壁上的鏡子,一併噴出的還有已呈黏糊狀的大塊血肉,八成原本是他們的心臟。我記下在毫無生氣的左肺和肋骨旁已呈灰色的內膜,看起來很明顯地是向外噴出,而且是被某種內在的力道扯斷的。──《巫師神探:血魔法之罪》哈利.德列斯登,住在美國的大城市芝加哥。是個有執照的私家偵探,以及,一個掛牌營業的巫師。他同時身為FBI、芝加哥警方與巫師議會黑名單No.1,外加當地最大黑幫的老大一起攪和,不計一切地想招攬他──狀況已糟到出現在他身邊三呎範圍內的電子產品也即刻報銷。但是,當芝加哥市警局遇上超越凡人的創造力和能力所及的案子時,他們找上了德列斯登。當警方向他諮詢這樁血腥無比、和黑魔法有關的雙屍案時,他彷彿看到了白花花的銀子朝自己奔來。然而,只要有白魔法,幕後就會有黑魔法,當凶手知道了德列斯登參與了調查時,也將這位偵探列入了自己的狙殺名單之中……──奇幻文學評論者譚光磊◎專文推薦──「布契這位讀而優則寫的怪胎作者,早就用他機車爆笑的對話,哭笑不得的主角魅力,紮實的魔法設定,以及難以喘息的敘事節奏,擄獲無數讀者的心……他自承一張大嘴老是惹禍上身的巫師哈利頗有自傳色彩,還說這個系列打算寫二十幾集,最後再來個『毀天滅地世界末日三部曲』,因為,有誰不喜歡世界末日呢?」
章節試閱
凱琳.瑪菲正在麥迪遜飯店外面等著我。凱琳和我正好相反,我長得高高瘦瘦,她則短小精幹;我有著一頭黑髮和一對黑眼眸,她則擁有秀蘭.鄧波兒的金色捲髮和湛藍的雙眼;我的輪廓全都細瘦得有稜有角,還有個鷹勾鼻加尖下巴,她則渾圓玲瓏,還有個在啦啦隊長臉上可看到的可愛鼻子。 這是個有點風的沁涼天氣,宛如一般的三月天。她穿著一件長外套,搭在長褲套裝上面。瑪菲從未穿過洋裝,我一直懷疑她應該有一雙結實、有形的小腿,就像體操選手一樣。她的體能很發達,這一點從她辦公室裡那兩座合氣道比賽的獎盃即可證明。她的頭髮齊肩,在春風裡...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吉姆.布契
- 出版社: 奇幻基地 出版日期:2008-08-28 ISBN/ISSN:9789866712265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